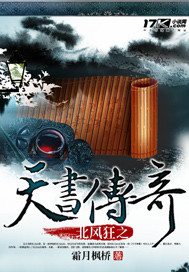慕缺也是越斗越惊,跟这些黑衣人也已拆过上百招,竟一人都没伤到,虽说是只守未攻,也惊叹于这些高手之间的默契。舟上两个黑衣人一直观战,见亭下已渐渐围上,两人同时出招,分袭向慕缺、古烟萝二人。
亭下本不宽敞,黑衣人一涌上来,慕缺渐觉施展不开,一把拦腰抱起古烟萝,往上一掠,一掌拍飞了亭盖,落在了亭顶。黑衣人也陆续蹿上亭顶,又是一番抢斗。刚出手的两个黑衣人明显比其余人武功高出不少,他二人一加入,慕缺对古烟萝已护应不及。
黑衣人又布剑网,攻势越来越急,眼见一人刺向古烟萝,慕缺飞身一转,一掌拍向黑衣人,却被黑衣人跃身躲开。又一人从肋下突刺,慕缺刚想截住,忽见剑锋一荡,摆向了古烟萝。
慕缺一急,闪身上前,护住了古烟萝,手臂却被剑划了一道。
自打入江湖以来,慕缺从未受过半点轻伤,现在又见古烟萝深陷险境,怒火陡起。闪身一掌打飞古烟萝近旁的黑衣人,又伸手弹断身后袭来的两剑,抬腿一扫,只听“噗噗噗”三声响动,三个黑衣人跌落到了湖里。
正当慕缺应付当前几个黑衣人时,又听得一声响,慕缺大惊,转头一看,才知是黑衣人想偷袭慕缺,被古烟萝打飞出去了。慕缺从不知古烟萝会武功,且能胜过黑衣人,那武功决计不低。
湖上中年人突然朗声笑道:“姑娘,你还是出手了啊!”
话刚一落,又从林中窜出十来个黑衣人,黑影一晃,也掠上了亭顶。两人被重重围上,古烟萝出招利落,一时半刻,黑衣人也近不得身。
慕缺暂去了后顾之忧,从容应敌,又打伤几个黑衣人落到湖里。黑衣人见斗不过慕缺,又分出数人把古烟萝困住了。慕缺一急,又打翻两人,夺下一把剑,几个起落,又刺伤数人,落到湖里。
见慕缺渐地逼近,六名黑衣人接连换招,一举制住了古烟萝。六把剑分别抵向古烟萝各处,逃无可逃,一黑衣人抬剑指着慕缺道:“住手!”说完又把剑抵在了颜若喉颈处。
慕缺大怒,把剑扔出,又刺翻一人,冷冷道:“放了她,我留下。”
黑衣人看他剑已脱手,一拥而上,把慕缺也围在当中。
古烟萝突地喝道:“不准动他!”
慕缺转头一看,发现古烟萝一脸冷峻,怒目而视。倏儿看向慕缺,眼神陡换,目光灼灼又满是柔情,饱含关切。
中年人道:“姑娘,父命岂可违?”
古烟萝:“父命不可违,夫命亦不可违,烦劳先生转告父亲,夫死妇随,断无余地!”
慕缺未料她如此性烈,看她一副言辞笃定之态,就知此生此世,二人必然能生死相依,也算是遵了诺言。暗叹:有妻如此,况复何求!心头一暖,笑了出来。
中年人叹口气道:“知女莫若父啊?斋公倒也留了一条生路。”说完又对慕缺道:“慕大侠,自废武功,离开此处,再不过问江湖事,可否?”
慕缺漠然道:“容易!”说完强注内力,冲破心脉,一口鲜血喷出,武功尽散。
古烟萝心痛莫名,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兀自难过落泪。
中年人大笑一声:“方才我布的剑阵,举天下英雄,能堪堪应付的,不过五人而已...好啊!天下数一数二的武功,说废就废,大侠之名确也担得。”忽脸色一换,阴沉沉问道:“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慕缺本想大笑,却牵动了心脉,反而咳嗽了两下,道:“若是连这都食言,你家那主子也成不了大事,你也趁早别跟了。”
中年人笑过两声,向古烟萝道:“姑娘,斋公留下两句话带给你:父女缘尽,好自为之。”
此话一出,古烟萝心中悲怆,泪落涟涟。
黑衣人随即撤走,古烟萝将慕缺带到亭下,等返回住处,才发现竹枝、晚霜两个丫头早已被杀,古烟萝悲痛欲绝,放声大哭。慕缺稍作调养,古烟萝也心情稍有平复后,二人才把两个丫头入土为安。
经此变数,害的慕缺废了武功,两个贴身丫头横遭大祸,古烟萝也决定不再隐瞒身世,向慕缺尽数道出。
原来古烟萝本姓陆,其父正是火行主陆止渊。几年前入京,也并非是家道不幸,误走风尘,而是受父命接近金玉楼,随时打探金家父子情况。只是意料之外遇上了慕缺,就此一发不可收拾。虽在金玉楼处呆了几年,但也只知了了,引得陆止渊大怒,这才回了绿竹林。而此处才是古烟萝自小长大的地方,竹枝、晚霜二人也是打小跟从,三人情同姐妹。几日前,古烟萝得到父命,要其除掉慕缺,古烟萝本想跟慕缺一走了之,不料被猜到会逃走,这才派人来追杀。
慕缺听完,倒不觉多意外。初见古烟萝,看她体貌举止,就似长于富贵人家,只不知还有这等身世。
慕缺问:“你爹为何要杀我?”古烟萝摇了摇头。
慕缺又问:“为何有这么多一流高手?那中年人又是谁?”
古烟萝又摇了摇头:“我只知他叫梁充,我自小就管他叫先生。”
慕缺疑道:“梁充?当年殷光照有个座上宾也叫梁充。”
古烟萝还是摇头。慕缺见她所知确是不多,也不再多问。二人简单收了些细软,拿上琴,装了马车准备离开。
慕缺架着马车,古烟萝坐在车里。
古烟萝问:“我们去哪儿?”
慕缺道:“鼠兄给我们找了去处?”
古烟萝道:“那是哪儿?”
慕缺笑道:“听说那里奇山秀水,风景如画,没有江湖,没有名利,男女作种,老幼相携,是个隐居的绝妙去处。”
古烟萝满怀憧憬,轻声问道:“真有这样的地方?”
慕缺缓声道:“那是鼠兄的故乡,我去过,还跟他约定要是死了都葬在那儿。”
古烟萝心生雀跃,一脸笑意,似是已经在脑中勾勒起往后那平淡闲适的生活,渐有些沉醉了。半晌道:“这样才好,正好你没了武功,就不会想着再出来了。”
慕缺抿嘴一笑,轻声自语道:“武功?会回来的。”
说完,赶着马车直往西北去了。
杨青羽与沈末二人悠悠的打马往南,又自汉水下长江,入到洞庭湖。刚出发沈末就说,只把杨青羽送到岳州就回杭州,眼见进了洞庭湖,沈末却再决口不提要走的事,杨青羽也装作不知,从来不问。
二人本打算先找到干戎,大喝一场,后一细想,岳州府说大不大,但要找个人也还是不易。
魏允贞曾有诗云:“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自范文正公挥毫写就《岳阳楼记》,岳阳楼之大观遂天下闻名。二人从湖上一靠岸,就直奔岳阳楼。
庆历年间,滕子京谪守巴陵,治为天下第一。政成,增修岳阳楼,范仲淹为记,苏舜钦书石,邵竦篆额,一时精笔,天下叫绝。
杨青羽所思所念想亲眼一睹的,正是这被称为“天下四绝”的“四绝碑”。
岳阳楼几经损毁,又几经重修,依旧盛名在外,游人往来络绎,争相瞻仰。岳州之地,水陆通衢,帆舶鳞萃,不少人跟杨、沈二人一样,不辞远道,只为一睹这蔚然大观。
岳阳楼除了“四绝碑”久负盛名,李太白一联“水天一色,风月无边”也脍炙天下人口。
二人细细看了两遍,心满意足,就近寻到一家酒楼,临窗而坐,正前方凭栏可眺岳阳楼,右侧放眼可望洞庭湖,位置绝佳。
二人点了几个菜,要了一坛酒,喝了起来。难得开怀,二人自顾尽兴,只是瞥见邻桌一年轻人觉得行径怪异。这人面目清秀,身着浅灰直裰,一副读书人模样。
桌上一方砚、一沓糙纸,这人不时抬头左看右瞧,又沉吟片刻,继而在纸上写写画画,不知一壶酒已喝了半晌,也自在陶醉其间。
杨青羽端着一碗酒走到这人跟前,招呼道:“兄台旁若无人,可是在写文章?”
这人道朗然一笑:“兴之所至,聊以述怀而已。”
杨青羽扫了眼纸上的字,见他年纪轻轻,笔力不弱,来了兴致,搁下碗,拱手道:“兄台,高作可否一览啊?”
这人哈哈一笑:“尽可一览,尽可一览。”
杨青羽见他一派洒脱,毫不拘束,确跟料想中的读书人截然不同。
杨青羽随手拿起一张,念道:“游之日,风日清和,湖平于熨,时有小舫往来,如蝇头细字,着鹅溪练上。取酒共酌,意致闲淡,亭午风渐劲,湖水汩汩有声。千帆结阵而来,亦甚雄快。”
其文畅快,不拘时体,别有生气,杨青羽惊其才学,又随手抽出一张,念道:“九水愈退,巴江愈进,向来之坎窦,隘不能受,始漫衍为青草,为赤沙,为云梦,澄鲜宇宙,摇荡乾坤者八九百里。而岳阳楼峙于江湖交会之间,朝朝暮暮,以穷其吞吐之变态,此其所以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