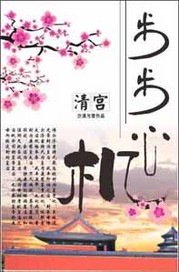萧昊天此时早已听见远处隐隐传来的鸾铃声,一骑蹄声答答而来,飘飘洒洒的雪霰子里,他抬头望过来,看见骑在马上的男装佳人,一双眸子宝石一样灿烂,波光流转,素净的小脸因为冷更如是白里透粉,如同水蜜桃一样。
他呆愣一下,以为自己是因为日夜思念产生了幻觉,微微闭了一下眼睛,再次睁开,见朝思暮想的人就在他眼前,对他微微一笑,在这冰天雪地里如同百花齐放,悦耳的声音响起:“王爷,我来了!”
萧昊天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他看见马上的凌东舞翻身跃下,向自己翩然而行,萧昊天觉得西边的晚霞不知怎地突然黯淡了下去。
他竟然毫无意识地愣愣的看着凌东舞走到他身边,“王爷!”凌东舞珠玉般的声音在他耳边再次响起。
萧昊天这才猛然惊醒,神情带着些慌乱:“凌丫头……是你,真的是你!”
凌东舞还是第一见到萧昊天如此失魂落魄的样子,突然觉得心跳加速,面上火烫,她暗吸了口气,平静了下来,微笑道:“王爷,是我,我来看你了!”
萧昊天这时似乎清醒了一些,双眼燃烧着热切的光芒,看见凌东舞因为寒冷不住的搓手,急忙把身上的紫貂大氅脱下来裹在她的身上,银狐的领子几乎挡住凌东舞半张脸,他则只穿着青色箭袖,腕上翻起白色的马蹄袖,把他映衬的更加玉树临风,精神至极,“凌丫头,来,随本王进屋吧!”
凌东舞随萧昊天进到屋里才发现,萧昊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落魄,这间屋子舒服温暖,屋里已经拢了地炕,凌东舞从外面一进来,只觉得热气夹着些幽香往脸上一扑,暖洋洋的一室如春。
两只鎏金大鼎里焚着安息香,那淡白的烟丝丝缕缕,凌东舞仔细看了看格局,单是八宝架上的翡翠玉如意就不是一般人养的起的。地上铺着大红的波斯地毯,一梭一纬都是手工做的,价值不菲。那一朵朵的花,红的让人耀目。
萧昊天见凌东舞的脸被冻得都变了颜色,亲自把她带到屋里,忙不迭的让凌东舞坐到里面暖阁的火炕上。凌东舞坐在炕上只顾四下张望,一低头才发现竟然是萧昊天在亲自为她脱靴子,她急忙把脚抽回来:“王爷,还是我自己来吧!”萧昊天这时也缓过神来,刚才自己只是担心凌东舞冷,急着让她脱下靴子上炕,竟然没发现自己这个动作有多逾越。
凌东舞因为骑马,无法活动手脚,鹿皮靴套在脚上冰冷透骨,她因为手疼得发僵,折腾了许久也没办法把冻的硬邦邦的靴子顺利地脱下来。萧昊天见状,再次蹲下身,捉住她的脚踝,帮她把靴子脱下来。他的手心凉凉的,停在脚踝处一阵酥麻。凌东舞看着他的头顶,脚背的神经不自觉地抽搐起来。她准确地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内侍这时已经移过脚炉,道:“王爷,脚炉来了。”
凌东舞的脚已经被冻的几乎没有知觉,伸着脚放在脚炉上,暖和着渐渐缓过劲来。
萧昊天到外间吩咐人给凌东舞准备洗澡水和饭菜,同时吩咐人速速去京城为凌东舞取几件合身的貂裘来。凌东舞一听急忙光着脚跑到外间,急急的说到:“不要那么麻烦了,我只是路过此地,本打算来看王爷一眼就走的。”她又看看外面有些黑了的天说:“现在晚了,我明早就走。”
萧昊天从看见凌东舞开始一直热切的眼睛,一下子变的暗淡下来,沉吟不语,那双漂亮狭长的蓝眼睛看着她,距离分明这样近,她却没有办法望到尽头,似乎他的眼晴就恰如一泓深潭,她永远探不到底,也因此看不清掩在其后的那些念头和情绪。
侍女把凌东舞带进里间的浴室,正是隆冬季节,这里却温暖如春。室中临池设有石床,一色的汉白玉治理,隔壁房间安装有加热的铜炉,热水经过引流到浴室里时,已经水波荡漾,丝丝热气弥漫,恰到好处的温润。
浴台设五色流苏锦帐,外面罩一层帷幔,用纯白色锦丝制成,薄如轻雾,如梦似幻。帷幔的四角,各放置一个纯金镂花的香炉,香炉中用烧着名香,散发出一种淡淡的香味。
凌东舞目瞪口呆地看着如此豪奢的浴室,从她见到萧昊天的住所后,就发现他在这样也并没有受半分的委屈,反而看起来过得很惬意自在。
凌东舞见侍女们把准备好的衣服放下,鱼贯的退了出去。她仔细的检查了一下门窗,见都已经关好,才放心的下了浴池。
她连日奔波,疲惫不堪的身子浸在恰到好处的热水里,懒洋洋的舒适让她都想哼哼……也不知过了多久,感觉到腹中饥饿,她才起身,走到旁边放着衣物的台子前。萧昊天很细心,让人送进来一套男装,一套女装。
凌东舞拿起男装刚要穿上,想了一会儿又放下,换上了那身女装,梳理好头发,走了出去。
萧昊天自从当年和凌东舞在乌口城中一别,在这过去五年多的时间里,每次看见凌东舞,她都是穿着紧身衣裳,男人装扮;今天见她本色容颜,脂粉不施,清丽无匹,穿着一件月下白透地罗袄,衬底是淡紫红绘纱女袄,系一条绛紫色罗湘裙,刚露绛瓣蝴蝶弓鞋,织银沿边大裙摆拖曳地,胸前挂着八宝璎珞,头上斜插一支金掠细巧金花鬓钗,绝色面容更是沉鱼落燕,惊艳异常。
萧昊天见惯绝色粉黛无数,如今,竟觉得生平所见女子,统统加起来也不及凌东舞的万一。凌东舞见萧昊天难得失神呆愣,对他微微一笑,烛光下但见她明眸如水,光亮照人。
萧昊天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掩饰的干咳一下,引着凌东舞来到桌边吃饭。凌东舞走到桌旁,只见上面已经摆好了十分精致的菜肴。
萧昊天道:“凌丫头,吃饭了。”
萧昊天吃饭的时候话不多,只是一杯接一杯的喝酒,喝的凌东舞都有些心惊,明灭的烛火,仿佛主人的心思,飘摇不定。在这个冬夜里,平添了几分阴郁。
凌东舞知道眼前这个曾经意气风发,气吞山河的镇南王已经变成了匣中猛虎,空有大鹏之志不能伸展。但是,他和自己一样,还有大把的人生要走,总不能揪着这个问题一辈子放不开吧!
于是干笑两声说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实这样闲云野鹤的生活也很好啊,我感觉王爷你现在在这里反倒享受起来,这在以前哪有机会啊!”
萧昊天此时已经从初见凌东舞的狂喜中清醒过来,他清清楚楚的记得,两个月前暗机门给他传回的信息,凌东舞和穆紫城举行了婚礼,只差入洞房那么最后一个步骤了。他听到那个消息时,嫉恨的想杀人!几欲疯狂。当时的自己觉得心是彻底的死了,再也不会复活了。
当悲伤足够巨大时,人就会在心死的疯狂麻木中变得平静下来。内心的绝望让他认命的接受凌东舞永远离开了他的事实,用酒精麻醉自己,用美女腐蚀自己,直到父亲去世。皇帝利用机会不断的排挤他,他万念俱灰的交出兵权,没有带任何女眷,只带着一支禁卫军来到景山,给父亲守灵。
但萧昊天万万没有想到凌东舞会来看他,千里迢迢,顶风冒雪的来看他,心中对凌东舞那份痴狂的念头,在见到凌东舞的一瞬间,又死灰复燃一般。他心想,如果你要在这里一直陪着我,就算如此过一生我也很是快乐,可是明日一早,你就要离开了!萧昊天心中痛楚难言,只得强颜欢笑,满满一杯酒饮下去,呛得喉间苦辣难耐,禁不住低声咳嗽。
凌东舞听说萧昊天被没收了兵权后,日以继夜的赶来这里,本来有一肚子要劝慰萧昊天的话,可是看见他以后,尤其是现在,又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苍白的,无力的。
二人一时具是默然,低头吃饭。
过了半晌,凌东舞咬咬嘴唇,终于开口问道:“王爷,你真的,真的被夺了兵权吗?”
“自古以来,帝王都知道,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所以君主对掌兵武将向来忌惮,武人本就难以操控,一个不慎便有军变之险。本王早就知道自己日后必遭人猜忌,所以有今日之事,也在意料之中!”
凌东舞听了萧昊天的话,心中顿时百味掺杂,一时说不清是酸是涩,口中却是笑着,说道:“我,我真的觉得王爷现在这样也很好,至少不必在出生入死,随时的身处险地。”
“是啊,这么多年的征战厮杀,本王还真的是累了,所以这次就索性顺了他的心意,歇息一下。只不过本王运气不济,即使闲来无事,也无法体会到红袖添香的乐趣了!”
凌东舞闻言一怔,抬眼见萧昊天正静静地望着自己,眸光如水,沉静隽永。她自然知道萧昊天话里的意思,不由把心一横说道:“王爷,你还不知道吧,我已经和穆紫城成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