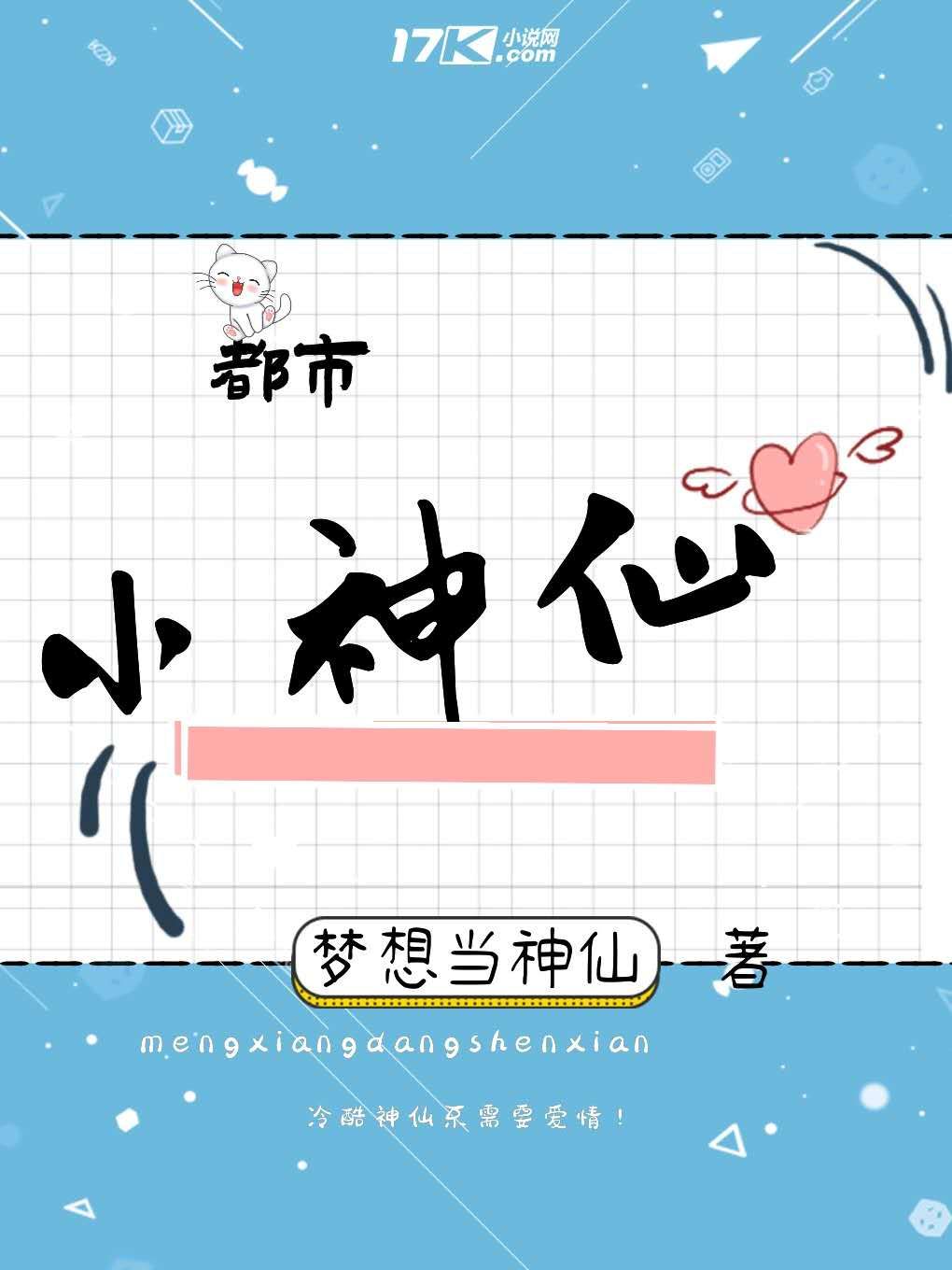福宁姑姑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了片刻终于开口:“你呀,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我们在皇后娘娘跟前儿伺候,其实跟在御前伺候的人一样,皇上每隔几日便到娘娘这里来,所以比起别宫的奴婢,我们更容易触怒龙颜,更应该小心谨慎着点。你倒是好,这般张扬,日后可怎么办!”
“我?张扬?”我诧异地看着她,她拍了拍我的手:“旁的我说也不合适,话就说到这儿,谨守本分才是要紧的。”
说完,福宁姑姑就掀了帘子出去了。留下一头雾水的我,坐在榻上一个人发愣。
我想着,总算是虎口脱险,怎么也应该去给恩人道声谢才好,于是就起身端了芙蓉糕朝皇后娘娘的大帐走去。赫舍里皇后向来不是很死板的人,所以我们做贴身丫头的也就轻松了点。我站在大帐门口,高声叫了几声没声音,门边又没人守着,想来娘娘许是睡了,于是就端着糕点打算转身就走。这时候,却听见帐内传来“哗啦”一声,像是什么东西落地砸碎了的声响,我一惊,赶忙掀了帘子冲进去。这一进去不要紧,该看见的不该看见的都看见了。
我转过身捂住眼睛跪下来:“皇上娘娘赎罪,奴婢该死!”
半晌没听见身后有声响,就想着悄悄移动到门口溜出去算了。还没来得及动作,就听见身后传来皇帝的声音:“别跪了,过来帮忙!”
这回,不是康熙被我撞破傻在原地了,而是我就这么傻了。帮忙?帮什么忙?
“奴婢……奴婢实在不精于此道,请皇上恕罪!”我颤颤巍巍地开口,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事。
身后却就在这时传来了脚步声,来人一把将我拎了起来,奈何我现在身体缩回了十五六的模样,轻的要命。我用手捂住眼睛不肯回头看。却被人狠狠地将手掰下来,定睛一看身后这位不是我们的康熙爷是谁啊!他用左手拎着我,打着赤膊,眼神里满是戏谑。
“你以为朕想让你帮什么忙?”
我的目光从他的脸向下移,猛然看见皇帝流血的右臂,顿时一惊:“皇上!”
赫舍里这时走上前来,用纱布将伤口捂住:“皇上,您快坐下来!”语罢转头瞥向我,有一丝的不悦:“还不快过来帮忙!”
我应了个是,赶忙上前。待将康熙的胳膊包扎好了,我竟出了一头的汗。退到一旁立着,看赫舍里为皇帝将衣服穿好。又想起非礼勿视,于是赶忙低下头。
“这会儿知道不该看了?”皇帝的声音似笑非笑地响起,我将头埋得更低,沉默是金,沉默是应对一切挑唆的法宝,以不变应万变!打定主意就紧紧咬住下唇不说话。
皇帝却笑了:“说你胆小,你做出的事儿照比平常女儿家不知道出格了多少,若说你胆大,这会儿倒是没了个声响了。”
我答:“奴婢在别人面前胆大,在皇上面前胆小!”
“哦?倒是朕有那么可怕喽?”他的语调微微上扬,听不出情绪。
我依旧低着头:“皇上那叫威严,不是可怕!”千穿万穿马匹不穿,这个道理在马身上都受用,何况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呢!
果然,他不再追问,良久才开口:“今日的事,既被你撞破,本该除了你以绝后患,但看在皇后的份上,便饶了你,所见之事切不可告诉任何人,你知道后果!”
我心里一紧:“奴婢什么也未曾看到。这就告退了!”
皇帝朝我摆了摆手,我得了意思,就赶忙跪安出门。
我是来送点心的,可不是来送命的。
第二日我一早奉皇后娘娘的旨意进去送新花样的茶点,康熙依旧时一脸云淡风轻的模样,丝毫没有伤患的痕迹。这或许就是做帝王的功力。我上前将茶现在康熙面前布好,然后走到各位陪聊大臣面前上茶。
听闻一直在御案前埋头的康熙忽然开口:“好!真是好词!”
福全道:“我早说过好,皇上今日总该认同了!”
康熙笑:“朕何时说过不认同了,这些年来,朕也读过他不少词作,而这首《金缕曲》道尽了有情有义的男儿精魂!实在是令人不得不叹啊!”
我听他如此夸奖,便垂头望去,但见那笺上刚劲的字体是分外的熟悉。
金缕曲
谁复留君住?叹人生、几番离合,便成迟暮。最忆西窗同翦烛,却话家山夜雨。不道只、暂时相聚。衮衮长江萧萧木,送遥天、白雁哀鸣去。黄叶下,秋如许。
曰归因甚添愁绪。料强似、冷烟寒月,栖迟梵宇。一事伤心君落魄,两鬓飘萧未遇。有解忆、长安儿女。裘敝入门空太息,信古来、才命真相负。身世恨,共谁语。
我心里一紧,只默然心道,公子。
福全上前一步:“这个纳兰性德确是个人才,皇上您看如何?”
康熙点头:“就怕到头来只有这绣花枕头的功夫,孱弱书生总不算好!”
福全脸上一愣,有些诧异地望向皇帝。我已经没心情思考他这个神态是什么意思了,我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就在那一刹那腹中的话就脱口而出了。
“纳兰公子才不是绣花枕头,公子的骑射也是一流的,只是此方才气更胜而已。”
这话一出口,屋内所有的人都愣愣地望向我,我赶忙放下手中的茶,垂首而立,不知道该怎么收这个场。
半晌才听见康熙开口道:“朕听闻,这个纳兰性德是你的表兄?”
我一惊,顿时发觉自己的莽撞。他本就是等着我这句的,帝王就是帝王,对我的性格已经摸透了。我张口应了个是,就不再出声,只继续低着头,苦笑自己的幼稚与愚蠢。却也一边想着,他这般试探我的缘由。
“福全,你向来与纳兰交好,如此定是见过若浅这丫头的!”康熙的语气不动声色,但我却是狠狠紧张了一回,若是福全知道我在明府里的一切,那我岂不是就是欺君之罪了。我转头偷偷望向福全,却恰好撞上他望向我的目光,只一瞬,他便偏过头去,望向皇帝:“回皇上的话,福全一直以来只与纳兰公子在别院渌水亭中相交,很少到明府去,更何况若是没有特殊缘由,女眷也是很少出来见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