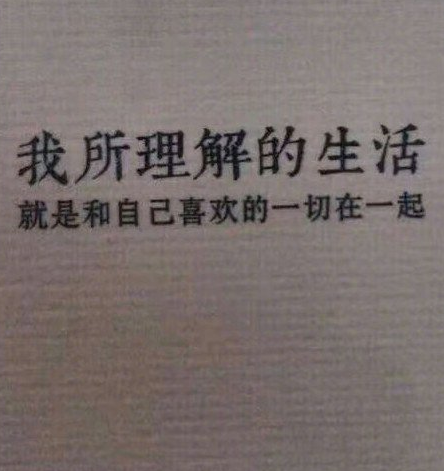那天晚上下了场大雨,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停,因为考虑到农忙季节,厂子里给爸爸放了一天假,劳累的他们一直睡到了第二天傍晚。
起床后他们才发现肚子已经前胸贴后背,猪圈里也传来饥饿的嚎叫,妈妈往猪圈里先倒了半桶水,然后倒进半背篓猪草,去爷爷奶奶那里接我回家,把我交给爸爸,然后自己去地里摘菜,不一会儿回来就开始做饭。
所有的事情一气呵成,几乎没有浪费一分一秒。
“展堂,你看。”妈妈提着米袋子让爸爸看,“还有这么多!我们今天全吃米饭吧!”妈妈高兴极了,说完似乎又觉得自己好像说错话一样,默默的把米往盆里倒。
“你平日都没吃吗?怎么剩这么多!”爸爸瞪着妈妈。
“怎么没吃,没吃的话这米哪里去了,我要是不吃现在还能做饭吗,早倒下了。”妈妈开玩笑似的说着,一边把洗好的米倒进锅里。
爸爸没有接着话说,只是抱着我到灶前帮妈妈添柴烧火,妈妈则洗菜切菜炒菜。
不一会儿,香喷喷的饭菜就上桌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爸爸在家吃晚饭,也是第一次看到妈妈的碗里是雪白的米粒。
晒谷子也是一件累人的事情,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晒着金灿灿的一片,那是大家来年的生活基础,所以累却也是快乐的。
地方有限,每天能晒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晒好还得一点点搬回屋里,要是遇到午后的瞬时雷雨更是麻烦,谷子被雨淋湿后要晒两三个太阳才能干,妈妈一个人是根本快不过大雨的,有时候邻居李婶家要是先抢完的话就会过来帮忙。
过了大半个月,谷子终于全部晒干了。
那天妈妈叫爷爷奶奶称谷子,因为分家的时候说好的,谷子晒干后要给他们一千斤。
“爸,你跟妈现在空不?我把谷子称给你们吧。”妈妈找到村口跟别人一起喝茶的爷爷。
“你没看到我现在没空啊?”爷爷没个好声气。
“那要不你看哪天有空跟我说一声。”妈妈说到。
“你还是去吧,给你谷子都不要!”“是啊!”“先去嘛!”一起喝茶的人劝说到。
看大家这么说,爷爷便问:“谷子晒干没有?”
“晒干了的,全部都晒干了的,要不你去看。”
“这样,你明天再弄出来晒一下,下午收的时候我跟你妈再过来。”
“哎呀,晒干了的还晒,还能多晒出几斤水?”“明天要是下雨呢?”旁边有人挖苦道。
“下雨!下雨就等天晴了再说!”爷爷显然自知理亏,甩下这句话拂袖而去。
还好第二天太阳不错,妈妈先晒了五百斤称给爷爷奶奶,又等了个好太阳晒了剩下的五百斤。妈妈知道要是一千斤铺在一起晒有点厚了,他们又会挑刺的说没晒干。
秋收后家里有了好多好多的谷子,在屋里用围席围得跟山一样,不愁吃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秋收仗打完后,人们又开始了乘凉,他们聊得更开心,收获的喜悦在纯朴的人们身上是掩饰不住的。
后来太阳渐渐的没那么毒了,夜晚也越乘越凉,不知不觉的,已是深秋。
我满一岁了。
一岁的我开始学走路,学说话,一切变得那么美妙。
妈妈下地里干活也会带着我,我可以待在路上玩泥巴,再大一点后妈妈就允许我到地里边了,因为我可以在地里站稳啦。
冬天的脚步加快了,门口的大黄桷树下没有了人们乘凉的谈笑声,得安静好几个月,黄桷树就那样静静的守候着村庄的静谧。
近过年的时候我们家可热闹了,因为家里杀猪,妈妈邀请了村里很多人过来帮忙。另外一头猪早在几天前就被卖给到村里来收猪的屠夫了。
关于过年前邀约亲友到乡村杀年猪,现在有一个时髦的叫法,刨猪汤。
看着大家忙里忙外,我也跟着高兴,吃饭的时候爷爷奶奶也来了,是妈妈去叫的,邻居们都夸妈妈贤惠,不知为什么如此优秀的妈妈就是得不到爷爷奶奶的认可,他们装出一副大家长的姿态注视着一切,也许是妈妈太出色,想掩饰他们的无地自容,又或许是想在鸡蛋里面看能不能挑出骨头。
那一天就像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聚会,热闹非凡,喧闹声久久才褪去。
剩下的肉妈妈全部做成了腌肉,然后用一种特殊的纸包起来,这样可以放的时间长一些,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冰箱。
人们总是勤劳而智慧的,这种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追求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年猪一走,猪圈清闲了几天,妈妈很快就联系好卖小猪的人家。
过年的热闹新世纪的小孩都已经没法体验,那时候物质条件是匮乏的,很多东西都不是平日里能唾手可得,于是节日多了仪式感,腊月里的大扫除,准备年货,买新衣,除夕祭祖贴对联,年夜饭从上午就开始准备,除夕夜有压岁钱,三五块钱能让晚辈们高兴一年。
过年那几天爸爸要上班,所以去给外公拜年也拖了很久。外公有大半年没见妈妈了,分家后家里条件拮据,妈妈要照顾我,还总想着多种点菜能去集市换些银两以减轻爸爸的负担。
外公几次带信问妈妈情况,妈妈都说过得很好,可外公总是担心自己的女儿的,他知道即便过得不好她也不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