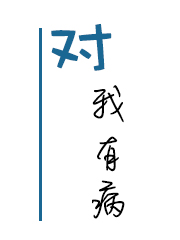给馨雅讲故事的事情,还一如既往地进行,她依然会中途有惊人之举。
那次说到我从来没有给妻子送过玫瑰花的事情,她又突然蹦出来,说:“其实是送过的,送的不是真玫瑰,是用狗尾巴花代替的,女儿那时已经3岁了,当时是一家人在郊外玩儿,女儿还说,爸爸你为什么送妈妈玫瑰花不送给我。”
这次我并没有生馨雅的气,反而很开心地笑了,也许是因为当时的那个氛围太温馨好玩儿了。
“你笑什么?”馨雅问我。
我说,“笑你刚才讲的那个场面啊!”
馨雅好奇地盯着我:“我讲什么了?”
馨雅能“未卜先知”的都是我跟妻子之间过去发生过、我准备讲但还没有说出来的事情或者情景。我经常怀疑馨雅有特意功能,能知道或者预判我的思维走向。
但这终究不是一个正常人的行为方式,必须好好检查,该治疗及时治疗,发展下去谁知道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真成了一个精神病的话,我也难得安生。
上次把馨雅骗去医院检查,没有发现器质上有什么问题,我想这次应该从心理上去找大夫看看。
从馨雅叔叔打听到馨雅车祸后负责她康复治疗的医院和主治医生后,一直还没顾上过去,为了在心理医生面前能提供尽可能有用的信息,我决定在带馨雅见心理医生之前一定要去一趟馨雅的老家。
“你为什么这次要出差这么久?”馨雅听说我要出差一个星期,感到有些惊讶,连续出差6-7天在我的工作中是极少见的。而我之所以说要那么长时间是考虑到了解馨雅过去康复治疗的过程有可能不如想象的那么顺利。
“也不一定,顺利的话也许3-4天就回来了。”我轻描淡写地说。
“你在外面可一定不要喝多酒晚上出去惹事啊!”
“你还是认为那些事是我干的,是吗?”
跟雯雯的事情也好,砸串烧店也罢,我已经跟她解释不是我做的,看来馨雅仍然没有完全从内心排除对我的怀疑。
======
按照馨雅的叔叔提供的医院名称和地址,我很容易就找到了当地的市中心医院,但是找到那个当年的主治医生还是费了不少周折。
当年负责馨雅康复治疗的康大夫已退休几年了,另一个了解情况比较多的李护士长已经辞职另谋高就去了。
医院方面给我的是康大夫家的座机号码,我从医院出来就开始拨打但一直没人接听。心想反正也是要见面聊的,索性直接上门吧。吃了闭门羹后,电话依然没人接听,我不得不返回医院继续找医院负退休办去拿到了康大夫的手机号码。
难怪康大夫家里没人接听电话的,老两口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女儿家,帮女儿看孩子。
但康大夫女儿的小家在另外一个城市。
两个城市有几百公里的距离,跟康大夫约好后,当天只好就地住下,第二天再去找他。
晚上正在街面上吃晚饭,馨雅打电话过来,追问我在哪儿出差,听那口气非常懊悔没在我出门之前问清楚。我撒了个谎,随便说了一个城市的名字。馨雅半信半疑地让我晚上能不喝酒就尽量别喝酒,千万别出去了,早点睡觉。
我本来就没有喝酒的计划,自然答应得非常痛快。没想到晚上半夜11点我都迷迷糊糊要进入梦乡了,馨雅又微信视频我:“你是在酒店房间里吗?”
“你什么意思?查岗啊?”我知道馨雅还是不放心,怕我出去惹事。
“我才不稀罕查你岗呢!嗯,不错,是在房间里,早点休息吧。”
第二天一早,我赶第一班高铁去找康大夫。
为了不影响康大夫女儿家的生活,我把康大夫请到附近的一个茶庄。康大夫明白我的来意后,不住地摇头感叹:“真是一个奇迹啊!包括从省城大医院请来会诊的专家,没有一个人认为馨雅还能活过来。即便她刚活过来的时候,大家也认为她只能是一个卧床不起的植物人。”
“这还得感谢您医术高明、妙手回春。”我恭维道。
康大夫挥了下手,摇着头:“别说那个,我真没那么大本事,我只能说这孩子命大。唉,真是悲惨又可怜,爸爸妈妈一下子就都没了,她自己当时还完全失去了记忆。”
“对了,康大夫,我就是想找你了解一下馨雅那时记忆康复的情况的。您能跟我大概说说吗?馨雅恢复记忆花了多长时间,后遗症明不明显?”
康大夫用力砸吧两下嘴巴:“别的很多病人的情况我都记不全了,馨雅这孩子的情况我还是记得的。这孩子经过脑部手术后的记忆恢复得很快,也就2个多月吧,有些客观事实的记忆就开始快速恢复,特别新东西记忆能力的恢复超出我们的想象,不然的话,她不可能完成他的大学学业。不过,”康大夫顿了顿,遗憾地摊了摊手,说:“她关于自己身份、生活经历、亲人、情感情绪方面的记忆似乎完全丧失了。”
“我也听馨雅说过,说她叔叔告诉她的,她没有关于父母的任何记忆,也没有关于自己过去的记忆,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岁数,一无所知。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
“怎么会这样?有记忆就是有了,没有就是没有,还存在选择性吗?”
康复流露出无奈的表情:“从器质和神经方面,不太容易解释清楚。但参照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我们当时认为馨雅的情况适合用解离性失忆症来解释,因为这种失忆症最常见的而表现就是对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失忆,但对一般资讯的记忆则是完整的。”
“您是说馨雅当时就具备解离性失忆症的特征?”
康大夫点点头,进一步解释:“这个对馨雅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因为她能够借助外界帮助很快重新确定自己的身份,也可以把过去的生活经历像复印机一样复制到自己的记性中,但情感感受这些东西却没法复制,所以馨雅没有对过去生活经历的感性成分,真的像是‘六亲不认冷漠无情’的样子。”
“您的意思是说,她记忆的能力恢复以后,你往她脑子里灌输什么就是什么,她能记住,但情感上的东西她没法认可,是吗?”
“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吧,情况比较复杂,我们也不是什么都懂的。”
“您经手她的康复治疗期间,注意到她还有什么其他后遗症没有?比如总有似曾相识感?”
“似曾相识?这个当时还没听她说起过,但我们也留意到她有恍惚的时候,这一点也能够理解,毕竟脑部受到过那么大的创伤,偶尔出现记忆混乱或者错搭从而感到困惑也是难免的。”
“没错,她现在也经常神情恍惚,灵魂出窍一样的。最让人担心的是,明明她没经历过的事情她总觉得自己经历过参与过,还把自己当成另外一个人,您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康大夫很吃惊的样子:“怎么会这样?有没有到医院检查过,比如脑部组织经过这些年后有没有什么器质性的变化?”
我告诉康大夫已经排除了器质方面的问题后,康大夫沉默了一会儿,很婉转的口气让我带馨雅找心理医生看看,他认为馨雅的那种创伤不只是肉体上的,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也是非常严重的。
我想康大夫并不是心理方面的专家,再跟他探讨怕有些勉为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