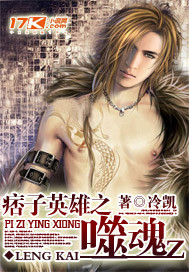一个白色的身影逆光猛的扑向萧启,正是赤额,萧启本来就是勉力支撑,撞击之下,仰面倒在地上,昏厥过去。
赤额开始没有察觉,但当它嗅到萧启身上的血腥气后,低低哀嚎一声,委屈的从萧启身上爬下来,回头看向安平,安平也发觉出不对,急忙蹲下身,探查萧启的脉搏,半响才叹口气,看向奚正阳:“怎么回事儿?”
奚正阳一愣,茫然摇头道:“我也不清楚……”
“不清楚?”安平愤怒的抓起奚正阳的肩膀,狠狠的晃着,脸上的面具愈发狰狞:“你和他一直在一起你不知道?”
奚正阳摇摇头,垂首不语。
安平一拳打在奚正阳小腹,然后弯腰抱起萧启,走出山洞,奚正阳捂着肚子想要跟上,却被安平狠狠喝止:“不许靠近他!”
奚正阳自觉理亏,不敢跟上,只是低声道:“外面有敌军。”
“我不会傻到跑到外面去!”安平冷冷的丢下一句话,抱着萧启转身离去,赤额冲着奚正阳低吼了一声,也跟在安平身边。
安平抱着萧启,来到黑山寨一间还算完好的卧房,将萧启轻轻放在散发着霉味的木床上,抬手为他摘下面具,只见萧启双目无力的微睁着,青黑的嘴角黑血已经干涸,心中又是一痛,赤额也呜咽着要去舔萧启嘴角的鲜血,却被安平阻止:“有毒。”
赤额呜咽着看向安平,眼中满是祈求,安平不语,只是用腰刀划开自己的手腕,鲜血汨汨而出,继而撬开萧启紧闭的双唇,将流血的手腕伸到萧启唇边,谁料萧启剧烈的咳嗽起来,有一大口黑血涌出,溅到安平的手腕上,火辣辣的痛。
安平叹了口气,等萧启平复下来,又将手腕伸到他唇边,等到伤口凝固了,便再划开一道,如是折腾了三四次,萧启面色才稍稍有了些改变。
安平有些头晕,便坐在床上,看着昏迷不醒的萧启,心中有些悲凉,主人,你总是想着兄弟们的愿望,还记得你自己的吗?
曾经你说过,只想回家,尽人子之责,还有伊娜,伊娜……
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安平飘忽的思绪,安平扶起萧启,轻轻替他捶背,萧启好不容易缓过气来,又昏昏沉沉的睡去。
安平将萧启的面具拿起来,七郎,就是带着这个冰冷狰狞的面具为了所谓的誓言征战沙场,对与萧启的做法,安平谈不上认同,但不得不敬佩。
只是七郎,什么时候你才可以以本来的名字和面目,傲然立在朝堂之上?
赤额呜咽着跳上床,看了看昏睡中的萧启,又看了看一脸沉静的安平,将大脑袋放在萧启肩窝。安平扫了一眼赤额,道:“你去叫其他人来吧。”
赤额恋恋不舍的看了萧启一眼,听话的跳下床,奔出屋中。
安平的视线,重新落在那只面具上,恐怕即使齐煜也不知道,这张鬼面背后,承载了七郎的多少坚毅和柔情?又隐藏了多少迷茫与苦痛。
“将军他……还好吧?”
安平惊讶抬头,却是奚正阳。
此时再为萧启戴上面具已是来不及,于是挪到床头挡住萧启的脸,才冷冷道:“你来作甚?”
“我……”堂堂天时将军奚正阳此时却有些理亏:“七将军他还好吧?”
“死不了!”
这个回答将奚正阳噎的一愣:“没保护好将军,是我的责任,回到军营,自然会领罪。”
安平也知原来在千夫营时,奚正阳对萧启百般照拂,刚才而言相向也是因为担心萧启,此时见他这样说,本来心生不忍,可又想让他赶快离开,只得硬下心肠道:“这里有我,还请奚将军回去吧。”
奚正阳长出一口气,犹豫道:“七将军他……是展邦吗?”
安平一怔,自觉刚才并没有让奚正阳看到,便稳住思绪,冷声道:“不是!”
“不是……”奚正阳怔怔看着安平手中的面具,摇头道:“怎会是……他死在中州了,那么年轻……”
安平心头也是一阵黯然,但还是冷漠道:“奚将军请回吧,这里有我就好。”
奚正阳强忍住想看一眼萧启容貌的冲动,道:“鹿肉已经烤好,一会儿给将军送来,我命人熬了些汤,等七将军醒来后,还烦传个话。”
安平不耐的点点头,奚正阳一步三回头的离去,约莫着奚正阳已经走远,安平刚想起身,就听萧启轻声道:“面具给我。”
安平木然的递上面具,萧启拿在手里,并没有着急戴上,而是虚弱道:“何苦对奚将军恶言相向……他……”
安平垂下眼皮道:“属下知错。”
“并非责怪你……安平……奚大哥他似乎认出我了。”
“七郎……”
“他问我,是不是展邦?我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名字,回答他不是,也不算说谎,对不对?”
安平不知如何回答,沉默半响道:“七郎,奚将军知道也不是坏事……”
“我又怎能害他?”萧启挣扎着坐起身,神情略微激动:“我怎能害他……我已经不算个活人了……”
安平不善言辞,只是沉默。这时,萧启冰冷枯瘦耳朵手搭上安平的手腕,轻声道:“你……用你的血救我?”
安平怕伤到萧启,不敢挣脱,只是低头默默不语。
“我不想死,可也不想让你受伤……”
“安平此生,只为护七郎周全。”
“可你……可想过自己?”
“七郎你想过自己吗?”
萧启不语,可眼神中满是黯然。
安平自知说错了话,推说去给萧启拿鹿肉汤,起身走开,只余萧启一人静静坐在床上,看着手中的面具,有看向门外已经暗淡的天色,只觉更深的疲惫袭来,而胸口的疼痛丝毫没有减轻,挽起衣袖,看到那条黑线除了颜色浅些,根本没有消失,看来,身上的毒并没有完全解除,摇摇头,看向灰白的墙面,只觉上面黑点乱窜,而呼吸似乎也有些不畅,于是又软软倒在床上,昏睡过去。
萧启再次醒来,已经是五日后,兄弟们已经带他走出马头关,回到大齐军营。
安平等人将萧启安置在军营外专门为家眷准备的平房中,日夜守候照顾,又有迷糊日日熬药,萧启的精神还是慢慢好了起来。那条黑线在距离心口一寸处止步不前,颜色也变成浅灰色。
可无论安平和迷糊怎样努力,那根线的颜色,却丝毫不会淡去,对于大家的担心,萧启只是一笑置之,精神略好时,还是会不顾阻拦翻阅各种情报,而一直与咯卫什百越互市的黎子建,也不时送来手下商队“不经意”搜集的情报。
很快便已入秋,咯卫什那里迟迟没有动静,缇娜部落也是一直没有任何动作,对于这种平静,众人虽然不安,但也知可以利用这一时机韬光养晦,以期一举破敌。
这日,萧启喝完药,就闻有人来报,黎子建来访,便请他进来。
不料这次郁矜飏竟然也一同前来,黎子建一见萧启,第一句话便是:“这几日觉得身上怎样?”
萧启笑道:“早已无妨,只是兄弟们坚持要我在这里。”
“你莫要大意。”郁矜飏毫不客气的坐在萧启对面,端起茶水喝了一口,道:“关外风沙真大,幸亏我有带茉莉膏,否则我的脸可就毁掉了。”
“我家娘子花容月貌,怎么会毁掉?”黎子建笑着摸了摸郁矜飏的头:“也不知谁坚持要过来。”
“家里大的小的吵得我头疼,躲躲清静!”
“怎么,不怕我再给你添几个小的?”黎子建丝毫不避讳萧启在场,玩味的笑道。
郁矜飏也没有普通女子的娇羞,只是大笑道:“那我就多生几个,吃穷你们黎家!”
萧启低眉浅笑,只听郁矜飏在叫他:“神尊,可否让我看看。”
萧启知道他要看那条黑线,便也没有推辞,挽起衣袖将手臂放在桌上。
郁矜飏凑过来,几根乱发弄得萧启的手臂微微发痒,半响,郁矜飏道:“曲径幽那几人该打!根本没有将神尊照顾好。”
萧启忙道:“无论是百越战场还是在咯卫什,他们三人都是出了大力的,还请前辈不要责怪他们。”
“呵呵。”郁矜飏调皮一笑:“神尊不嫌弃他们三个就好,这几日不要太劳累,静养为主便好。”
萧启苦笑道:“有兄弟们管着,我不想静养都难。”
几人又闲话了一些江湖事和互市发生的趣闻,黎子建与郁矜飏便告辞离去。
两人走出军营五里,黎子建才问道:“风起他怎样?”
郁矜飏叹了口气,道:“回去我便写信给活不救。”
黎子建大骇道:“真的要找她吗?她不是……不救活人吗?”
郁矜飏垂下眼帘,半响道:“一个月内,活不救不来,就真的救不活了……”
“安平的血不是一切毒的克星吗?”
“是,可正因为如此才更加危险,他的血只能抑制铁箭上的毒,而那花斑和尚掌风之毒,却不是安平能解。相反,两毒本是一体,安平的血解除铁箭上的毒,让我们看不到黑线,自然也不知道那花斑和尚的毒已经发作到什么程度,现在神尊身体虽无明显不适,可那掌风之毒,已经扩散进入心脉,危急万分。”
“那……安平岂不是害了他?”
“自然不是,如果当时没有他的血,神尊早就不在这人世……”
黎子建点点头:“既然如此,唯有联系活不救了,还望她不要拒绝才好。”
关外,咯卫什皇城。
扎卡亲王猛的将手中的战报扔在地上:“什么?那七将军还没死?”
跪在脚下的副将战战兢兢道:“启禀大人,那七将军即使不死,也撑不过一个月。”
“一个月?”扎卡亲王怒道:“一个月?他竟然还敢再活一个月?我现在就要他死!死得越痛苦越好!”
副将道:“王爷,等那七将军毒发时,自会痛苦死去,花斑和尚说了,中了他一掌的人,都是痛死的。”
“痛死?会比失去儿子还痛吗?我要让他看着身边的人一个又一个的死去,然后毒发攻心,痛苦而亡!”
副将道:“王爷的意思是……”
“意思?还能有什么意思?真是笨蛋!”扎卡亲王用力踢了副将一脚,吼道:“给我派兵,攻打大齐军营!不管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将他们赶尽杀绝!”
副将皱了皱眉头道:“王爷……入秋大齐会加紧戒备的。而且,这半年,他们围墙加固了不少,听守卫说,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士兵的呐喊声,可见他们在日日练习,想必军力也加强了不少。”
“没骨气!”扎卡亲王骂道:“我堂堂咯卫什男儿,会惧怕那些弱小的汉人吗?”
“王爷,并非害怕,只是……”
“我知道了,我会和缇娜那里联系,只要是为了除掉七将军,他们和我一样不惜任何代价!”
是夜,两骑在黑暗中从咯卫什皇城出发,向北飞驰而去,很快便不见了踪影。
几乎与此同时,一只雪白的信鸽从石城飞出,一路向南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