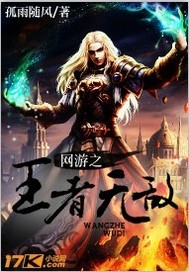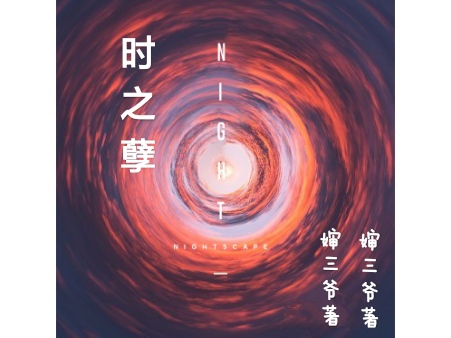秦舒玉志学之年前,除了日夜感知体内先天精气之外,对医学药理也涉猎不少,毕竟成为正式的修者之后,免不了就要与人交手。
修者之间的对决,更容易受伤,而且,一般情况都是要命的伤势,而他生来就未曾考虑过,要把自己身体健康与否的决定权置于别人手中。
所以,在这个医药层面,他下的功夫或许并没有比感知气息来得少。
细米草乃属于常用药,他自然一清二楚。
见秦舒玉王君尧两人一来,守在门口的段德明还有县衙的人面上一喜,正想上前打招呼。
王君尧却偷偷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们暂时不用过来。
她所熟知的秦舒玉,是个对长辈极其尊敬的人,此时,他爱的女子的叔叔段明德就站在药铺门前,他却未先去见礼,就说明,他还不着急暴露身份。
她的手下自然听从她的指示。
而段明德同样会遵从,他每隔半个月都会上夕河县衙汇报乡里治安状况,自然认得这个红衣少女乃县令爷的千金。
他进药铺里去了。
听得秦舒玉的话,华服男子仿佛被戳到痛处,手上的药方折都不折一下,便慌慌张张甩进了袖口,而后,正了正面色,冷道:“你也知那是寻常之人吃了这味药才不会犯忌,而我马家车队的那几人,个个身受重伤,或许本就伤到了心脏,亦或是早年落下暗疾也未可知,但他许文林他身为大夫,望闻问切,不弄清楚明白,便胡乱开方子,这就是草菅人命。”
秦舒玉淡然一笑,道:“可我听说你们马家欲以谋杀的罪名罪将许大夫告上县衙。”
华服男子越发理直气壮,道:“那是因为本少爷话还未说完,本少爷现在怀疑,许文林根本事先就诊出了这六人心脉受损,才刻意用的这味药,其目的就是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他们。”
这人便是马子禄吗。
观他面相,印堂塌陷,眉毛粗疏,这样的人,很冲动,也同样自负。
秦舒玉心里暗暗一笑,面上却不动声色,道:“杀人需要动机,我听说许大夫平素待人宽厚,鲜少与人结怨,与你们马家更是相隔十数里,似乎想结怨也不太容易。”
马子禄冷笑道:“或许你还不知道,今晨许文林为这六人上药之时,动作粗鲁,他们吃痛,就忍不住打骂了他几句,哪想,他如此心胸狭隘,不甘受辱,便恶向胆边生,下此毒手。”
乡邻们中,有人再也听不下去了,他们面色愤然骂道:“你们这完全是在污蔑……”
秦舒玉举起了手,让他们先别激动,这些乡邻们见他是帮着许大夫说话的,便听他指示,安静了下来。
见此,秦舒玉才摆出一副了然的模样,道:“原来那六人还能张口骂得,出手打得,我以为他们早就痛得奄奄一息了。”
马子禄皱眉道:“你这是何意?”
秦舒玉道:“这六人既然还有余力打骂,就说明服药之前,他们心脏的损伤并不严重。”
马上禄问道:“这有何干?”
秦舒玉笑道:“你是真的一点药理都不懂啊。”
忽地,他面色一转,冷道:“莫说二钱细米草,便是生煎二两让他们几人喝下去,也绝无可能在半个时辰内,全数暴毙身亡。”
马子禄怒目斥道:“你如何知晓,你是大夫?”
秦舒玉沉声道:“我不是大夫,但今日便是京城御医来此,也是这个说法,这本就是医学常识。”
马子禄撇嘴道:“还京城御医,你以为你是谁,请得动他们?”
他呸了一声,道:“本少爷不是大夫,也不懂什么药理,但本少爷的眼睛可好使得很,反正本少爷只瞧见我马家那几位兄弟死去的时候,右手死死拽住胸口,这不是死于心脏骤停,又能是什么?”
秦舒玉笑道:“不错,心脏骤停,确有此症状,不过……”
马子禄道:“不过如何?”
秦舒玉学着刚才华服男子的模样,寒声道:“我怀疑,这一切就是你们马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自己演一出戏,目的就是想陷害许大夫。”
马子禄丝毫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道:“你这种胡说一气的话,有谁会信。”
马家那些跟来的人也是笑了起来。
连乡邻们都忍不住摇了摇头,小声议论道:“马家的人不至于如此残忍吧,拿自家人的身家性命去陷害许大夫。”
“我虽然支持许大夫,但也觉得这个年轻说得不太靠谱。”
只有王君尧相信,她知道有些人掉入了坑里而不自知。
秦舒玉却看起来很固执的道:“我这话绝不是胡说八道。”
马子禄全当听人说书了,竟拍手鼓起掌来,他饶有兴趣地道:“好,本少爷听你刚才之言,杀人可是需要动机的,那你来说说,我马家有何缘由,为陷害一个既没有名声又不富裕的大夫,狠到残害自家兄弟。”
秦舒玉没有着急正面回答,而是慢悠悠地笑道:“近些年,我时常听到向家的一些人,甚至是下人,都在吹嘘向家实力如何强横,每年都在涨你们马家的回佣,今年更是要收你们马家多达七万余两。”
他靠近了一些马子禄,轻笑道:“而你们马家的大部分人,屁都不敢放一个,竟有人还当场表态支持向家,这种做法,明明有伤家族根基。”
乡邻们听得当即一片哗然,一是被这回佣的数额吓到了,二是,想不到乡里实力最强的马家,竟对远在数十里之外的向家摆姿态如此之低,未必也太没下限了。
马家来的人中,一位车队的灰衣管事马脸一黑道:“喂,你小子没有根据就别胡说。”
马子禄脸上的笑容也是瞬间凝固,他不禁退了一步,甩手喝道:“你这是从何处道听途说来的,绝对没有这回事,而且,此事和你说的杀人动机有关联吗?”
秦舒玉却仍是绕着弯子,自顾自的道:“当然,我也听说了,你们马家有些人也还是颇具气节的,大骂向家狮子大开口,不给人留活路。”
马子禄面色好看一些,他免强挺了挺胸膛,沉声道:“我们马家的人个个都是好汉,岂会如此奴颜婢膝。”
秦舒玉突然讽刺道:“是吗?我为何听到有人在传,说那些骂过向家的车队,之后一直闲置在马家无所事事,而那些支持向家的却有货可运,就比如此次帮向家运盐去往玉田镇的这支,他们的管事便是第一个支持向家的。”
马子禄当即甩手怒喝道:“这是谁活腻了,敢传我马家的谣言,最好别教本少爷抓到,否则,看本少爷不打烂他的嘴,我马家出车队,历来都是按排号来。”
秦舒玉遂道:“想来是我听错了。”
马子禄面色一滞,厉声道:“喂,你小子一直在这里拐着弯抹黑我马家,是不是你根本就说不出我马家有何杀人动机,所以一直拿本少爷开涮了。”
他伸手指着秦舒玉,厉声道:“你若真说不出来,那你就是在造谣生事,本少爷可就要履行方才的诺言,动手打烂你的嘴了。”
那个车队管事已经冷笑着开始摩拳擦掌了。
秦舒玉丝毫不惧,淡然道:“那我还是说回刚才那个车队吧。”
他轻咳一声,道:“这个车队的管事支持向家,但他几个手下却对此颇有微词,常常在暗地里骂他软骨头,吃里扒外。管事很生气,可碍于整个车队的颜面,他不好拿他们怎么样,就一直拖着,一直被他们戳脊梁,久而久之,积怨加深,这个管事便萌生了杀意。”
马子禄越听脸色越阴沉,他道:“你该不会是想说,这几个骂他们管事的人便是那死去的那几人,而这个管事便是要杀他们的人吧。”
秦舒玉微笑着道:“马少爷果然聪明,一听就明白。”
“竟然是这样?”乡邻们终于听明白了一些,便开始起哄了。
马子禄身后的管事忍不住跳了出来,他凝着粗眉,对秦舒玉粗声骂道:“你小子纯属放屁,老子就是这个车队的管事,他们几个虽然是对老子支持向家有怨言,但也只敢暗戳戳地抱怨,所以,老子根本不在意,更谈不上想杀了他们。”
秦舒玉笑得更欢了,他道:“如此看来,向家向马家索取巨额回佣的事不假,而这次死的也确实是这几个人了。”
管事呼吸一滞,道:“你……”
他再也说不出什么来,因为他一冲动,便被套了话去,就退了回来。
但他并不后悔,因为他确实没有杀这几个手下。
乡邻们刚才被管事吓得噤声,此刻又开始指指点点起来:“原来真有这回事啊!”
“那这杀人栽赃的事,只怕也被这个年轻人说中了。”
马子禄脸皮很厚,反倒镇定了下来,他道:“那又能如何?商场上收回佣之事本就是潜在的规矩。”
秦舒玉笑道:“那我至少就不用被马大少爷打烂嘴了,毕竟,我已找到你们马家人杀人的动机。”
马子禄又问道:“那还有陷害许文林的理由呢?”
秦舒玉瞬间变脸,寒声道:“许文林乃许清妜之父,许清妜是夕河镇秦家庄少庄主秦舒玉的心仪之人,秦舒玉又和向家大公子向坤有仇,因为他废了向坤的手下,抢了向坤先看上的女人。所以向坤联合你马家设计陷害许大夫,想引出秦舒玉来,加害于他。”
他瞪着马子禄,轻声问道:“不知我这次说的,马少爷能否听懂?”
马子禄心中一沉,眼神明显开始躲闪,道:“秦舒玉是谁?”
“他不正站在你面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