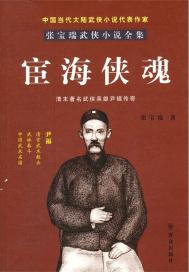灵竹躲开他来拉自己的手,飞快地跳进船舱。祈岁小砂锅里的水溢了出来,沾到衣摆上。“呃,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灵竹挠挠头,真是百事不利。
祈岁皱着眉拿起旁边的抹布,一声不吭地自己擦拭,然后把砂锅盖子盖上了。等小馄饨煮好,祈岁分了三碗,招呼流云进来吃。灵竹见到他,像躲瘟疫一样躲得远远的。祈岁察觉到异常,问道:“你们怎么了?”
流云端着瓷碗,表情很是无辜。“她嫌我坏……”
祈岁拨弄着虾皮和紫菜,眼皮都不抬,说到:“若是论坏,谁比得上霁雪。记得当年情窦初开,我莫名喜欢上小芽菜,心里没谱,不知道要不要告白,就拉着霁雪躲在花丛里偷看,问他漂不漂亮。”
说到这里,祈岁很轻地哼了一声。“第二天我再偷偷去看小芽菜,发现霁雪那小混蛋堂而皇之地牵着她的手。从那以后,我再喜欢上谁,死都不告诉霁雪。流云你把灵竹藏了那么多年,实在很英明。”
灵竹被汤汁呛到了,咔咔地咳着。流云闻声看过来,这次灵竹摸摸鼻子,没再躲开。年少无知时,大家都有过这么天真可爱的往事啊,唉!
回到灵府的时候,已经入冬,竟央和萩侞带着一大帮侍女小厮等在大门口,听见马蹄的声音越来越近,神色也越来越期待。等流云下了马,把灵竹从车里抱出来,竟央和萩侞早就笑得合不拢嘴,甚至侍女们都欢腾起来,小厮拥上来准备牵走马匹。
灵竹不好意思地从流云怀里跳下来,扑向萩侞,抱着她的胳膊使劲蹭。“灵母灵母,我好想你。”
萩侞把她的双手捧在怀里暖着,眼睛留恋地在她脸上逡巡。“瘦了,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灵竹调皮地笑着。“哪里有瘦,我天天过得特别自在,胖了不少,不过都被衣服盖住了,灵母看不到。”
竟央朝流云和祈岁点点头。“风主,魂主。”
祈岁回了礼,便抱住手臂站到一旁,也不多话。流云以准女婿自居,自然是一番礼貌的交谈。唠叨了好一会儿,竟央才说到:“太高兴了,一时糊涂,这大冷天的。赶紧进来吧,屋里烤着炭火,备着热茶,暖暖身子。”
灵竹往自己的院子走去,刚到拱门,就看到瑶儿带着几个丫头,等在门口,见她回来,慌忙迎了上来。“幼主,您可回来了。”杏眼里盛满了笑意,语气半是高兴半是埋怨。“您在外边游山玩水,把我们丢在家里大半年,我们好孤独啊。”
她身后穿着绿衣服的小姑娘也跟着说:“是啊,幼主,您不在,府里一下子冷清了好多。”
灵竹笑呵呵地左手抓一个右臂揽一个,往自己屋里拖。“冷死我了,等我进了屋子暖和暖和,你们再说我也不迟。”
依绿捧着刚沏好的热茶走过来,瑶儿从她手里接下来,递给灵竹,又把一个小巧的暖手炉塞进她怀里。“幼主,喝口热茶就会舒服很多,再拿这个暖暖手,有点热,小心别烫着了。”
灵竹小心翼翼地抿了几口茶,寒气逼出来了,舒坦地叹了一口气。隔着衣服捧着暖炉,胃部烘得暖和和的。“还是家里好啊。”
瑶儿从桌子上端来点心盘子,说道:“幼主尝尝这个,又酥又脆,甜甜的,非常好吃。”等灵竹拿下一个,咬了一口,复又问道:“幼主,您这次出门,是不是见了很多好玩的事?跟我们说说吧,我们都很好奇。”
灵竹经不住一堆小丫头渴望的眼神,只好一点点地叙述沿途见闻。讲到花主容貌时,她们都一脸花痴,口水都要流出来。讲到战争的残酷时,她们又一脸不忍,泫然欲泣。灵竹挑一些不太重要的事讲了讲,舞桐的死,席捷的复活,都隐瞒下来。
一番话讲完,瑶儿羡慕地说到:“幼主,您好幸福啊!风主陪着您游乐,还能看到那么多风景,经历那么多有趣的故事。”
灵竹挑眉。“你觉得我很幸福?”
瑶儿不断点头。“当然啊!不信您问问其他人,依绿,你说,幼主是不是很幸福?”
其他的丫头也附和地点头,灵竹忽然就想到舞桐,自己不也曾经认为她很幸福么。这样一想,灵竹不由得苦笑,人们总是会把自己之外的人想得很幸福,而在那光辉外表之下的苦楚,他们看不到。位于高处的惹人艳羡的位置,从来不是那么简单,处于那个位置上的人,必须承受多于常人数倍的痛苦。
不过,都无所谓了,在其位谋其事,既然注定如此,顺应天意便是,多想无益,只会自寻苦恼。于是灵竹很得瑟地抖动肩膀,说:“是啊,我很幸福啊,你们不要太羡慕哈。”然后在众人嫉妒的眼神里,笑得特别傻。
第二天早晨,灵竹刚刚起床,坐在梳妆台前,任瑶儿宝贝地梳她的头发,流云就进来了。灵竹在铜镜里看到他的影子,也没回头,笑道:“云哥哥。”
瑶儿抬头看到流云,慌忙行礼。“风主早安。”
流云点点头,走了过来。灵竹见他手里拿着东西,忍不住转身去看。青花瓷盘,清澈的水,彩色鹅卵石,养着一株碧绿的水仙。“给我的?”
“嗯,无意中看到了,就拿一棵来送你。”流云把水仙放到梳妆台上,而后把手搭在灵竹肩上。“花开的时候,清纯美丽,就像竹儿一样。”
灵竹本来在抚摸水仙的叶子,听到后一句,很不好意思地收回手。瑶儿轻笑了下,故作正经地说到:“风主、幼主,我先退下了。”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想的,还顺便把门带上了。
灵竹很无语。“看看吧,都是你,让人误会了。”
流云拿起瑶儿放下的梳子,接着替灵竹梳头发,两个人的身影倒映在铜镜里,模糊如梦境。“夫人,我们有什么好让人误会的,不都是事实么?”
灵竹惊讶地站起来。“谁是你夫人?不要乱叫。”
流云眼波流转。“对呀,谁是我夫人?”然后不怀好意地笑着,拉住灵竹的手,去挠她腰侧。“你说是谁?是谁?”
灵竹边笑边躲,奈何挣脱不开,眼泪都笑出来了,腰弯得像大虾。“我投降!我是希望是那个人是我啦,只不过……”灵竹突然收口,掩饰地嘿嘿傻笑。
“只不过什么?”流云抹去她两颗泪,又抚平乱了的头发。“难不成你要悔婚?有我在,你不会得逞的,早日打消这个念头吧。”
灵竹也不再回话,拉着他往外走。“早饭应该准备好了,走走!吃饭吃饭!”
五个人坐在大圆桌旁,安静地喝粥吃清淡的小菜,灵竹不知是不是被那句夫人刺激到了,一顿饭表现得特别贤淑,不论谁碗空了,都抢着盛饭。
祈岁莫名其妙地盯了她好久,灵父满脸女儿大了知道回报父母了这种幸福的笑容,灵母也感动得不行。流云一开始还很欣喜,飞快地解决自己碗里的粥,然后大大咧咧地往灵竹手边一放,看她乖乖地站起来添饭,异常满足,但渐渐的表情就痛苦起来。
早饭后,流云的眉头皱成了川字,手抚在胃部,嘴角紧紧抿着。灵竹担心地问道:“云哥哥,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流云刚张开嘴,就打了个特别响的饱嗝。灵竹满头黑线,听他接着说道:“吃得太撑了……”
灵竹看着他脸上委屈的神色,很是无语。“又不是特别好吃,吃那么多干吗呀,真是……”说着就要去找瑶儿,问问她有没有消食的药。
流云一把拉住她,眼睛水汪汪的。“你侧身盛饭的姿势特别好看,我只不过想多看几次。”
灵竹沉默,半天后叹了口气,无奈地帮他揉胃,说:“以后又不是没有机会。”
流云把她的手按在胸口。“以后太远了,什么变故可能发生,我能握住的,只有现在。”
灵竹惊异地抬头,心想,难道他都知道了。但想了想,还是不要问的好,彼此都装作若无其事,这样平静而温馨的感觉,才比较自然。于是灵竹转转眼珠,坏主意冒上心来。“云哥哥,我帮你促进下消化吧!”
等流云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被逼着换上一身小厮的衣服,头上裹着一张白毛巾,手里拿着一把大扫帚。而灵竹为了表现有难同当,也换上了同样的装束,手里的扫帚几乎跟她一样高。流云忍不住嘴角抽搐,“竹儿,你这是要做什么?”
灵竹十分威武地叉着腰,嚷嚷道:“小云子,不要多话,快点扫地!”说完大力一挥,飞起尘土一片,流云被呛得咳嗽不断,举起扫帚开始反击。于是乎,两个平日里优雅高贵的人穿着粗布麻衣,挥舞着笨重的扫帚,上演全武行。
祈岁正巧路过,看到两个小厮不好好扫地,闹腾得乌烟瘴气,不由得厉声喝道:“你们干什么呢!”而等那两个人转过脸来,除了眼睛和牙齿是白的,整张脸变成炭黑,嘿嘿笑着看向他,祈岁的嘴巴张得可以塞下一枚鸡蛋。“你们……”
两人解开头上已经变得灰不溜秋的白毛巾,用力朝他挥舞做告别状,扫帚在地上拖出长长的沟痕,转身大摇大摆地走了。留下震惊过度的祈岁,傻傻地站在原地,几乎风化在空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