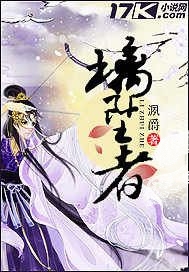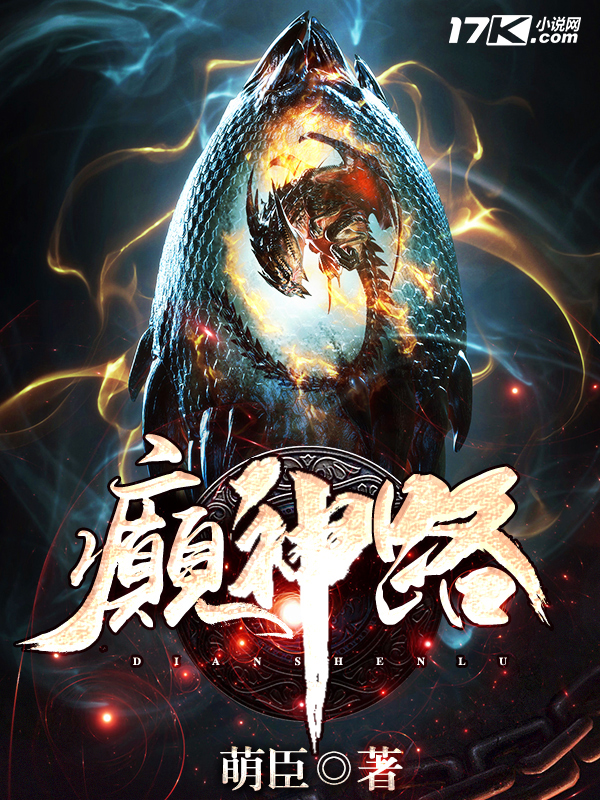海梓暄跟海纵天正在昔悦楼三楼的隐蔽雅间内,沏着一壶大红袍茶相向而坐,端着杯身轻轻吹热烟......
今日早朝,吏部尚书刘琮年上表,奏曰诸位皇子虽未大婚,但皆逾弱冠之年,文成武威乃国之大幸,如今天下太平民富安康,皇子可以效法宇空大陆的其他先朝,封土立府,为各处驻地稳定民心,为各处百姓谋求后世太平。
明显这折子是针对他们俩来的。但细想之下,如此长居于宫中,在宫内和众皇弟贵戚中威信日升渐长,对大婚之事又一再推托。三帝已颇有微词,如此一表。正中下怀。
此奏尚属潼文天宇朝政的新举措,如平地惊雷,但郑郑有词之下,又不无道理。惹得众大臣议论纷纷,一个早上都在争辩没个结果。让他们心凉的是,最后荣帝来了句,交由门下省管审议。
一登九五绝三亲。出生皇家,犹如行走独木,看来帝爷此番是动了心,要镇一镇他们的帝位,肃一肃宫里的境况。而且,最近确实出了很多事,在他们看来皆是查得毫无头绪……
“三哥,看来这道奏折拟来,也不会是一天两天的事。”海梓暄看着紫砂杯中浮底的金红色茶叶,淡淡地说。心忖,赐王爵,又建府又封地,其中原委奥妙恐是难测。
海纵天端着,抿了一口,说到:“五弟所言极是,天帝遗训王者六十五后禅位,是以泽辈后世。储君本是个虚称,就算是其他先朝的太子之位,也不是说废就废。”其实,他也知道自己有时在朝堂难免地锋芒太露,手里又掌着一部分兵权,始终是犯着帝爷的忌讳。他们自觉宝刀未老,还有十多年的威慑天下,而他……
“为人臣子理应顺诏,”海梓暄放下茶杯,眼中精光一闪说道:“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
海纵天看了他一眼,心里也是认同,缓缓地说:“估摸着,这两天定会颁旨,到时可就有一阵忙活。”顿了顿又说:“缮奇怕是现在已经出了帝都外界。想不到六弟这次是动了真格,看他平日里嘻嘻哈哈,心里还是有章法的。”
一晃眼,皇弟们都长大了,为这事,虽然被父帝责斥了一顿,但也算有点安慰。海梓暄清俊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却突然,蹙了下眉说道:“只怕霄族的麻烦是结大了。三哥,还没她的消息吗?”
想不到有人的情报能比他精心载培的“蜂髓”还快,在迷楼十几米的地方就把人劫走,担心之余,不得不派魏重拿着令牌去了逸风观。
“是啊,小官这次可是唐突地厉害……”海纵天黑眸掠过一丝冰凉,默默摇了下头,“也不比寻常,怕是碰到她,心里难免把持不好。”又低叹一声,妙计啊,一箭双雕。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各怀心事,执着茶杯慢慢喝了起来……
正如皇子们所料。此时,乌博明已端坐在迷楼的正厅上,一脸黑沉地看着官广威,问他要人。
“乌兄今日大驾光临,官某有失远迎,怠慢啊。”
乌博明“哼”了一声,人坐地笔直,双手扶着黑柚木的宽椅扶柄,也不答话,只是一双眼睛凌厉地望着他,泛着摄人的寒光。
官广威被他看得心虚地厉害,知道来者不善,何况是自家理亏,只好谦声说:“乌兄,事已至此,在下也不便隐瞒什么。令千金确实来过本庄,前日里,在下已经安排马车和随从送回族内。”
“官广威,我且不问你无端带了小女来此是何原因。你口口声声说已经送走,我和禽族的五百多个侍卫,一路寻过来,可是半个影子都没照见。”
听得乌博明语气森然,面露薄怒,官广威额头有点小汗,心里也是急得热腾腾。让他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现在是进退两难,说道歉也是甚无意义,“乌兄,本来是一场误会啊。犬子在帝都就得缘结识了令千金,邀来我府相叙数日。两人相谈甚欢,公主又颇喜欢我们庄子,所以停留了几日。如今犬子为了打理族内事务出了远门,当日也命人送了令千金回去。我官某跟乌兄结识三十余载,乌兄应知我为人,若有半句打诨听凭处置。”
“小女虽顽皮,但绝不会无故跟个刚认识的男子回府。况且,她早受了潼文宫的浩命,怎会行事如此不分轻重?官广威,我不想听你多啰嗦,人是在你家不见的,你们肯定脱不了干系。”乌博明见他还在辩解,却是半字不提女儿的行踪,心里又是焦急又是恼怒。“今天若是不交人,休怪我不客气!”
话音一落下,“哗喇喇……”的声响,禽族在庄里头的几十个侍卫已经把前厅和大门口团团围住。马上,又是一阵“哗......”的声响,霄族的侍卫们见状,也纷纷拔刀站到前头对阵。
大家都执着武器,纷纷怒目相对,整个厅堂里剑拔弩张,如同装满火药的大桶,极有一触即爆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