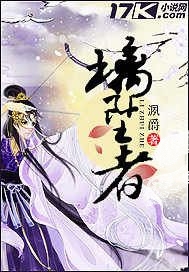乌向云被他拉着不好一下摔脱,只有硬着头皮死撑。但见里头走出八个身穿浅蓝色雪纺璀丝百褶裙的丫头,中间领头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者,几步过来对着他们,分两边排开,长身一跪,大声禀道:“拜见少宗主,恭迎少宗主回庄。”
她看这排场,心里暗暗叫苦,如此一来,更是半点逃跑的机会都没。官之明挥了挥手,示意他们起来,让那两个先头赶车的壮汉带头,拉着她一起走进去。
过了一堵萧墙,和怪石林立,兰草葱郁的前庭,他们来到前厅堂。“钟伯,让厨房在郦水亭摆上一桌好酒好菜,我要招待客人。”官之明刚站定,就对老者吩咐着。又转头令着一个蓝衫的丫头,“带西兄去追月阁好好歇息整理,坐了三个多时辰的马车想来是累了。”
“我……”乌向云刚想说不累,见到官之明清亮的双眸温和地看着自己,充满了真挚和关心,心里一抖,就把后头的话都咽了回去,乖乖地跟着丫头走进去。
看她的背影远了去,官之明的瞳孔收缩着泛起几道冷光,俊美的脸上极是阴冷,哪还有刚才的半点柔顺和女态。唤了声莽阳,狠狠地说:“找个漆夜的人,过几天放个消息出去,就说绚兮公主身陷魔狼谷。”
“这……少宗主,此人身份特殊,事关重大,要不要等老宗主回来商量下?”莽阳看着他,眼里有几分迟疑。这个主子是年少得志,武功了得,只是待人太不亲厚,野心也实在太大了点。他们虽是天宇数一数二的大宗族,可禽族却是都惹不起,更别说高高在上的潼文宫。
官之明一举手,打住了他,说到:“我自有分寸。”说完,喝令另一个跟从,“把这庄子守严实,费劲心机弄回来的,可不能让她轻易跑了。”
乌向云跟着丫头穿过几个回廊,来到一个临水小院,里头青柳摇曳,花香鸟语,钟石奇丽,水榭小阁横梁两重门楣都刷成暄红色。屋子里满地铺着青白玉石,正厅里头摆着一套酸枝木的雕花八仙桌椅,墙上挂着泼墨山水画和一管横笛,色差分明,装点适中,十分洁净怡雅。
“西公子,可要沐浴更衣?”那个丫头轻声问道,很是恭敬。
乌向云一路走,一路都在记路线,思忖着怎么逃出去,哪有心情休息更衣,摆着手说:“不用。”想起刚才官之明说还要跟她一起用膳,又问:“你知道郦水亭在哪里?”
丫头笑了笑回答:“回公子,就隔着追月阁,跨过一个院落。晚些奴婢会带公子过去的。”说完屈膝行了个礼,退守到门外。
官之明看起来只是一个谦谦君子,喜好男风,一想跟自己相交。看他并不打算使强,用完膳饭后,应该有机会出去。她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把整件事情想了一遍,心有忐忑,却找不出破绽。
过了小半个时辰,正觉得有点乏。那个蓝衫丫头走了进来,说到:“西公子,晚膳已经准备好,这就带你过去吧。”她振作了下精神,跟了出去,倒要看看官之明打算怎么招待她。
郦水亭是个湖心亭,一面沿着小径挑出入水,三面朝着湖,深蓝色的八角顶柱,撑着明黄色宝塔盖,上头还描着白凤红雀的,还挺有逸趣。亭里已经摆上了八盘头菜,两只浅青色酒樽,斟着水酒。
乌向云看了皱皱眉头,这人怎么又忘了我不喝酒啊,看到站在亭中的男子面水而立,颇有几分临江仙的飘逸味道,勉强地挤出了点笑容说到:“官兄,太客气了。取了药我得回去,何必如此烦劳。”
官之明转过身,爽快一笑说道:“西兄,今日天色已晚,赶路也颇有不变。不如用过酒菜,就在阁内歇息,明日上路也无不迟。”
话到此时,她已觉事情有异,再看一眼亭中的那个男子,神清气朗的样子跟先前颇有不同,感到自己好像跌进一个圈套。定了定神,说道:“官兄,这般盛情,在下心领了,家里老师还在等候,就此告辞。”说完就转身,迈开步子。
“你以为还走得了吗!”背后传来阴冷的声音。
果然摊牌了。乌向云心里一沉,慢慢转过身,面无表情地问道:“少宗主,是怎么看出来的?”
官之明一脸神秘地走前几步,来到她身侧,伸出手揪起衣领,缓缓说道:“潼文宫皇子们的衣衫,都是由江宁府上等的小登高云锦所制,且都在领口低处都用金丝线绣着三片祥云纹,别人不知道是因为没有机会穿,你不知道是因为才刚刚回天宇。”
“所以你打第一眼开始,就已经知道我是谁?”还是根本就是打我出城就盯上了,失败啊,原来从头到尾都是在被人耍。
“是啊!而且我还特地摸了你腕上的月翅印痕,实在是确凿无疑。”官之明逼视着她,眼神却是象在欣赏一头逮到的猎物。
“那又何必大费周章呢,直接把我点倒,掳了来就是。”乌向云瞪着他,一肚子的火。
“能请到你来,是我此行去帝都最大的收获啊。绚兮公主!多少人盯着呢,怎能如此贸然行事。况且,万一你闹腾起来,难保会有什么族、什么人跳出来救你。”他定定地看着她,眼里的精光象要把她吞吃掉,“我们可是绕了多少路,小心翼翼地才把你弄到这里。”
原来如此。一路上,在车里气定神闲地跟我瞎胡侃的时候,外头那两个人正在天宇的大地上拼命绕圈圈。什么孕妇、女态、草药搞到她一惊一乍的,看来都是为了骗她故意安排的。还真以为自己是个好演员,其实人家才是一个超级影帝。
“什么目的?说吧。”她冷然地看着他,这个狡猾的男人,算是领教了江湖的尔虞我诈。
官之明笑了笑,竟然有几许快意,轻声说:“其实,也只是想让你在这,陪我清静地住几日而已。”
听起来好随意,但是打死她也不会信。况且,住几日?这种事情可大可小,乌向云已经失去揣测他含义的耐心,只看着他,直白地问道:“这是怎么个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