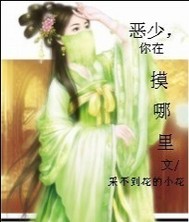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三万骑兵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朝凉州城进发了。而这一切,都在新唐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进行着。
雁门关内,剩下的十万大军各司其职,守城的守城,操练的操练,粮草也几乎把原来的粮仓给挤爆了。在城内百姓看来,回鹘人打算在雁门关长期驻扎下去,与新唐进行持久战。
另一处,由拜索率领,苏挽言坐阵的三万精兵在破晓时分终于来到了古浪峡。古浪峡被称为“金关银锁”,最窄处宽仅数米。狭长的走廊,峭壁千仞,势若蜂腰,中有小道,蜿蜒西窜。只要派几十人驻守在高处,就可以扼住整个通道。
幸好此时,新唐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雁门关,凉州又在另一侧,想来凉州的守将对凉州的地理优势信心十足,断想不到苏挽言他们会兵行险招。
寅时是日与夜交替之际,是人的警惕性最松弛的时候,这也是苏挽言强调一定要在寅时到达古浪峡,然后在守卫军士还在做美梦的时候穿过峡谷。一旦引起什么风吹草动,那么,他们就唯有死路一条,而旁边的悬崖便是三万人最好的墓穴。
好在,这三万士兵都是雅格身边的近卫军,可谓训练有素,在穿越峡谷的半个时辰里,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甚至连呼吸声都是一致的。
到达凉州城外时,正好是天光大亮的时候,苏挽言派了两人分前后回去给雅格报信,以便随时准备后援。剩下的人,便在城外驻扎了起来。
凉州城内,守将陈野还在卧室里与刚掳来的小妾翻云覆雨,便听见门外有人大声呼喊,紧接着门便被踢开了。
陈野正在兴头上,况且年轻气盛,被人搅了好事,自然一肚子火,也不管来人是谁,劈头盖脸便是一顿怒骂,“找死啊!连本将军的卧房也该闯,来人,给我拉出去砍了。”
闯进来的乃是守城的一个无名小兵,见陈野横眉竖眼的样子顿时一慌,连自己是为什么来的也忘了。站在门口抖抖嗦嗦了半天,却吐不出半个字。
等到肩膀被人架起时,那小兵才哇地一声大喊道:“将军,事不好了,城外出现了一大批回鹘兵。”
“什么?你怎么不早说。” 陈野一听,只觉大事不妙,气得抬腿便给了小兵一脚。匆匆披甲带胄,吆喝着一干心腹手下往城门跑。
凉州地势险要,鲜少被人攻破过,所以守城的将士与预备役兵加起来也不过四五万人。本来只要守城也已足够,但人都有好逸恶劳的天性,凉州自新唐建朝以来,一直都是太平安定,所以久而久之,里面的将士也都放弃了操练,纵情声色。而会派李野这个不过二十年纪的毛头小子驻守一座边关要镇,也是因为这个道理。
刚一登上城楼,陈野只觉眼前密密麻麻的都是人头。听到探子回报回鹘只派了三万骑兵来攻时,顿时信心大增,跃跃欲试。他在凉州待的闷出了一身腥臊,早已期待你能有一场战争,能帮助他建功立业,好平步青云,离开这个破地方。
还不等双方将领通报,陈野便命人打开城门,杀将了出去。
此时此刻,苏挽言正骑在一匹黑色的骏马上,从头到脚都裹着一块黑色的轻纱,这样的目的自然是避免自己的形象太过招摇。她正在马上眺望凉州城内的光景,忽然就看到城门被打开了,一青年将领遥遥领先身后的士兵朝己方冲来。
拜索在见状,一勒缰绳,来到苏挽言身侧,声若洪钟,“军师,敌将好像比我们快了一步。”
“此人有勇无谋,不足为惧。”苏挽言冷哼一声,继而道:“拜索听令。”
“末将在。”拜索翻身下马,拱手恭敬地道。
“擒贼先擒王,待他进入我方五十米内,我命你一人迎战,务必取下他的首级。”说完,苏挽言便将虎符掷到拜索手中。而她自己,已经悠闲地骑着马跑到了远处观战。
本来她认为此战有一定的危险性,她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才会不顾雅格的反对,执意要与拜索同行,一旦失败,便以死谢罪。可她没想到新唐居然会放任一个如此冲动的人来驻守这么重要的军事重镇,不可不谓天助她也。李修,没想到你也会有如此大意的时候。耳边听着回鹘兵士的欢声呐喊,苏挽言蓦地扬起了唇角,朝着南方的天空绽放了一抹恣意的笑容。
此战,胜负已定。她不由得松了口气,与雅格签订的协议终于可以划下休止符。她终是不喜欢与日月同眠,黑白颠倒的生活,该结束了……
可是,当夜幕降临,她站在高高的城楼之上,眺望苍穹星际时,她又开始迷惘了。
风瑟瑟兮,野茫茫。寂寥的夜空下,她清清楚楚的看见,银白色的发丝在月光下诡异的飞舞着。她伸手抓了一把银光放在手里,片刻,那淡若樱瓣的双唇之间荡出一抹冷笑。
经年已过,既然他没死,为何迟迟不肯来寻找自己。难道真的是香印成灰,只做得永世枯骨?
泪眼问月月不语,觉来已是相思蚀骨。到如今,现在这模样,恐怕已无人敢窥见。
本来还奢望有他相陪,时光匆匆,可见他也要弃她而去。再无人陪她一生一世。
何时,她变得如此多愁善感?何时,她变得如此自卑怯弱。当真是风光不再,人言可畏吗?
月光皎洁如镜,映得苏挽言整个人如同一片白色的飞絮般,飘飘摇摇仿佛随时将会随风飞去。
你为我,散尽繁华;我因你,苍颜白发。算来也是一干二净了。衣袖抖了抖,一串碧绿的翡翠念珠落在苏挽言的手上。脸上的泪迹未干,她咬着苍白的唇,手才刚用力,便又颓然的松了开来。
末了,她还是放不开他。哪怕他真的选择远离她。付出了感情就像东流的水,回不来了。看着那抹碧绿,她眼中的泪又开始扑簌簌地往下落。
褪去了所有的锋芒,苏挽言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女子罢了。
而在苏挽言落泪的同时,长安通往代州的官道上,苏瑾正一脸惆怅的坐在马车里,在他身旁,是早已哭的不省人事的乔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