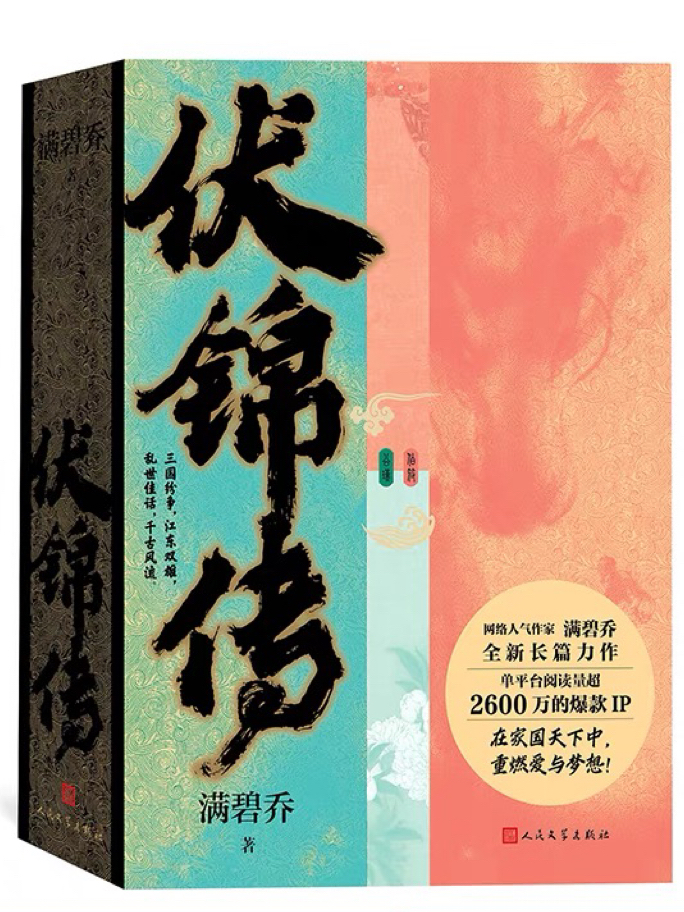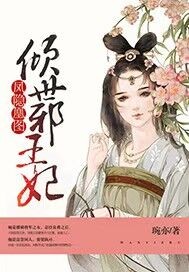冰冷月色,泄了一地光阴,空旷天际,云层漂浮,时而遮盖,可瞧见星辰点点,从窗口望去,一排红色灯笼挂在长廊上,随着风的涌动,摇摆不停,再远点,又隐没在无穷的暗处
窗台边放着一把藤椅,苏若离半眯着眼坐着,随着藤椅上下晃动,沉静的脸被烛火照的半明半暗,似乎隔绝了周围的空气般,只在自己一人的世界中。忽然,双手扣住藤椅的把手,就这么停顿下来,身体慢慢坐直,原本散在肩后的长发顺势滑落在脸颊两边,盖住了脸,长睫半合,瞧不见此刻神情。
一抹明黄色映入视线,沉默的气氛环绕在两人之间,良久,其中一人终是打破了这诡秘的气氛:“没有话对朕说?”
苏若离抬头,一双星眸在火光下黝黑深沉,以坐着的姿势仰望,淡笑道:“父皇想听什么?”
“你是朕最宠爱的一个女儿,离儿,你太让朕心寒了。”威严的帝王,难得露出这般带着疲倦的声音:“朕不愿意相信,一向善良仁慈的孩子居然做出这种事情,朕想听你一个解释,告诉朕,这件事不是你做的。”
缓缓的站起来,失去重力的藤椅独自晃动,上下摇摆个不停,苍白的脸上带着倨傲,还有一种模糊难辨的决然,忽然,整个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我做的,父皇降罪给我吧。”
“为什么,你。。。”
“既然父皇无法为母妃讨回公道,那么,只能用我自己的方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你就相信一个宫女的话,况且,那个宫女已经畏罪自尽了。”
嘴角含着冷笑,仰头道:“馨儿是为什么死的,父皇比谁都清楚,不是吗?”眼睛的寒光逼视,令皇帝也一震,不由自主的往后一退,苏若离继续说道:“自小时候起,我最敬仰的人便是父皇,在我心里,我的父皇是高大、威严又慈爱的,他忧天下之忧,想百姓之苦,明是非,处事公正,”陷入回忆中,眼神渐渐柔和,忽而,神情一转,控诉般说道:“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父皇突然不见了,我的母妃是被人陷害的,而那两个人是谁,父皇难道不清楚?还是,父皇存心包庇,让凶手逍遥法外。”终于查了个水落石出,原来那两人想借用宸妃的手害死兰妃,再让皇帝惩治宸妃,来个一举两得。
仰天长叹,沧桑的容颜浮上无奈:“有些事情,你不懂。”这天下的事如何这般简单,他自然知道敬妃与淑妃是主谋,可是,若轻易判罪,这两人背后的家族势力联合起来造反,势必会天下大乱,叹息道“皇帝也往往有无奈之举。”
“恐怕是父皇在温柔乡待得久了,欲令智昏了吧。”
手掌挥出,在接近脸庞时停顿住,那是一张毫无惧意的脸,平静的目光直视过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淡然,五指合掌握起,脸上布满怒意的皇帝呵斥道:“你怎么变的这样。”
撇过头,咬唇道:“父皇降罪吧,我无话可说。”
“你以为朕不会处置你吗,你就拿着朕的宠爱来无所欲为?”
“儿臣不敢。”
“不敢,你还有什么不敢做的,”颓然在旁边的椅子坐下,一向威严的肩都似胯了下来,这一场变故,就算皇帝如他也万万料不及。看着不远处跪着的女儿,悲戚道:“离儿,这一次,朕无法再放任你的任性了。”黑色的眸子蒙了一层水渍,慢慢的往外走,脚上像拖了千金般重,身为皇帝,也有莫可奈何的时候。
“儿臣。。。明白。”苏若离低声应道,死灰般的面色沉静如水,眼中又含了深深的歉意,一滴清泪,还不了生养之恩,只望来世再报。转头看向桌案放置的酒杯,从地上爬起来,慢慢踏步过去,伸手拿起,一仰头,饮尽。
这所有的爱恨情仇,便这般离去,再不会固执,再没有痛楚。若离若离,情非得已;若寒若寒,焉能相守;天道道,然无情;人渺渺,何安生;一抹香魂,无所依。
热闹的街道上人来人往,香粉味夹着隔壁卖煎饼的炭灰味,还有路边乞丐的馊味,倒也形成一幅和谐画面。然而这般热闹的景象中,有一个白色身影分外扎眼,总觉得不搭调。就像是一堆玫瑰里混了一支百合,一群鸡鸭里来了一只山猫,很突兀。
一个壮汉的喊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快去看啊,孟家那边有好戏。”
其中一个疑惑道:“孟家?不就是今天娶媳妇的那家吗?”
壮汉回道:“对啊,你说稀不稀奇,只听过抢新娘的,还第一次听见有人抢新郎。”
先前提问的那个笑道:“这有啥稀奇,如今的小姑娘可厉害着。”
那个壮汉又回道:“奇就奇在抢新郎的也是个男的。”
众人哗然,惊讶道:“这事情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还不快去,迟了就没戏看了。”
忽然一阵风卷过般,所有人全拥着往那边跑去了。走在路中间的白衣女子往人群拥挤处看了一眼,马声嘶叫,一抹暗青色与红影交加一同往这边袭来,白衣女子反应倒也快,连忙往路边一闪,虽是避过了疯狂奔走的马匹,却也因这一阵狂放吹起面上白纱,却原来是早被毒酒赐死的苏若离。
原来那日刚饮下毒酒,便被闻声赶来的宸妃和曼妃救下,这皇宫里是没法待了,更何况苏若离已厌倦了那般生活,第二日,消息放出来,公主突染病身亡,实则是,苏若离在暗地里已偷偷的出了宫。
看着眨眼间已奔至远处的白马,无波眼神起了一阵波澜,隐隐透露出一种羡慕,原来感情可以这样简单,因为相爱而在一起,就算受尽世人唾骂,心甘情愿,只因身边那个人,是自己付出生命想拥抱的。
转身要走,脚步顿时停留,十尺开外,一袭青衫,眉角额头沾染了细雨,长睫上头挂着小小的水珠,原来已开始下雨,她竟未感分毫。很短暂的停顿,然后,踏出一步,慢慢的,如优雅的散步,如此漫不经心般走到那男子的前面,再擦身而过,居然不再停下一刻。
一个错身时,听到熟悉的温润声音喊道:“离儿。”
身子一僵,仍是往前继续走着,直到手臂被猛然拽住,垂下头,细雨中有微风鼓动,轻柔的面纱飘动着,低声道:“公子认错人了。”
“离儿,我来找你了。”
抬头,陌生的目光令夏似风一时呆愣住,只听得同目光般清冷的嗓音重复道:“公子认错人了。”轻轻的一甩手,挣脱了出来,对面而立,明明靠的很近,可夏似风总觉得两人无形间被拉的很远。
放手让她离去,残留在手中的余温渐渐变淡,手掌渐渐合拢,这一次,该是换他来固执一回。
白马终于跑的倦了,停在一处茅草房边上,木栅栏围起来的房门松垮垮的合着,轻轻一推就打开了,黑衣男子先跳下,回头道:“去讨口水喝,再赶路吧。”红衣男子微笑颔首,一双黑眸柔情似水。院中一个男人正赤着上半身砍柴火,瞧见有人进来,停下了手中活计,取了边上衣服披上,黑眸弯起,笑道:“有什么事?”
黑衣男子抱拳,尴尬的说道:“我们想讨口水喝。”看来打小是没有问人家讨东西的习惯,这句话说的分外生涩。
男人却不甚在意的笑道:“来,进门就是客,你们坐着,我给你们打水去。”
“谁来了?”清脆的女音自屋内传来,话说完,已经出现在大家视线中,清冷的面容似乎总是把人隔绝在几尺开外,但仔细看,又发现一双眼睛中透着一丝柔情。
男人笑笑,回头道:“两个过路的客人,我去给他们倒两碗水,你招待一下。”
女人看了看自家院中的两个男人,目光扫去,令原地站着的人都觉得有点不自在,仿若什么都被看透了。却见她半垂眼睑,淡道:“两位请坐。”
两人还未有动作,忽然一声惊呼自院旁的大树上传来,眼前一闪,再看时,原本进去的男人又出现在面前,手中还抱了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娃娃。虽然才逃脱坠下来的危险,此刻咧着嘴却笑得很甜,似乎早就知道有人会接住。
“然儿又调皮了。”男人嘿嘿一笑,把小娃儿放在地上。被唤然儿的丫头拉扯着她爹的衣角,不依道:“然儿要飞的高高的,爹爹带然儿从上面再飞一次。”
这般可爱的孩子,连两个无端闯入的人都被逗的扬起微笑,正当男人无奈点头时,一个清冷的声音道:“然儿,进房去抄三字经一百遍。”
原本吵嚷的小娃儿苦皱了一张小脸,转头哀求,尾音拖的长长的叫唤道:“娘。。。”
“两百遍。”
小小的身影转头往里面走去,男人不忍心的说道:“雪儿,这然儿还小,别这么认真。”
“养不教,父之过。”说着,径自往内走,去端半天没端出来的茶水。
男人摸摸鼻子,苦笑的对着旁边的两个男子说道:“让你们见笑了。”
红衣男子叹道:“我觉得你们很幸福。”
黑衣男子伸手将他的手握在掌心,对视一笑,男人聪明的转头叫道:“雪儿,这种粗活还是我来做吧。”
不知何时,绵绵细雨落个不停,洒在茅草屋顶,洒在院中的石桌上,也洒在院中两个执手相对的人上。
细雨三四月,无意中踏入一片梨园,雨中的梨花娇嫩开放,花瓣纷纷扬扬的落下,但是,看着满枝头的花,总觉得再怎么样也落不完似的。这一场花雨,下的这般绚烂,连心口都被填满。
模模糊糊的音律透过斜风细雨传来,脚步不由自主的走过去,长亭外,梨花树下,白影独立,亭内一人独奏,垂头拨弦,恍然沉浸在两个世界。然而,两人忽然对视一笑,坦然又安宁的笑,如当日初见般,抬手拂去她肩头花瓣,柔声道:“这一曲,便是那日送你的。”什么也没问,似乎昨日才分开,今日又见面了的家常闲话般。
苏若离笑答:“可惜只听了一半。”
“我再弹给你听。”
苏若离想道,和这个人相处最是舒适,就算万般情愁,也忽然就消了。再想起另一个男人,再见面,哪里真如表面般平静,以为不在乎,可以坦然相对的,怎么心就不像长在自己身上一般,随着跳远了。
音停,笑言:“人活的太累的原因就是想的太多,为何不跟着心走。”
茫然抬头:“跟着心走。。么?”
温颜点头,指尖挑过弦,垂头掩去眼中一闪而过的落寞,软声道:“就如这琴,若是无心之人,弹出来的曲也是没有灵魂的。”
亭内亭外,不过几步台阶,然一层雨幕,隔开了两个空间,亭外的人抬头嫣然一笑,却是往梨花更深处走去。亭内的人抬头凝视,呆然片刻,复抬手起弦,仿佛一切未曾发生过。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