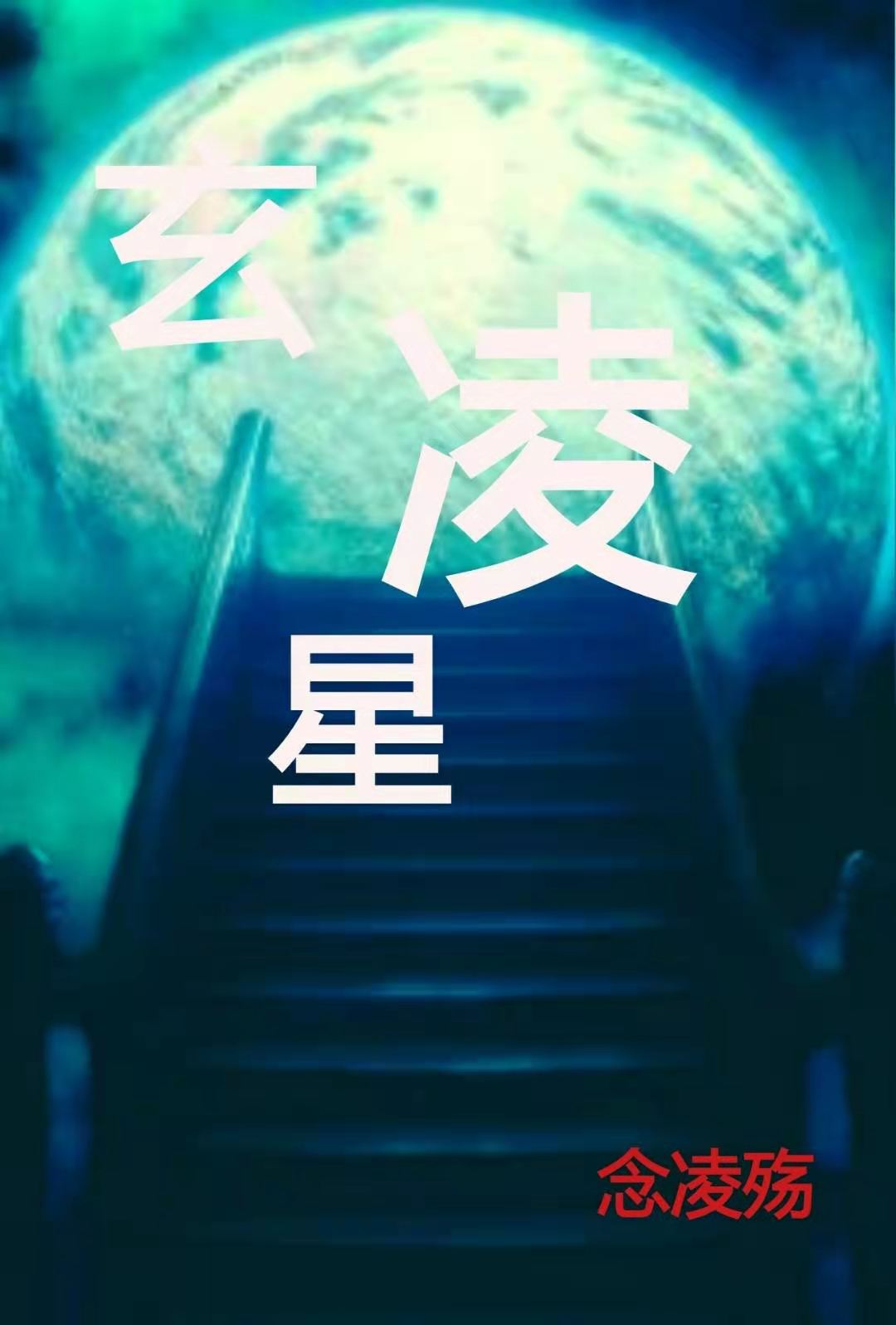爸爸抽了一张纸,递给白乐天,直了直身子,缓缓地说道:
“农村没有挣钱的门路,为了挣钱,男人都出外打工。九二年的春天,我和王洪亮结伴,来到了成都,找了一份建筑工地上的活。”
“成都?”
“嗯,我们是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去的。那时的成都高楼大厦不多,马路也不像现在的那么宽,路边到处是卖麻辣烫的小摊,当然茶摊也很多,还有掏耳朵的手艺人,挑着担子的商贩,沿街叫卖的声音,就像唱着曲儿一样。”
爸爸抿了口水,接着说,“工地在人民南路三段附近,王洪亮做泥瓦工,我做木匠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四月十八日,整个白天都是飘着细雨,雨雾蒙蒙的。下午收工时,小雨逐渐停了,街道上湿漉漉的,我和王洪亮到小天竺街,要了份川味面,喝了杯白酒,然后沿着锦江岸边闲逛,这是我们消磨时间的最好方式。”
爸爸停下来,看了一眼白乐天,又看看窗外。
“晚上十点多,我们边走边聊,快要走到九眼桥位置时,一个身穿黑色上衣,戴着同色口罩的男人,跌跌撞撞地从身后跑过去。在昏黄的街灯下,他跑得很着急,差点撞到我们身上,一个趔趄斜着身子跑了,王洪亮还小声骂了一句‘着急去死啊’,那人并没理会,继续往前跑。”
“那人是谁?”白乐天小声问道。
爸爸没有回答,继续讲道:
“过了没两分钟,黑衣男子转身又跑回来了,站在我们面前。他的眼睛瞪得很大,对着我们大声嘟哝着,喘着粗气,双手不停比划着,可是我们一句也没听懂。他说的好像是少数名族的语言,这也正常,成都的街头常常有许多少数民族的人。我仔细一看,吓了一跳,发现他袖子里有一股鲜血流出来,流到了手背上,顺着手指滴在了地上,一会儿就染红了地面,显然他受伤了。他的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婴儿外面包着小棉被,用灰色的棉带紧紧缠绕在上身。正在我们疑惑间,他突然解开身上的带子,将婴儿放在我的手上,再次跌跌撞撞地往前跑掉了。”
“那孩子就是我?”
“是的。我抱着孩子,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还是王洪亮出门多,见多识广,他忙把我拉到河边,远离那条路。不过十分钟,十几个身穿藏青色衣服的男子急匆匆跑过去,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尖刀,显然是去追刚才跑掉的男子。好在孩子在熟睡中,没被这些人发现。我又等了半个小时,那人还没有回来,我们只好沿着河边的小路,返回到工地。”
“我一个大老爷们,不会带孩子啊,正好工地上有一个做饭的大嫂,我就拜托她帮忙照顾这个孩子---也就是你喽。”
“后来呢?”白乐天问道。
“后来,我和洪亮抱着你,也去过九眼桥附近,但是没有人来找孩子,我们也很留意报纸和墙上贴的小卡片,都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后来,就把你抱回家了。”妈妈插话道。
“嗯,就像你妈说的那样。我们是外地人,交给政府又怕说不清楚,实在没办法,王洪亮说我和你妈结婚五年没有孩子,说不定你就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干脆就带家去吧。我想想只有这样了,辞去木匠活,带着你坐火车回到了汉东省。”
“是啊,绝对的福星!你到我们家后,很快就添了弟弟妹妹,你爷爷奶奶多稀罕你不。”妈妈自豪地说道。
“难道我不是汉族?”白乐天自言自语道,“少数民族的语言。”
“我不知道,这就是你的来历。你长大了,你会弄清楚的,我们没有文化,帮不上你了,儿子。”
“有没有线索帮助我,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也没啥东西啊,小孩的衣服旧了,穿烂了,被我们扔掉了。奥,对了,还有个棉麻的包被,一个小孩的玩具。”妈妈答道。
“在哪儿放着呢?我想看一下。”白乐天问道。
“藏在我陪嫁来的柜子了,就是那个漆成深红色、放在墙角的那个柜子。”妈妈接着说道。
“我能看看吗?”白乐天看着他俩问道。
“当然行,这本来都是你的东西。”爸爸答道,“以后,你也不能忘了我们啊。”
“怎么会呢,你们永远是我的亲爹娘,我会给你们养老送终的。”白乐天点点头说道。
“等你工作不忙时,有机会的话,你还是去找找亲生父母吧。”爸爸叹了口气说道。
说到工作,白乐天又想起了风教授的案子,说道:“差点忙昏了头,寻亲的事以后再说吧,确实工作上还有些棘手的事需要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