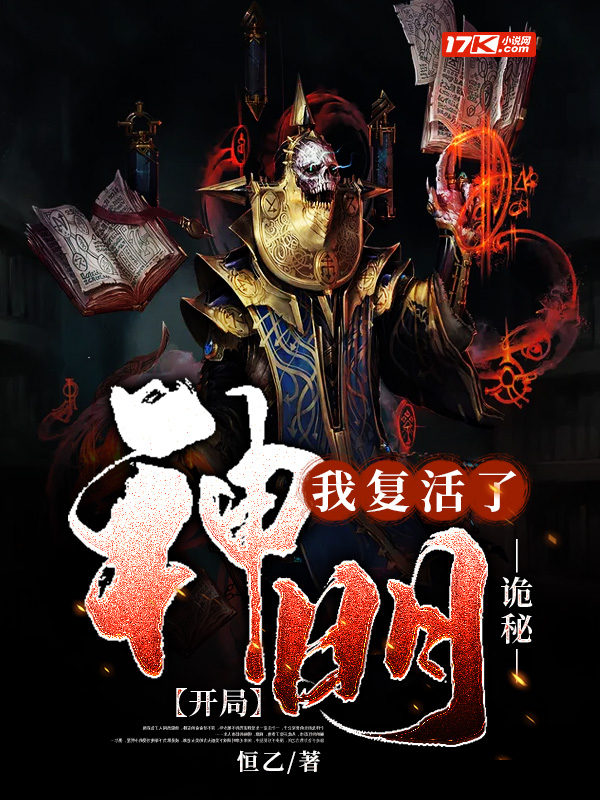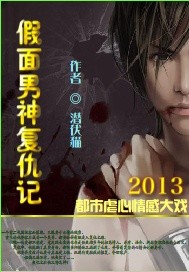如斯从泠泠苑回到松临阁时四处找遍都没有找到三公子的踪影。问青松银松,两个人都是一脸茫然摇头说不知,只知公子去与福相说要搬出府的事情没有带上他们。这一去便去了一个时辰,也没有见公子回来。
如斯一听,心中便知福相肯定没有答应三公子的请求。她跺了跺脚,朝福相所在的前厅而去。
出了拱门便是松林,如斯奔跑着不经意的一回头,看见那葱郁非常的松林,心中一动。她停下脚步朝松林深处走去。
三公子果然在松林里,虽是春天他却仍旧披着冬天才穿的白色貂裘。他背对着如斯,对着一棵松树手里拿着小刀不知在刻画些什么。
“公子!”如斯喊了一声。
三公子回过头朝如斯一笑,大概是被这林中寒气浸久了,脸色白的发青。他将小刀放入随身的小布囊里,朝如斯走了过来。
“你在刻什么?”如斯说着还作势朝三公子身后张望。
三公子按住如斯的肩膀,笑说道:“现在不要看,以后再看。”
“反正都是要看的,还在乎什么现今以后啊!”如斯虽然是这样说,却依旧听话的随三公子向林外走去。
如斯伸手握了握三公子的手,发现他的手冰冷如铁,于是便执起放在唇边呵气揉搓起来。三公子笑看着如斯的动作,沉默不语,那一双清亮的黑眸里盛满了笑意,只是那满满的笑意中又带着一丝让人不易察觉的波澜。
“是不是老爷拒绝了公子的请求?”如斯问。
三公子点了点头,低声说道:“母亲怪我,才回来不到一个月就想要搬出去。父亲亦说我不孝,惹母亲伤心。”
“不搬出去就不搬出去喽!”如斯歪着头笑看着三公子,说道:“只要公子还能每日教我就行了。”
三公子笑看着如斯,点了点头,又似突然想起什么,对如斯说道:“你去把房里的那架琴抱来,我教你弹琴。”
如斯欢快的应了一声,朝松临阁内奔去。三公子扶着身边的一颗松树,捂住胸口咳了两声,尽力抚平自己的气息。
他只觉得冷,全身都冷。胸口下的部位很疼,牵拉着胸口也变得十分疼痛。他举起双手一看,手指尖泛着一股不正常的青色,看上去十分骇人。他努力的搓着手,直到双手恢复了正常的颜色,而此时如斯也抱琴而来。
如斯先铺了一层软席,又在软席上铺了一层厚厚的虎皮,然后才让三公子坐在软垫上,将琴递了过去。
三公子笑看着如斯忙碌,乖乖的坐在软垫上接过琴,对如斯道:“这琴名为焦桐,乃用烧焦的桐木所做,是父亲的故人相送。‘焦桐弹罢丝自绝,漠漠暗魂愁夜月’,焦桐琴音清透绝美,弹之可绕梁三日不绝。”
三公子说罢,十指放于琴面,铮铮拨弹。
琴音清冽而古朴,仿佛远处的钟声寂寞敲响,又仿佛近处的雨声滴滴清脆。那琴音又如九天之云好像能够触摸却又倏而远去。又如青谷之风挥挥洒洒缠绵壮烈。清冽之中含着一股决绝而悲壮的力量。
如斯托腮倾听,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也跟着琴音飞翔在九天之上。过了许久,当最后一个音符静止之时,如斯依旧没能从自己的想象中回过神来。
三公子侧目看向如斯,微微牵起唇角,静静的笑了。
松林里的凉气一点一点的浸入三公子的身体,肺叶传至胸口的疼痛也越来越浓重。三公子不动声色的捂住胸口,忽然困惑的抬起头看向那密密松叶之外的天空。
为什么出生之时会得如此难治之症?为什么自己活着就是为了等到某一天死去?而那一天,会来的那么早那么早……为什么要在等死的日子里遇见她呢?
三公子垂首看着如斯,胸腔之中的疼带着浓浓的酸,直冲他的喉头。
风儿吹过,如斯才陡然惊醒。她看向三公子,问道:“公子弹得是什么曲子?”
“是柏舟。”三公子淡淡说。
如斯挑眉,雀跃的说道:“我会背柏舟的!”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如斯背完,得意的看着三公子笑道:“公子,我背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一首?”
三公子定定的看着如斯,许久许久,直到如斯不好意思的调转目光,他才抬起手抚着如斯额前乌黑的留海,缓慢而悠长的说道:“你没错,是这首。”
“可这写的是臣子不遇明主,怀才难舒的忧愤之情啊,可公子的曲却仿佛……”如斯歪着头想了好一会儿:“仿佛像是……”
“咱们回屋吧!”三公子说着,将琴抱起站立。
如斯只好跟在他身后用软席将虎皮与软垫一起卷了抱在怀里走出了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