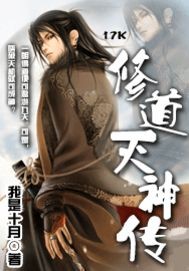季长风醒来,看见熊荆于伏在床前,登时两腿一伸,就要坐起。
熊荆于给他这一番动静闹得醒转,揉了睡眼,说道:“干嘛呢你——起个身这么大动静。”
季长风问说:“我几时回的?”
熊荆于回道:“约摸是巳时罢。”
季长风略一回想,蓦的一个骨碌,从床上滚下来,不及披衣,就要夺门出去。
一恍神,熊荆于已抢在跟前,将他一把拦住。
“你要去哪?”熊荆于问。
他回道:“临安府衙。我得去接回我师傅的遗体。”说着便要绕开。
熊荆于后退一步,复又挡道:“云中君不可能把尸体给你的。”
季长风道:“那我就偷,就硬抢。不然,等到他们把尸体给太一道全派上下的人看过后,没了利用价值,那华采衣不知会对遗体做什么!”
熊荆于道:“你现今的心境我能体会,可是劳烦你想想,云中君是琉璃轮阶位的高手,起码五阶!你要从他手下拿人,该不该思量妥当些?”
季长风道:“我没得思量了。就我一个人,横竖都是如此。”
熊荆于喝道:“你个二傻子你想什么呢!白潮声那天在招员武会说了啥你不知道么?你是明堂的人!明堂的人!我们都在这儿呢——要做什么,有我们替你商议,你不是一个人!”
季长风顿了一顿,咬唇,咽了两口唾,似在定心,复又说道:“季某——谢谢你们。这点事,不敢再劳烦了。”
熊荆于听了,登时也是发蒙。本以为适才的说辞能作些宽慰,不成想起了反效,不但没叫季长风打消执念,还引他话里生疏,用了“季某”的称谓,拉远了二人的干系。
交往多日,熊荆于只当季长风是个心肠耿直好猜之辈,今日对话却没了默契,始终拿不准他在想些什么。
她素来有一副伶俐的口齿,这当时也没了用处,接答不上,互相面对着,只是呆立。
毕竟是亲友离间、恩师长逝,此时再多的言语,都显得扭捏作态;反是无声相陪,倒许还起些效用。
正相持间,房门忽然开了,进来了白潮声。他见了屋里对立的两人,立时知道是怎么回事,吭吭两声,说道:
“熊姑娘,三娘子那头寻你有些事,你且去看看罢。”
熊荆于点点头,回身在季长风肩上拍了两下,便自去了,走前不忘将门给带上。
一时屋里又是两人,不过错开丈余,各不看对方表情。
久了,白潮声说:“我不会安慰人。”
季长风闻言,深吸了一口气,回道:“这几日,承蒙白公子照顾了。待季某日后得了斤两,再与白公子相还。”
白潮声道:“日后相还?言下之意是??????”
季长风转身,拱拳说道:“对不起,恐怕又要辜负您的美意了。”
白潮声见他如此,倒是意料之外,一个错愕,问道:“眼下境况,你不归依明堂,要到何处去?”
季长风道:“我??????还没想好。应该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罢。闯荡玄门,又不非得要依仗人势。”
白潮声听他这话,蓦的一个开窍。熊荆于死想不通的理,他在霎时间里竟猜了个七八。现今的季长风,定是敏感且多疑的。
这不奇怪。十余年来至亲至信的三个人,师傅,师叔,师弟,或欺瞒,或算计,或离间,或相残——
至亲至信尚且如此,试问再能有什么人能令他信赖?
思及此,白潮声只觉喉头干涩,哽噎难言。作了几声咳,这才通畅了,因说道:
“我这般对你,不是怜悯,不是算计,你——莫要错会我的意思了。”
季长风听了,一时也不知该答些什么,恐开口要支吾,干脆闭了口,不接话。
白潮声见他如此,知是给自己说中了,便直入话锋道: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同情你?我假仁义、滥充德,故意借此来圈养声名,好得个侠心义肠的称誉?”
季长风见他语气急切,忙回嘴道:“不是——季某绝无此意!”
“你就有——”白潮声说着,一步步欺到近前来,“要不然,你就觉得我是在收拢你,好让你感恩戴德,日后为我所用,报复太一道——”
眼见白潮声步步逼近,季长风没得招架,只得步步后退。
嘴上一时也没了回应,两眼惶惶,实在不知白潮声此举的底细。
这当时,白潮声蓦的一个跨步,整个的贴近了。登时两人四目相对,鼻尖相去不足一粒米。
周遭的景致一时都失了真。能看见听见的,只有相互的一对眼,一口气。
“或者说,你怀疑——我在利用你。我想拿你做筹码,或者别的什么,好去跟那云中君一辈做周旋,将你做我摆布的棋子?”
一阵静谧。
窗外有野猫在叫,很凶。咣当一下,屋顶的瓦片跌在了地上。紧随着一个扑棱声起,是只鸟雀,很急的拍着翅子去了。
拍翅声远去,季长风咽了口唾,错开了眼,说:“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