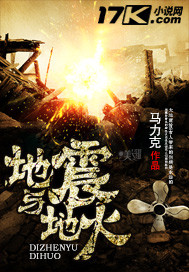花伶侬睁开眼,见了那人,立时就要逃。但她使力不起,才知是在那人的怀里。
本来是相当的冲动,这时候突然就松塌了,隔了四五层布料感受着,好像回到了二十年前的晚上,与他双双栖在床榻里,一并望着星夜叨着过往与将来。
一想之间,她就要落泪。
汤洗澄也是说不出话。他欲唤她的小名,像二十年前那般,却始终叫不出口,毕竟对的是一张老去的脸了。
往后再叙些什么,问可安好么?他心知肚明,定是不好的。
说好久不见么?隔了这么久才重见,说到底也是他的缘故。
那些话出了口都要变味道,因而百般思量,什么也没说。
最终花伶侬还是推开了他,望百丈上的崖顶钉了绣花针,针尾引了根绣线在手里,倏的一下便擎着绣线上去了。
这期间她听着些打斗声,斗得正烈,然而她一眼也不瞧,径直去了。
到了崖顶收罢了针与线,她便听到后面簌簌风鸣,知是有人追赶上来,灵犀一通,她不回头,也知是他,便不再踟蹰,忙放足远去。
这一跑之间,她忆起了在冥间与喜儿的对辞。
“喜儿,把汤给我罢。”
“喝了这个汤,你可就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费了这么大工夫才找回的记忆,你打定主意了么?”
“以前是觉得,那些记忆很重要。等找回来了才知道,其实也没什么的。”
“你就不想知道,他有没有骗你吗?”
“不想。”
“你真的放下了么?若真如此,你又何必还闭着双眼?适才马面已经将你的生卒期辰递交给我,你的卒期未到,分明就是一缕生魂。之所以闭眼,是怕见了阴间风物,难逃生天罢。”
“??????”
“所以,你还想活下去——你放不下。”
“??????”
“??????”
“走罢——你身上有香椿线,循着那线,就可以回到阳间了。还是说??????需要我这个老太婆,来帮你一帮——”
喜儿在她胸前拍了一掌,便将她推回了人间世。这当儿她一面跑,一面忆着喜儿的声喉,扪心自问,真不想知么?
问过了三遍,到底是屈服了,脚下步子一滞,停了下来。
这时才发觉,她已回到了戏水楼,后面一声呼唤,她回头,看见追将上来的那人,登时脚下发虚,恍恍惚惚。
两人面对立着。绣楼锦阁,公子佳人,一下子好似回到了二十多年前,他们刚刚相遇的日子。
“伶侬??????”他出声唤道。
还是那个声喉,硬朗,骨气,是沙场上刀口喷洒出来的热血,流进剔透的琉璃杯里,充满夜晚的温柔。
花伶侬就那样,隔了七八步远的望他。望得久了,好似是隔了千重山水来观这楼阁里的一切,从那云霄上望下来。
一霎里幽深,一霎里明媚,绣球,彩带,雕花门页,红漆木柱子,光光影影,明暗都在她心里,然而触碰不着,只是一段暂且的回忆——
——她残破的人生里不可多得的一点念想。
汤洗澄开口了,他说:“要去哪儿?”
要去哪儿——是啊,去哪儿呢?她走之前,真没想过这一遭。
戏水楼是不可能呆的了,中原的任何一处,她都安身不得,毕竟是仇人的乡土。
回滇南么——早是一摊寂寂的废墟,月下烧了火,一面温着土里埋下的家族陈酒,一面听亡魂唱家乡的谣曲,久了定要发疯。
思来想去,她真不知到哪儿去,登时慌了,哽了,一阵酸楚上来,只是呜呜咽咽的说:“五两,我们回不去了??????”
汤洗澄听她唤他“五两”,立时也是掩袖。
“五两”是花伶侬取的绰号,在青楼初见时,汤洗澄身上只带了五两银子,便扬言要替花伶侬赎身,娶她回家,叫花伶侬出了好大的糗。
后来他真的把她赎走了,用的真只那五两银,自此便成了她与他的戏称。
花伶侬问:“为什么要抹去我的记忆??????”
汤洗澄听了此话,抬起头来看她,郑重的道:“我希望你能好好过。”
好好过——原是这般简单的答案。花伶侬作了声笑,喃喃着,好,好,我知了,知了??????蓦的一个回头,发丝缠飞,就要拂袖而去。
“伶侬——”
一片静默。
“我们从头来过罢??????”
话音落了,迟迟没有回声。汤洗澄立在那里,看着花伶侬的背影,肩膀一抽一抽的上下耸动着,似在啜泣。
久了,终于听见她说:“来不及了,太晚了??????”
他知道是什么。且不说那些个家国羁绊,血海恩仇,他们各自都到了这般光景,凭现如今的心力,还有几年能从头呢。
说那话,本也是为了情分,而今道罢了,倒觉得多余,跟玩笑似的。然而两人是真笑不出来的,心里只是哀楚。
所以他也迟迟没有作释。他与王室的决裂,他冰封此处的守候,他托人抹去她的记忆。正如她所说:回不去了。
他才明白他为何到今只说了一句不痛不痒的玩笑话——他也打心底的衰老了。
“就这样罢。”留下这一句,花伶侬便自拂了袖,望西面去了。汤洗澄没有追。
汤洗澄立在那里,蓦然间好像走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青楼秋水苑。
迎面来了一个鸨母,扭着胯,讪笑着将帕子扇他脸上。她说怎生回事,这些日子才来,罢了便不听争辩,径直将他望那处拉。
坐在屋里的凳上,他听身后一身轻咳,而后便是羞答答的一句:
“你来了。”
汤洗澄回头,看见十八岁的花伶侬。
蓦地里一声响动,他才回来。
绣球,彩带,雕花门页,红漆木柱,寂寂然的,光光影影,明暗都在他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