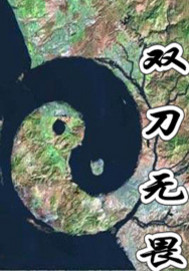“书呆子,你可知这女鬼为何总是每月的下旬才来会你?”她不等楚公子开口,自问自答道:“因为每月月圆之后,世间阴气逐渐转盛,这女鬼才好变化了与你相会,不然若是凭着这副尊容,岂非直接被你扫地出门?”楚公子回忆着半年来与这女鬼种种缠绵欢好的情景,再看看此刻她丑恶的嘴脸,胃里一阵翻腾,弯下腰来狂呕不止。
“楚郎,你说过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子都会喜欢我的,难道都是骗奴家的吗?”女鬼掩面而泣,倒是名副其实的鬼哭,果然凄厉幽怨,闻之战栗。
“你对这位公子也是真有几分情意,本姑娘也就不与你为难了,你现在就乖乖回地府排队报道,好好投胎去吧!”白衣女子素手向女鬼一指,颇有威势。
“什么?女侠竟然要放了她吗?这怎么可以?她一心要害死我,你且给我收了她。”楚公子强忍着胃里的痉挛,尽量不去看那女鬼,口中之言却是冷酷决绝。
女鬼赫然立定:“楚郎,你好狠的心肠。相处至今,我何曾起过半分害你的念头。”
白衣女子转头对楚公子点头道:“她若真有心要害你,你又岂能活到现在。”
楚公子广袖一挥,转换成一副富家公子独有的颐指气使的态度:“我不管,定是我爹爹妈妈请你来为我楚家驱邪除祟的吧!那你就‘收人钱财与人消灾’,给我收了这女鬼!”
白衣女子一听此话,很是鄙夷不悦,正要反唇相讥,却听女鬼幽幽地说道:“楚郎,你当真不记得我了吗?去年秋季稻香园的赏菊大会上,我们原是见过的呀!当时你我一见钟情,你说你心中思慕的正是我这样‘明眸善睐,顾盼生姿’的明艳女子,还赠玉佩给我作信物,说今年的秋闱试举一过便上我家来提亲的。呵呵!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玉佩也日日戴着从不离身,从那以后便茶不思饭不想,只求日子能快些过去。可惜天不作美,还没等到今年的秋闱,我父亲便硬是要将我许配给冯太守的三公子,我誓死不从,偷偷地离家出走,想要投奔于你,不幸路上却被强人所掳,为保贞洁我只有投湖自尽……即便是化而成鬼,丑陋不堪,我也依然不肯负了与你的约定,宁愿错过好几次投胎转世的机会也要来见你,楚郎,我……”
“住口。”楚公子不耐烦地打断女鬼,“人鬼殊途,无论我曾与你有过怎样的约定,既然你已经死了那便都做不得数,你本该好好投胎才是,何苦又来缠我害我,误我前程?”
“哈哈哈……”女鬼厉声狂笑,惨烈凄恻,“痴心女子负心汉,果然如此,我原不信的,总以为你有些不同,想不到你、你……”周围空气瞬间冷凝,女鬼肿脸上浮现一层青绿,发丝卷曲张扬,犹如水底随波舞动的海藻,血红的唇一张发出一声凄厉的呼号,十指卷曲,指尖如钩,凌厉地朝二人扑来。
白衣女子没料到她会突然发难,一时间慌了手脚,来不及拿法器和结印,只有去拔佩剑凝夷,但拔剑却是她下下之策,要知道凝夷剑是把上古宝剑,且多经炼化,又跟了她这么久,早就有了至高的法力与灵性,一般有道行的妖魔尚且承受不了,更何况是区区一只女鬼。
女鬼似乎有意求死,悠忽一下直往刚刚出鞘的剑身上撞去,凝夷“呜——”的一声剑鸣,碧芒大盛,只听女鬼两声凄绝的惨叫,被那宝剑震得魂飞魄散,分别幻化出三粒赤色和七粒蓝色的星芒,如萤火般在夜空中闪动飞舞。
“糟了。”白衣女子忙从腰袋中掏出一个紫色小玉瓶,口中迅速念动着法诀,一道金光自瓶口飞出,追着半空中的赤蓝星点左奔右窜,终于罩住了一赤一蓝两粒收回了瓶中,剩下的星芒却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白衣女子往瓶中望了望,心中有些怅然道:“这样情深的女鬼,却为了个薄情寡恩的臭男子落得个魂飞魄散的下场,实在是不值得,好在及时保住她一魂一魄,带回去让师父想想办法,他老人家神通广大,慈悲为怀……可是我摇光派并不以聚魂见长,就算是师父也未必能够帮到她,若是让师父他老人家觉得在我这个心爱的弟子面前丢了脸面,岂非是我的罪过?不过,这世上就没有师父搞不定的事情,嘿嘿!”
楚公子见她一会儿蹙眉,一会儿冥想,一会儿又微微含笑,哪里知道她心里这许多计较,于是不耐烦地问道:“女侠,这女鬼可收服了?不会再来纠缠我了吧?”
白衣女子瞪他一眼:“不会了,她永远也不会再来缠着你了。”心道:“臭男人,她这辈子遇上你是她倒了八辈子霉。”
这时,院子里的廊灯全被下人们点燃了,照得一片火红通明,尽除刚才的森森鬼气,楚员外和楚夫人从院外推门进来,迫不及待地奔向他们的宝贝儿子,神情又是欢喜又是担忧。
楚夫人看着儿子薄如纸片的身形和瘦削苍白的脸庞,心疼得几乎哭出来,楚员外则上前来向白衣女子作揖道谢:“多谢多谢。实不相瞒,犬子自被这女鬼缠上,性情大变,喜怒无常,只喜欢把自己关在院子里,谁也不见,谁都不理,我老两口只有眼看着他日渐憔悴,白白地焦急心疼。这半年多下来,前后也不知请了多少位法师,可全都不经事,不是连那女鬼的面都见不着,就是被他一吓掉头就跑,如今终于在道长你的剑下伏诛,真是苍天有眼,怜我楚家,也是道长法力高强,神通广大,解我楚家灭顶之灾。”
白衣女子翻了翻白眼,冷冷道:“别道长道长的叫我,把本姑娘叫得又老又古板。”她平时其实是十分尊老敬贤的,只是因为不喜这寡情薄性的楚公子,连带也不喜他的家人。
楚员外连连点头称是,朝身后的一众家丁招招手,家丁们纷纷端着托盘走上前来,第一个托盘上有白银五百两,其余的托盘上却全是珍奇古玩,灵药补品之类,张员外想这女子既是修仙之人,想来对黄白之物必然看不上眼,是以只准备了白银五百两,而古玩灵药的价值却远在这个数目之上。
可令人极其费解称奇的是,这看似清冷淡泊,不食人间烟火的白衣女子,对那些古玩灵药却是嗤之以鼻,反是看到银两的时候眼中大放异彩:“咳咳,这些古玩姑娘不懂也不喜欢,就不要了吧!灵药补品呢……还是留给令公子补身体吧,银子嘛,我就却之不恭了。”
楚员外愣了愣,突然明白过来,心想:是了,珍奇古玩又怎可与她道家的法宝**相比,说到灵药补品,那更是贻笑大方了,他们可才是炼药的祖宗,如何看得中我这些凡间俗品,相比之下,倒是金银来得简单实在了。当即“呵呵”一笑道:“这区区五百两虽不是什么大数目,携带起来却也不大轻便,老朽另用匣子为姑娘装盛如何?”
白衣女子道:“不必麻烦。”拉开自己的腰袋,向袋口一指,那银两便“嗖嗖嗖”有条不紊地往袋中飞去,看得在场诸人瞠目结舌,拍手称奇。
末了五百两白银全部落袋,那小小一个花布腰袋仍是扁扁平平,好似里面空无一物,白衣女子志得意满地拍拍布袋,说道:“多谢了,告辞。”
楚员外道:“姑娘请留步!”
白衣女子道:“还有何事?”
楚员外道:“姑娘您是我楚家大恩人,仙山何处,尊名可否告知,我们也好立牌供奉,时时感念恩德。”
白衣女子道:“真是啰嗦。昆仑摇光,昭彦玄女晏青璃。”话音刚落,人已消失不见。
诸人纷纷感叹道:“哎呀,神仙那——”,有的人痴痴呆望,有的人则俯首膜拜,只有楚员外喃喃道:“原来是昆仑摇光门人啊!”
众人见晏青璃能够凭空消失想必是天上神仙才可做到,楚员外心里却清楚,她这是土遁之法,为之“缩地术”,比如别人从这院子里走到楚府大门外,需得穿廊过巷几千步,而这晏青璃只需一两步便可做到,正所谓“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身随意转,意随心至,心无界限时,则身无界限”,这已是道家极高超的法术,看她不过双十年纪,就已到达这种级别,假以时日,白日飞升也不在话下。
楚员外悠然神往,不禁想到自己年轻时曾上蜀山求仙问道的一段经历,只不过自己仙姿太差,十五岁上蜀山直到三十岁,却一直连个观微境界都未达到,修成仙身更是无望,只好拜别蜀山回家潜心读书,想不到一举便高中状元,之后也算是官运亨通,事事如意,如今忆起二十年前的这段修仙往事,仍是感慨良深,怅然不已。
“凡事各有缘法,既然与仙道无缘,也不必强求,老爷你这些年来享尽人间富贵,妻贤子孝,岂不好过修仙清苦几千几万倍?”一直跟随楚员外的老奴阿夏似看出主人的心事,上前劝慰道。
“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为之逍遥。逍遥不逍遥,只有天知道。”楚员外望着漆黑深远的天幕,长叹一声,同楚夫人一道将病弱的儿子扶进屋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