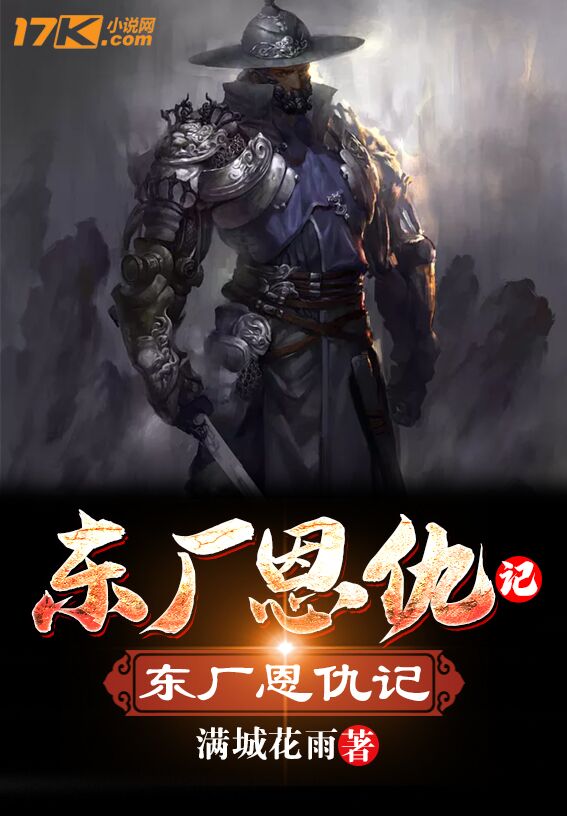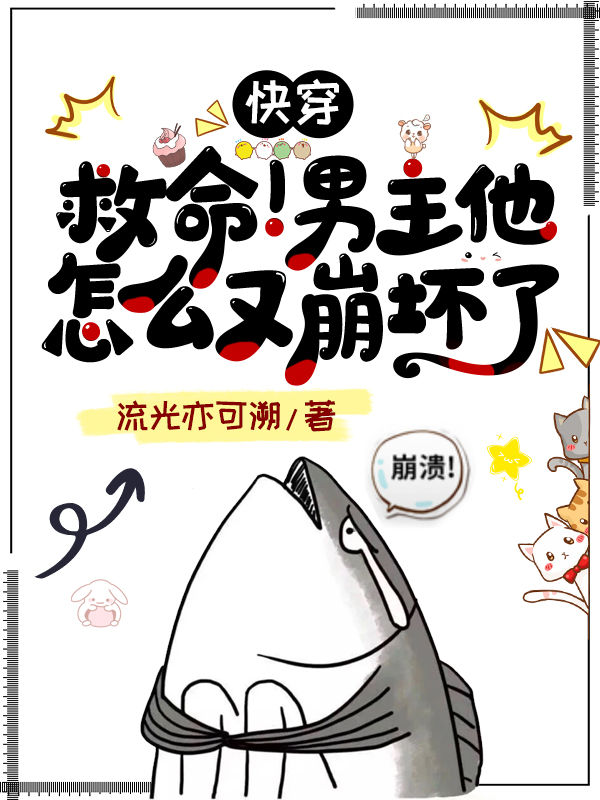“赦上仙这时候倒是想起来自己的身份了。”
郁垒低眸浅笑:“希望为时不晚。”
公子赦挺直身体向阁楼里走去:“我住哪里?”
乔娘赶忙跟在身后:“客官,我这里能住的就两间房,我住一间,你们二位委屈一下挤一挤?”
“难道我和他看起来关系很好么?”
公子赦反问着,面前的这个女子轻浮市侩,毫无夏离的影子,他看着竟然有一丝厌恶。
郁垒紧跟着凑过来:“乔娘,你要是不想这酒馆半夜被拆了,就让我去你房里住吧,我可以打地铺。”
“不行。”公子赦沉着眼眸,用眼角瞟了郁垒一眼:“你睡外面。”
“凭什么不行?”
郁垒跟着乔娘就要往屋子里去…
公子赦的剑又重新搭在郁垒脖子上…
乔娘拨开公子赦的剑,赔着笑脸道:“二位贵客一人一间,我去长廊里过一夜便可。”
“不行!”
这回俩人倒是异口同声,话音刚落二人互望一眼,略微尴尬地收回目光…
“那你们说如何是好?”
乔娘一屁股坐在一旁的栏杆上,这年头生意真是不好做。
公子赦只得指了指郁垒,命令道:“你!过来跟我睡。”
两人皆一夜无眠,也没有再说过话,只怕一开口就打起来不得安生。
翌日一早,乔娘被食物的香气唤醒,起身一看,院落里的桌子上已摆好了羹汤,郁垒正忙着弄手里的酱菜。
听到响动,郁垒抬头,撞上正站在楼梯上的乔娘的目光。
“早啊,吃饭了。”
乔娘望着清晨阳光下忙碌的少年,心里莫名涌过一阵温暖。
清晨的阳光并不热烈,是恰好的柔和,照着杂草上的露水,晶莹剔透,饭菜在阳光下也都笼罩了一层温馨的色彩,她望着他挽起的白发,和低垂着的认真的眉眼,只觉安静又美好。
“托客官的福,我们开酒馆的晚歇晚起,已是很久没吃过早饭了。”
郁垒脱下长袍递给乔娘,语气自然道:“披上些,小心受凉。”
郁垒仍旧注视着手上的活儿,语气神态像叮嘱一位故友一般自然温柔,毫不像是只结识一晚的陌生人。
乔娘这次没有拒绝,而是顺从的穿好,坐到桌前捧着碗喝下一口热汤,赞叹道:“客官好手艺!不如留下给我当膳房伙计,我开工钱给你。”
“你若真心想我留下,无需一文工钱,我可为你做一世羹汤,如若你愿意,我还愿下重金聘礼娶你为妻。”
郁垒转身郑重地望着乔娘,迎着阳光笑起来。
乔娘坐在木椅上,仰头望着郁垒,望着他迎光眯起来的眼睛和灿烂的笑容,露出的洁白的牙齿,恍然间竟觉得无比熟悉。
“客官…太唐突了些。”
“别叫我客官,我有名字,你可以叫我郁垒,或者夫君。”
乔娘一时失语,不知如何应答,只能低下头去喝汤。
郁垒露出一个小孩子恶作剧得逞一般的笑容。
公子赦也走出来坐在桌前,不过好在他没听到刚才那一番对话,不然免不了又是一场战斗。
早饭过后,公子赦起身去轮回之眼找女娲后人瑾萱,想尽快结束夏离的渡劫。
偌大的院落里,仅剩郁垒与乔娘两个人,乔娘开了一坛好酒放在桌上:“算我请你的。”
“乐意奉陪。”
郁垒坐在乔娘身边,开口道:“你为何叫乔娘?”
“我也不知道,其实没有名字,随便起的。”
“这一世你又经历了什么?”
郁垒的目光中流淌着心疼。
乔娘饮下一杯酒笑着道:“什么叫这一世?”
郁垒也跟着笑:“你是否相信人有前世今生?”
“那我前世一定是大王的女儿,尽享荣华富贵,所有的甜都尝尽了,这一世才如此苦不堪言。”
“苦从何来?”
“众生皆苦。”乔娘眯起眼睛,不愿再提往事:“来,喝酒。”
“你可读书识字?”
乔娘望着郁垒,怅然若失地摇了摇头。
郁垒起身折断一截树枝,握着乔娘的手在地上写着乔娘的名字,一笔一画。
“郁垒二字如何写?”
“你想写我的名字?”
乔娘回身望着他点了点头。
郁垒低垂着眉眼,认真地教乔娘写字,乔娘感觉到耳畔微痒的气息,终于她开口说道:“你为何对我好?”
“因为你值得。”
郁垒的目光始终落在地上,并未抬眸望她,语气却无比诚挚。
“我这一生罪孽深重,如果没有遇到你,我便靠这些酒潦草度日,日日复月月,月月复年年,年年复此生。”
一颗泪掉落在郁垒手背上,郁垒顿了一下,写字的手仍旧没有停下。
“我出生那夜,村里下了一场大雨,母亲难产血流如注,父亲带着哥哥出村找接生婆,却在山脚下…被山顶滚落的巨石带走了性命。待雨过天晴,村里人本想来给我母女俩收尸,赶到时母亲早已气结全身僵硬,可没想到床榻上血泊里的孩子却起死回生…没人知道母亲是如何生下我的,也没人知道我在那场骤雨疾风的夜晚是如何活下来的。”
郁垒喃喃出声:“原来这一世你来的这样早。”
“什么?”
郁垒勉强笑笑,摇了摇头,注视着地面岔开话题道:“看,这就是我的名字,郁垒。”
“你写的字真好看,能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一起么?”
郁垒认真写着字,还是忍不住道:“想必活得很辛苦吧。”
“村里的人说我是灾星,是带着神明诅咒而来的罪大恶极之人。一出世便克死了自己所有的亲人,如果继续留着我,只会克死全村的人。”
“他们赶你走了?”
乔娘摇了摇头:“没有,如果是那样,我可能早就饿死在荒郊野外,倒还痛快。他们没有放我走,而是抹去了我生而为人的名义,让我以畜牲之名活着,这样我就不会被神明发现。”
乔娘的身子止不住的颤抖,眼泪逐渐滂沱:“他们把我关在马圈里,猪笼里,和这些畜牲一起生活,吃同样的东西,喝一样的载满污垢的水,在那里脱.光如厕,在那里睡觉,在那里带着满身淤泥与恶臭生长。”
乔娘回想起这些只觉自己太过肮脏,想离郁垒远一些,怕玷污了这个面容干净俊秀的少年。
可郁垒却在身后紧紧抱住她,不容她挣脱。
“你知道冬天有多冷么?你们都不知道,不可能知道彻夜的寒冷接着白昼的寒冷,没有尽头,没有希望,无处遁藏的感受。我躲在稻草底下,和那些畜牲围靠在一起取暖,那一刻,我恍然真的觉得自己是它们当中的。”
“夏天的时候,饭菜馊掉的味道比畜牲身体里所散发的味道还要难闻,永远赶不完的苍蝇,永远挑不完的虫子,黏稠得糊在一起,就是这样的吃食,还是要和几头畜牲在一个铁槽里拼命争抢才能吃上几口。”
“他们鞭打我,唾弃我,恐吓我,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发泄在我身上。我看到太多了,平时和蔼可亲的婶子,在暗地里扎着布偶诅咒村里的孩子去死,每次递给孩子们的糖都沾着她的口水。”
“年轻男子与他的情人在我面前苟合,并且合力杀死了情人的夫君,剁成了肉碎给我吃,只说这个男人是失踪了。”
“平日里受尽欺凌的哑巴总是蜷缩在角落里,可到夜晚之时,他便会拿着烫红的铁烙来折磨我。仿若我是能使他活下去的,这个人世间所寄予的最后的希望,那就是原来世上还有比他更不幸的人。”
“这是人坚持着活下去的最后的理由吧。”
乔娘转过身来,望着郁垒,她的眼里是他所不能直视的绝望,一字一句皆像一把利刃刺穿郁垒的心脏。
郁垒将面前的女子拥进怀里,啜泣着说道:“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来晚了,这一世我来晚了。”
“那我为什么不去死呢?因为我不甘心这样就是我的宿命了。可我并不知道该如何改变。一直到第十一载,这样的日子我整整过了十一载。我渐渐长大,并没有在某个肮脏的角落里死去。第一个想起我的男人,在一个寒冬的深夜里带着醉意来撕.扯着我身上的破布,他似乎恍然大悟原来我还是一个女.人,并且是任人宰割的女人。”
郁垒将头埋在乔娘的脖颈处,手指的关节因为用力渐渐泛白,声音颤抖得不成语调:“别…别说了…求你…别再继续说了。”
“你不想听了么?”乔娘的语气冰冷,一改平日里轻浮的模样。
“比这残酷的事还有很多,我说的不过凤毛麟角,你听完了全部,就知道我是身处炼狱,而非人间。”
“我知道,我知道,求你别再说了。”郁垒抬起头望着乔娘。
乔娘这才发现郁垒早已泪流满面,双眼猩红。
“你为何要哭?是怜悯我?”
乔娘伸出手,十分柔和地拭去了郁垒的眼泪。
“我的心好疼,疼到…”郁垒捂着胸口,俯下身去:“疼到再经不起你说一个字。”
“你是第一个这样对我的人,也是第一个让我感到温暖的人。”
“不,我是最愧对于你的人,如果我早一点来,早一点找到你,便不会发生这些。”
“这是宿命,就像他们的死也是宿命。”
郁垒愣住了,疑惑地看向乔娘。
乔娘唇角隐约笑着:“后来所有人都被我逆来顺受的模样欺骗了,他们对我放松警惕,以为我也不过是一头没有想法的畜牲。所以,我抓住了机会,用一夜的时间放了一场大火。火光连天,甚是明亮。”
乔娘笑起来,大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有几分狰狞。
“我手里拿着散落在畜牲棚的割草用的刀,走出了村子,在村口碰到一个逃出来的小男孩,他看到我,似乎看到了希望,向我呼救,可是我太熟悉他的样子,我记得他拿石头砸我,喂我吃蜘蛛蜈蚣时的狰狞面孔,我冲他笑了,他稚嫩的脸庞真像一个魔鬼。”
“他的眼里全都是绝望和恐惧,原来恐惧这样值得人享受,我看着他的恐惧,我满足极了。鲜.血.喷溅在我脸上的时候,我也是笑着的。”
乔娘双手做出落刀的动作,缓缓坐在桌边,抬手抓起酒坛一饮而尽。
“我果然是克星啊,他们所言极是!全村老少百余口性命,全都葬送在我的手上。”
“不是你的错。”郁垒的手覆在她的肩膀上。
“不,是我的错,我以为的解脱,原来是踏进更深的更煎熬的炼狱之中。”
“有我在,没有炼狱敢收你。”
乔娘望着郁垒恳切的目光,充满疑惑:
“为何要待我好?我没什么可给你的。”
郁垒抬手紧了紧她身上披着的长袍,语气温软:
“我什么也不要,只愿你余生顺遂,康乐,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