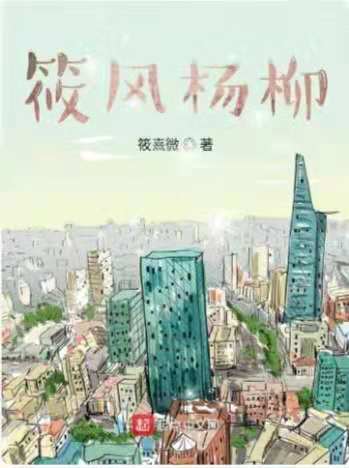“……”钟小娘被她问得哑口无言。
司马瞿这才出声回应道:“仁孝是好事,为人子女理应如此。去厨房盛了元宵给你阿娘送过去吧!谢管家,你陪三姑娘同去,就说是我的意思,让他们放行。”
语毕,司马黛凝忙欢喜致谢道:“多谢父亲,多谢父亲,女儿这就下去了,父亲慢用。”
说罢,她搁下木筷,领着丫鬟橙紫匆匆往厨房行去。谢管家也行礼,匆匆跟了上去
司马黛凝刚离去片刻,司马黛瑜也吃罢,起身行了礼,领着丫鬟离去。司马黛媱今日心情本就不好,也紧随其后回到自己闺房,留下司马瞿和钟小娘独处。
钟小娘用手里的小勺,搅动着碗里躺着的元宵,低声道:“夫君,这又是一个新年头了,媱儿又长一岁了。她的婚嫁之事,夫君可有什么主意?若再不定下来,媱儿可真成老姑婆了。”
“这不陆陆续续有人上门来提亲吗?等给硕儿办完满月宴,就让昀姝给张罗着办,从那些人中选个秉性纯良的佼佼者。”
自己亲闺女的婚事,自己也没办法亲力亲为,必需得交给卢昀姝这个当家主母。
一提到这,钟小娘就来气,若不是司马莞笙那贱蹄子从中作梗,卢氏怎会可能重拾主母身份,怎么可能有机会主持媱儿的婚姻大事。
“夫君,那楚将军之子楚南玄,你也见过,当真是佼佼者,若能成为司马府的乘龙快婿,无疑是好事一桩。夫君你和楚鸣鸿将军私交甚好,可不可以为了媱儿委屈一回?给楚将军提提此事?”温言细语,字字斟酌。
司马瞿一听,一掌拍在桌上,厉声道:“让我跟楚将军提攀亲之事,你真当你夫君这张脸是牛皮做的不成?还嫌我丢脸丢的不够?”
苏小娘大闹将军府一事,虽然找借口搪塞过去了,但雁过还留声呢!他怎么可能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堂而皇之再上门去谈孩子们的婚嫁之事。
再者,即便要和楚府攀亲,也轮不到司马黛媱。这嫡庶尊卑就算他司马瞿不在意,人家楚家也会在意,楚将军就这么一个独子,怎可能迎娶庶女进门为妻。
钟小娘见司马瞿动怒,忙安抚道:“夫君莫动气,妾身也只是随口一说。媱儿的婚嫁之事还望夫君多费些心,为媱儿觅得良缘。”
“罢了,我之前不是说过吗?不会委屈媱儿的。我吃好了,先回房了。”说罢,他匆匆起身离去。
钟小娘脸上伪装出来的笑容,瞬间收起,露出满脸怒气,牙关紧咬,手指把桌板抓得嘎吱作响。
我在这个家任劳任怨,苦心经营十余载,换来了什么?就换来这一通怒吼,一张冷脸。
……
丽春阁,司马莞笙的住处。
方才那丫鬟幽兰捧着汤盅,在茹霜的引领下进到房内。
司马莞笙正好在用膳,桌上就两碟小菜,一碗米粥。
丫鬟幽兰捧着汤盅躬身行礼道:“二姑娘,安好!家主差奴婢前来给二姑娘送元宵。”
司马莞笙拿着筷子的手悬在半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片刻之后,她不紧不慢的低声道:“搁桌上吧!”
丫鬟幽兰将手里的汤盅捧到桌上搁好,还特意把司马瞿的好意传达,“二姑娘,元宵要趁热吃,家主知道二姑娘喜欢吃酒酿,特意命奴婢多盛了些酒酿。”
司马莞笙闻言搁下筷子,揭开盅盖,看着盅里冒着热气的元宵。
司马瞿如此“厚爱”,她不知道自己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
司马瞿的漠然和是非不分,才是导致家宅不宁的元凶,他哪怕硬气一点,哪怕明辨是非一点,也不至于让这些妻妾这般无法无天。
司马莞笙不明白,为什么在衙里能替百姓申冤,能替圣上分忧的雒阳府尹,面对这些表里不一的女人,却没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她真的高兴不起来。
她低声道:“行了,没旁的事了吧?没有就退下吧!”
幽兰闻声,行礼后退了出去。
司马莞笙把手里的小勺扔回汤盅里,冷冷道:“凌妈妈,我吃好了,让她们把这些撤了吧!茹霜,你不是喜欢吃元宵吗?这还热着,你趁热吃。”说罢,她起身朝书阁行去。
茹霜那是个激动,连忙堆笑致谢道:“谢二姑娘赏赐!”
主子们的元宵,那可是精心制作而成,用料什么都是上等的。像她这样的丫鬟,能吃上这样香甜爽口的元宵,那可真是有口福了。
她乐得嘴都合不拢,把那汤盅如宝贝似的捧在手里,一个劲傻笑。
书阁里,司马莞笙找出信纸,在伏案书信。
凌妈妈在旁磨墨,出于好奇,她问了一嘴,“二姑娘,这么晚了,你这是要书信于谁?”
“给雍州的舅舅。”
“二姑娘,你这是想文城少爷和老夫人了吧?”
“想去母亲坟前尽尽孝,多年不见外祖母,我也有些想她。一月之后,就是外祖母五十大寿,等禁足期满,快马加鞭还能赶得上给她老人家拜寿。”
“二姑娘,你……你言下之意是要回雍州?”凌妈妈闻言,惊得磨墨的手也停了下来,“二姑娘,这可使不得,这雒阳离雍州千里之遥,路途艰险,危机四伏。家主那里,也不会同意你孤身涉险的。”
司马莞笙并没回答凌妈妈,把书写完的信放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下舅舅凌文城的姓名。递给旁边的凌妈妈道:“凌妈妈,你差人把信送到舅舅府上。”
“二姑娘?”
司马莞笙抓住凌妈妈长了冻疮的手,堆笑道:“凌妈妈,你就把心放回肚子里,莞笙不是三岁孩童,能辩是非,能知轻重。快去吧!”
凌妈妈重重舒了口气,点头应着,拿着信退出房去。
司马莞笙看着凌妈妈离去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元宵节后,司马府就开始发放宴帖,筹备司马永硕的满月宴。
司马府内,张灯结彩,丫鬟婆子们已经忙前忙后添购满月宴所需用品。司马府门前,车水马龙,送菜的,送酒的,送桌椅板凳的络绎不绝。
司马瞿特别在意这次满月宴,司马永硕的新衣和百命锁,都是他亲自挑选定制。小到一双棉袜,他都再三挑选,生怕委屈了这襁褓之中的小儿。
即便卢氏尚在月子中,他还是三天两头留宿听雪阁,对卢氏的态度,同之前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十五日后,满月宴如期举行。
司马府门口马车抬轿排了好几排,贺礼整整堆了半间屋子。自从司马家举家迁至雒阳,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司马莞笙原本还担心钟小娘会不甘心,会在满月宴之上再折腾。可结果比她预想的好太多,满月宴很圆满,司马府上下齐欢。
晚上,送走所有宾客,卢氏早已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司马瞿也累得够呛,回到房里,卢氏就命丫鬟们备了热水让他泡热水澡缓解疲劳。
卢氏原本也想洗洗早些歇下,但为了能当好这个正房太太,不让司马瞿失望,她拖着疲惫的身子还坚持去贺礼房清点贺礼,记账入库。
司马瞿泡完澡出来,发现她不在房里,随口问旁边的丫鬟道:“大夫人呢?”
“回家主,大夫人去贺礼房清点贺礼了。”
司马瞿闻言,取下衣服架子上的外袍穿戴好,又命丫鬟取了件披风,抱着披风独自一人去贺礼房寻卢氏。
他站在贺礼房门口,看着认真仔细盘点的卢氏,心里突然升起愧疚之意。
如此贤良淑德的夫人,我却冷落她这么多年,我真是愧为人夫。
他放轻脚步走进房里,将手里的披风披到卢氏身上。
卢氏被吓了一大跳,猛的回过头来,“夫君,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你是不是就打算今晚让我独守空房?”司马瞿一边替她系好披风上的绳子,一边温声细语道。
这没有水平的情话,卢氏听了却甜到心里去了。她望着司马瞿的脸,眼里是满满的感动,有些受宠若惊不知所措。
司马瞿夺过她手里的账本和毫笔,搁到那堆成山头的贺礼中。轻轻牵起卢氏的手道:“这么晚了,这些明日再整理,累了一天,你又刚刚出月子,要是累坏身子,谁来照顾硕儿?谁来替我持家?”
“夫君……”
“好了,走吧!”
司马瞿牵起卢氏的手,两人像一对热恋的年轻男女一般,朝着卢氏的睡房行去。
满月宴过后,司马莞笙的禁足期亦满。
翌日,卢氏以正妻的身份,正式接受妾室姑娘们的请安。
当然,司马莞笙也不例外,她早早梳洗完,简单用完早膳,领着凌妈妈朝听雪阁去。
听雪阁,卢氏住处。
卢氏和司马瞿已经用过早膳,卢氏正准备送司马瞿出门去衙里。
“夫君,我送你到门口?”卢氏见司马瞿的衣襟有些乱,一边替他整理,一边低声道。
如此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日子,她已期盼了十余载,如今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她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眼里心里都幸福。
“不用,怕耽误她们过来向你请安,你记得把我交待的事放在心上就是。”
“夫君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帮黛媱觅得良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