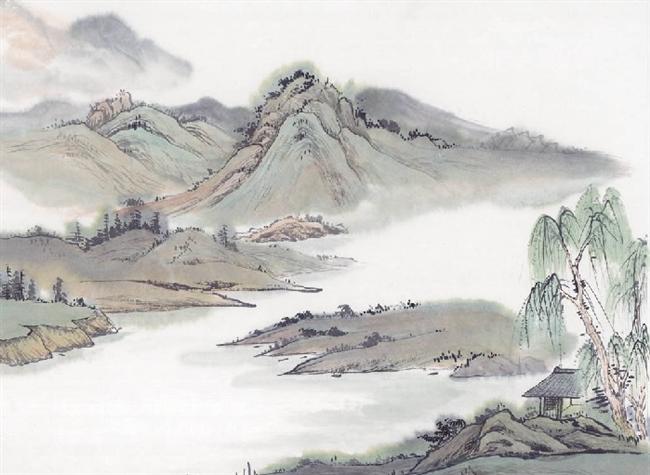能同当今圣上共进晚膳,这可是莫大的荣幸。刘赫受宠若惊,自觉此行必定相当顺利。
他没有迟疑,立刻应下。
秦淮闻言,即刻差人为他备案几软垫,又命人前去传膳。
陛下见众人忙乎,出声阻止道:“秦淮,不必再传了,把寡人的膳食一分二便是。”
秦淮应下,领着小太监们慌脚忙手的张罗。
刘赫眼高于顶,从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在和善的圣上跟前,他也不觉自己矮一截。当真把圣上当成亲叔一般对待,放开手脚陪吃陪喝陪聊。
与陛下共忆儿时趣事,相谈甚欢。
套完近乎,最后,刘赫才表明来意。
他起身离座,拱手作揖俯身行礼道:“陛下,赤之斗胆向陛下要个人。”
“要个人?”圣上闻言,放下御筷,似有疑惑,须臾,笑道:“赤之这是红鸾星动,好事将近?”
“并非儿女私情,只是赤之府中有职位空出,且又与那人一见如故,知己难求,还望陛下恩准。”
圣上若有所思片刻,问道:“所要之人,姓谁名谁,可有功名官衔在身?”
圣上是心思缜密之人,即便再在乎亲情,也不会毫无顾忌就答应。亲王地位颇高,门客裙带关系复杂,若掣肘不当,会让那包藏野心之人有机可乘。
故此,无关轻重的人可以给,有权有势,尤其是手握兵权之人,他是绝不会给。
“此人是新安县令之子,今年春季殿试中得三甲五十六名。”
小小七品县令之子,且只是个三甲而已,在朝中也无党羽可言。
圣上原本还想让人细查后再做回复,如此看来,无需多此一举,他爽快回应道:“行,寡人便把此人赐予赤之,望赤之惜才。”
刘赫闻言,甚是激动,“谢陛下隆恩,赤之一定替陛下守好均邑,为大焱的昌盛尽绵薄之力。”
圣上当即拟旨交于刘赫,刘赫所求之事如愿,欲告辞离宫。
圣上见天色已晚,留他在宫中留宿一宿。
翌日,他带着圣旨,找到当地县令,为余默褚开了各种凭证和路引。
从县衙出来,他举着那一堆凭证,得意的在手掌上拍打,一脸阴笑,“哈哈!有了这‘卖身契’,他想不就范都难。”
若是换作平头百姓家之女,他绝不会这般大费周折,早就强抢强要。司马黛媱毕竟是官宦人家之女,司马瞿又在天子脚下任职,他还是有所顾忌的,且他当真对司马黛媱有好感,他方才用明媒正娶这一套。
“走,去新安。”刘赫说罢,踏上候在门口的马车,马车绝尘而去。
余府门口,靳驿敲开了余府的大门。
刘赫表明身份后,余府下人赶紧折回通报。
不多时,余县令领着柳氏和余默褚亲自到门口相迎。
“王爷万安!”余家人都恭敬行礼,“王爷大驾,微臣有失远迎,”
“本王冒昧上门叨扰,还望余县令见谅才是。”一脸和善,给人很易亲近的感觉。
刘赫虽荒.淫无道,但这王爷该有的架子还有的。
“王爷大驾,敝府蓬荜生辉,微臣荣幸之至才是,王爷里边请。”余县令躬身将刘赫让进府里。
余府客厅里,刘赫坐于主座之上。余县令、柳氏、余默褚坐于客座之上,都面带拘谨之色,显然刘赫的到来让他们有些触不及防。
余家人自是要盛情款待的,吩咐下人们把一直舍不得吃的珍藏茶叶都拿了出来,用以招待刘赫。
刘赫不吱声,余家人也都闷声不吭,不敢多言半字。
刘赫端着茶杯,以茶杯盖轻轻拨动着茶杯里漂浮的茶叶碎末,表情很是镇定。轻轻吹动着茶杯里冒起的热气,小饮了一口。
他给靳驿使了个眼色,靳驿随即将怀里抱着的锦盒搁到余县令旁的案几之上。并将锦盒打开,一箱白花花的银子映入众人眼底。
余家人惊得双目圆睁,余县令尤甚,他满脸疑惑的问道:“王爷,这是何意?”
“这是赔给你家的聘礼。”刘赫直接开门见山,不想拐弯抹角。
“聘礼?”余家人面面相觑,不明白刘赫之话是何意。
对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余默褚,更是满头雾水。
“对,聘礼,本王要你们退掉同司马府的亲事。”刘赫用命令的口吻说道,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没有刚进门那般可亲,“本王也知道,余大人素有清廉之名。但此事不一样,绝不是受贿,只是名正言顺的赔偿。”
闻言,余县令夫妇脸色骤变。
未等夫妇俩开口,云里雾里的余默褚开始皱着眉头质问柳氏:“母亲,你不是说已经把这门亲事退掉了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柳氏闪烁其辞,不知该如何向儿子解释,低声劝道:“默褚,有客在,此事稍后再议。”
“微臣谢过王爷美意,这些银钱王爷还是收回吧!”余县令起身将那锦盒盖上,双手捧到刘赫身旁的案几搁下,方才退回座位之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刘赫怒问。
“回王爷,这婚姻大事,岂能说退就退,且聘礼已下。这种出尔反尔之事,恕微臣做不到。”
刘赫拍案而起,怒吼:“敬酒不吃吃罚酒。”他伸出右手,靳驿将余默褚的凭证和路引双手奉到他手上。他将折扇往腰间一塞,行至余县令跟前,将那些凭证和路引一一打开,冷冷道:“余大人,睁大眼睛看好了,看看这些都是什么。”
余县令站起身来,目不转睛的看着那些凭证和路引,脸色骤变,眉头紧锁。
看完,他瘫坐在椅子上。
柳氏在旁摇晃着他的胳膊,不停小声的追问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余大人,不知道你现在觉得,这婚事到底能不能退?”
半响,余县令才回过神来。
这均邑王的大名,他早有耳闻,简直就是个恶霸。既然刘赫盯上余家,就绝不会轻易罢休。
“王爷,你如此罔顾王法,难道就不怕陛下治罪吗?”
“哈哈!王法,你一个小小七品县令也配谈王法。怎么着,还想告御状不成?那敢问余大人,你要告本王什么?是强抢民女?还是逼良为娼?也或是威胁你?甚至是贿赂你?”刘赫满脸不屑,在厅里徘徊狂笑。
余县令闻言,表情变得更加凝重。双眉紧锁,一言不发。
柳氏从两人的谈话,也听得七七八八,原来是来和她抢儿媳妇的,她好不容易才促成这么良缘,岂会轻易言弃。
她提高嗓门吼道:“这门亲事是我们先订下的,就算你是王爷,也没有后来居上之理。司马家姑娘,我们余家娶定了,绝不退亲。”
刘赫闻言,冷若冰霜的脸上,掠过一丝讽刺的笑意,道:“余夫人好气魄,既然这样,我可得好好想想,该在我府里为你家公子安排个什么职位呢!是刷马桶的下等贱奴呢?还是膳房里挑水劈柴的低等奴才?”
“我家儿郎,可是进士,岂是你想让他做甚,他就做甚的。”柳氏没读什么书,自然是不懂得官场这些事。
“余大人,你呢?可是与余夫人口径一致?”
余县令眉头紧锁,同柳氏面面相觑,半天没吱声。
他身在官场,自是知道刘赫手中那些东西的重要性。他把目光投向余默褚,看着正是大好年华的余默褚,不想他的人生因此而毁,心中甚是纠结。
余默褚起身劝说道:“父亲,你们就答应王爷,替孩儿退掉这么亲事吧!孩儿同那司马小姐,本就无缘无份,何必强求。”
他心中暗喜。
天意,都是天意,若不是半路杀出个王爷,那恐怕我就真的引狼入室了。如若那样,大婚后,我余家休想有安宁日子,真是谢天谢地。
刘赫闻言,倒是对这个情敌颇有好感,他行至余默褚身旁,拍着余默褚肩膀笑道:“余公子大丈夫是也!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放心,以后本王一定会重用你。”
余县令知道刘赫位高权重,事已至此,若是不答应,不仅余默褚前途尽毁,恐怕连他头顶的乌沙也难保,余家此后定劫难重重,再无宁日,胳膊肘拧不过大腿。
他虽一身清廉,两袖清风,从不收受半文钱贿赂,但舍弃个人荣辱简单,要让一家人为他的清名陪葬,他做不到。
罢了,为了默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他重重叹了口气,无奈道:“行,我们可以答应退亲。”
语落,柳氏急了,忙劝道:“老爷,你怎么能答应他呢!你不是经常教默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吗?你这不是上梁不正吗?我们行的正坐得端,就算是当今圣上前来,也不敢说我们有罪不是?”
柳氏毫不避讳,扯着嗓子喋喋不休。
余县令疾言厉色道:“妇道人家,你懂个啥?这都什么时辰了,还不去让厨房张罗午饭。”
“我……”柳氏左右环视一眼,捂着嘴,带着哭腔道:“你竟然凶我?这日子没法过了……”她哭骂着跑出客厅。
余县令和柳氏感情极好,成婚十余载,从未红过脸,拌过嘴。
余县令突然这般疾言厉色吼她,她一时有些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