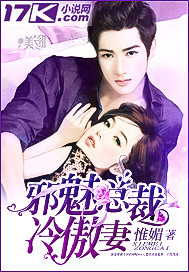司马瞿的脸早已变色,放下手中的碗筷,瞪着司马莞笙,厉声吼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差拍案而起了。
司马莞笙吓得身子不由自主一颤,无辜的望着司马瞿,急言:“父亲,莞笙没有。”她把视线投向司马黛媱,“大姐姐,你如此诋毁莞笙,就因为莞笙今日在盛会之上抢了你风头吗?那莞笙给你赔不是便是。你所言,可事关莞笙的清誉,事关司马府门风,慎言!”
脸上满是委屈,眼里似乎还闪烁着无辜的泪花。
司马瞿耳根子软,且就是个没主见优柔寡断之人,向来只听信一面之词,遇事不过脑,从不深究。也正因如此,钟小娘才能在司马府作威作福。
他见司马莞笙这般委屈,瞬间将愤怒的眼神投到司马黛媱身上。
司马黛媱有些措手不及,毕竟在这之前,她还是个没有城府,内心单纯之人。
这次,的的确确是司马莞笙有错在先,她今日若是招来旁人,多人为证,大喊大叫抓个现成。那么,是完全有机会让司马莞笙清白尽毁的,可她还做不来。
她结结巴巴道:“二妹妹,你,你狡辩,别企图往我身上泼脏水,把自己摘个一干二净。我和翡翠能看到,旁人必定也能见到。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别当了婊.子,还想立贞节牌坊……”
司马黛媱被司马莞笙这么一说,慌得口不择言。
“闭嘴!”司马瞿拍案大吼一声,打断司马黛媱的话,“你们俩还有完没完?媱儿,有你这样做长姐的吗?疯言疯语。”
钟小娘见司马瞿发怒,没敢吱声。倒是司马黛媱,理直气壮叫屈。
“父亲,黛媱冤枉,黛媱所言,句句属实,父亲若是不信,可以问茹霜,茹霜当时也在。”
卢氏见气氛紧张,忙出言安慰司马瞿道:“夫君,你消消气,莫气坏身子。我们是一家人,有事好商量,也许,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呢?凡事看开,万事想开,有事说开,没有解不开的误会。”
她这番话,让司马瞿的怒气消减大半。
卢氏还贴心的让卢妈妈去沏了杯热茶来,让司马瞿降火去躁。
众人都面面相觑,一场好好的庆功宴,硬生生被吃成鸿门宴。
良久,司马瞿才冷冷道:“卢妈妈,你去唤茹霜来。”
卢妈妈不敢有丝毫迟疑,领了命令退出房去。
膳才用到一半,谁也没有心情再继续吃下去。大家就那么一声不吭的坐着,屋里静得落针有声。
司马黛媱一直瞪着司马莞笙,脸上隐约露着得意的笑意。
不出半刻钟,卢妈妈就领着茹霜匆匆而来。两人都呵斥呵斥的喘着粗气,估摸着是小跑着赶来的。
卢妈妈行礼后,退到一旁候着。茹霜双手紧扣,低着头,紧张的杵在那里,不敢擅动。
“茹霜,家主有事问你,你可得如实相告,且不能说半字谎言。”卢氏先开口叮嘱茹霜,在她心里是不愿意相信司马莞笙会这般没分寸。
“奴婢不敢!”
语落,司马瞿冷冷问道:“今日在赛马场,二姑娘可有和外男接触?”
“回家主,有。”茹霜想也没想,斩钉截铁回道。
语落,司马黛媱忙激动的接过话,“父亲,听到了吧?连她自己的丫鬟都这么说,你总该相信女儿所言并非虚言了吧?”
司马瞿没有理会她,继续问:“你可认识那人是谁?”
“人挺多的,奴婢也不全认识。”茹霜此话一出,在场之人皆惊得目瞪口呆,“但和二姑娘骑射比赛那公子奴婢认识,是大将军府楚南玄小将军。对了,家主,陛下也算外男吗?”
闻言,司马瞿哭笑不得。
他自知,这丫鬟是没理解他所问之话的意思,“我不是问得这些。”
“奴婢愚钝,还请家主明示。”
“二姑娘……”司马瞿心一狠,“有没有和外男私会?”
茹霜闻言,瞄了一眼司马黛媱,司马黛媱给她微微点头示意,她斩钉截铁回道:“没有,绝对没有,奴婢一直陪着二姑娘。”
“你……”司马黛媱气得两眼冒火,怒而起身,“你这个贱婢,竟敢睁眼说瞎话。”
“大姑娘,奴婢没有,奴婢所言,句句属实,不敢有所隐瞒。”
“说,是不是司马莞笙抓住你什么把柄要挟你?你别怕,有父亲替你做主,她不敢把你怎么着……”
“闭嘴。”司马瞿实在受不了司马黛媱的喋喋不休,怒吼到。
“……”司马黛媱这才闭了嘴,坐回雕花镂空凳子上。瞪着茹霜,鼓着腮帮子生闷气。
好你个茹霜,拿了我的好处却不办事,看我事后不剥了你的皮。
双方各执一词,司马瞿也不知如何是好,思虑良久,他觉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毕竟这没影的事,也不能指责谁对谁错。
只是姐妹两人如此猜忌,针对,让他失望至极。
他愣了半响,说道:“行了,茹霜,你下去吧!这里没你事了。”
茹霜迟疑片刻,唯唯诺诺道:“家主,奴婢,奴婢……”她扑通一声跪到地上,磕头哀求道:“奴婢有错,求家主饶恕!求家主开恩!”
“你又怎么了?”司马瞿满脸不耐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心中很是不爽快。
司马黛媱一听,心中一喜。
莫不是这丫头想通了?
茹霜眼中闪烁着泪花,嗫嗫嚅嚅的,“奴婢,奴婢从来没想过卖主求荣,傍晚时分,大姑娘硬塞给奴婢一包东西,并以卖奴婢去秦楼楚馆相要挟,让奴婢诬陷二姑娘与人私通……”
闻言,司马黛媱拍案而起,强行打断茹霜的话,“贱婢,你胡言乱语什么,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说着,她就有冲上去打人的冲动。
“够了。”司马瞿一声吼,“当我是死的吗?”
“父亲?她……”
司马黛媱想为自己辩解,但司马瞿没给她机会,出言打断她已提到嗓子眼的话,“钟葭芸,这就是你教养出来的好女儿。”
钟葭芸也不甘示弱,为自己女儿辩护,“夫君,一个丫鬟空口无凭的话,不足为信。你是知道的,媱儿虽性格活脱点,但绝不是心思歹毒之人,可万不能委屈了媱儿才是。”
“是与不是,我自有判断,若是再敢多嘴,就滚去祠堂好好反省。”司马瞿疾言厉色道。
钟小娘也不再多言,起身强行将司马黛媱拽回凳子上。
“茹霜,你继续说。”司马瞿正襟危坐,对跪在那里吓得身子微颤的茹霜道。
或是司马莞笙今日为司马家长了脸,司马瞿下意识有些偏袒她。
茹霜从怀中掏出那包手饰,双手奉上,“这就是那包东西,还望家主为奴婢做主,奴婢不敢背叛主子。”
司马瞿接过包裹,把碗筷往边上一推,腾出一小块地方,将包裹摊开。
包裹里全是些值钱的手饰,司马瞿从中挑了一样拿在手里,望着司马黛媱道:“我若没记错,这手镯是你百岁时,我差工匠为你打制的,你可还有话说?”
司马莞笙在心里暗暗念叨:大姐姐,我原本想不计前嫌,与你井水不犯河水。没曾想你终究本性难移,你对我不仁,就休怪我不义。
司马黛媱原本想着,那些都是孩童时期的钗戴什么的,也戴不上,搁那里还占地。特寻出来打发给茹霜,让她识趣。
可她万没想到,这些,竟然成了人账俱获的证据。
司马黛媱看着那些砸自己脚的东西,灵机一动,“这些东西,已经丢了好久了,原来是被这贱婢给偷了去。父亲,这手脚不干净之人不能用,应该赶她出府去。”
“家主,冤枉,这些的确是大姑娘傍晚塞给奴婢的,不是奴婢偷来的。”茹霜害怕的为自己辩解,把目光投向司马莞笙求助。
司马莞笙的清白未还,这把茹霜也牵扯进来,她很自责,懊悔不该让茹霜揭发司马黛媱。
她看着桌上那堆东西,浅笑道:“大姐姐,若这些东西,茹霜真是偷来的,为何茹霜还敢主动拿出,她可不是如此蠢如鹿豕之人。”
“谁知道呢!兴许是良心发现。”司马黛媱想也不想,理直气壮的回到。
司马莞笙拿起其中一个长命锁,放在鼻尖轻嗅,“好香,正是大姐姐喜用的胭脂味。大姐姐,你的首饰钗黛,都是谁帮你收纳保管呀?”
“自然是翡翠。”
“那就奇怪了,今日茹霜捧着这包东西回来,我特意差人去问过翡翠,你的这些东西可还在,她拍着胸脯保证都还在。既然翡翠都不知道丢失,二姐姐你又是如何知道丢失了?且一直也没有寻找的动静传出?”
“……”司马黛媱被问得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回道。
她的迟疑,使事实昭然若揭。
“茹霜只不过是本本分分的丫鬟,还请父亲明鉴。”司马莞笙趁热打铁。
司马瞿也不是老态龙钟之人,司马黛媱的理由的确太牵强。事实如何,他心中自知。
“茹霜,你退下吧!”司马瞿脸色乌青,冷冷道。
茹霜谢恩后,起身退出房去。
司马瞿又让卢氏摒退屋里所有的丫鬟婆子,合上膳殿的门,留下一屋子自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