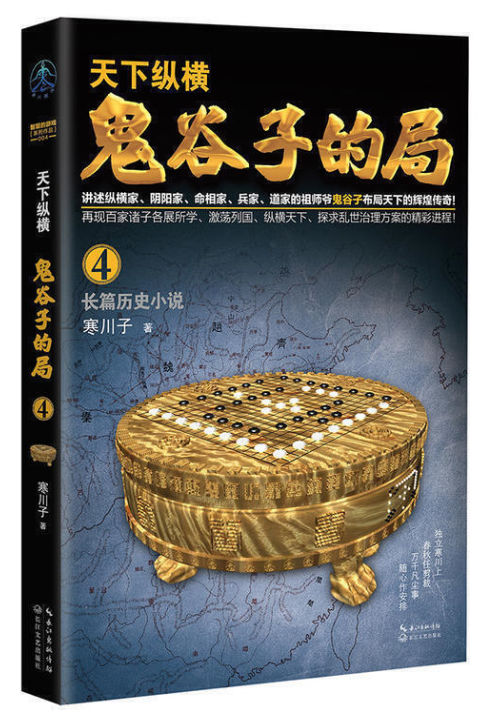橡皮股大闹上海?伍挺举一力质疑
陈炯的宿处被任炳祺特别安排在堂子后院,位于二楼西侧角落,是个极隐蔽的套间,一间办公,一间卧室。如果前往他的住处,须得经过前厅、中堂及一长排烟花女子的接客雅间。这且不说,为安全起见,炳祺又在这个套间里设有阳台,阳台下面是另一家的屋顶,万一事急,陈炯可以打开阳台,通过邻居屋顶一逃了之。
这日后晌,陈炯没有出去,正在书桌前书写什么。一个文静少女站在他椅后,或捶背,或揉捏肩、颈等部位。
一阵脚步声响,炳祺进来,看下少女,使个眼色。
少女走出,悄悄下楼。
“呵呵,”炳祺乐道,“看样子师叔蛮享受哩。要是不中意,徒子再换一个?”
“就她了吧,挺会照顾人。”陈炯笑笑,“你这辰光来,有啥事体?”
“有人寻你!”
“啥人?”
“就是你的那个兄弟,伍挺举!”炳祺扑哧一笑,“这人真是好玩,寻到门口,见是堂子,脸色透透红,以为走错地方了,不停地向龟奴道歉,重新拿出门号,核对半晌,再次敲门。龟奴以为他是头次到这地方来的,安排他进客堂,叫来几个小娘热情接待,把他吓得又蹿出去,龟奴生怕走了生意,追出去问,他说是寻人,龟奴问他寻啥人,他却不肯讲出你来,只说朋友可能是写错门号了。正要转身走人,徒子刚好回来,认出是他,得知是来寻师叔的,徒子让他到客堂等候,他却死活不肯,定要候在外面。呵呵呵,徒子自打开堂子迄今,还没见过介正经的男人哩!”
“是我的不是了,”陈炯苦笑一声,“留给他这个门号时,应该讲明啥地方才是!”
“师叔,”炳祺压低声,“瞧见他了,徒子这也想起大小姐的事体,师叔哪能个办哩?”
“你有啥个主意没?”
“叫徒子来讲,”炳祺压低声音,“就看师叔看重哪一宗了。要是师叔看重兄弟,就将大小姐让给姓伍的,要是师叔看重大小姐,就不能让!”
“呵呵,”陈炯笑道,“要是师叔二者都看重哩?”
“这这这,”炳祺拍拍脑门,“师叔这不是让炳祺作难吗?”
“你呀,”陈炯指点他的脑袋道,“用用这个!”
“徒子这不是??”炳祺挠会儿头,“大小姐只有一个,师叔与伍挺举却是两个,双凰争凤,师叔没有其他选择呀,要么是大小姐,要么是兄弟!”
“师叔问你,”陈炯紧盯住他,“师叔赠送宝刀的是啥人?”
“这还用问,大小姐呀!”
“那天在伍兄那里见到的那个女子,又是啥人?”
“她就是大小姐呀,徒子敢对天发誓!”
“呵呵呵,”陈炯笑道,“如果师叔没有记错,那日伍兄介绍她时,叫她葛小姐,在下这也打听清爽了,她还真就是葛小姐,她有个老阿公是算命长者,住在老城厢的一个小胡同里,偶尔会在清虚观里做些营生。”
“天哪!”炳祺惊叫一声,又捂住嘴,压低声音,“难道是太??师太?”
“我敢肯定,老先生就是!”陈炯断然说道。
任炳祺倒吸一口气,良久,道:“师叔,若是此说,我这就禀报师父,我们上门??”
“千万不能,”陈炯摆手止住,“师太既然如此,是成心不想让人说破,我们这去说破了,就等于赶师太走,既不忠,也不孝!再说,师太成心归隐江湖,一旦离开此地,我们再想去寻,岂不更难了?眼下最好,他在明处,我们是在暗处!”
“好,炳祺听师叔的!”
“记住,此事体谁也不可讲,包括你家老头子!”
“炳祺晓得。”炳祺似又想起方才的话头,凝眉,“师叔,炳祺仍不明白,葛小姐也好,大小姐也好,他们仍旧是一个人呀!”
“呵呵呵,”陈炯乐了,“一个是大小姐,一个是葛小姐,怎么会是一个人呢?”说着起身下楼,“走,会会伍兄去!”
二人出来,请挺举进去叙话,挺举婉拒,站在街边将商团事体简要讲了,要陈炯尽快拿出一个组建与训练草案,商会最快会在下周议决。
陈炯做梦也没有想到商会竟然这么快就有回应,朝挺举连连拱手:“筹建方案在下早已有数,三日后必定亲手交给伍兄!”
果然,在第三日傍黑时分,陈炯就将一份洋洋洒洒近万言的商团招募、训练方案起草出来,亲自交给挺举。二人赶到茂平谷行后堂客厅,对草案商讨到半夜,挺举根据商会情况略加润饰,形成一份切实可行的商团章程草案。
“呵呵呵,”陈炯掂掂方案,看着挺举笑道,“方案成了,伍兄也别忘记在下所求哟!”
“陈兄有何求?”挺举倒是怔了。
“赏口饱饭吃哟!”
“呵呵呵,这是自然。说真的,领兵打仗,还没有能比陈兄更合适的人选呢。”
“伍兄可知如何举荐在下?”
挺举这也想起杭州发生过的旧案,且他刺杀丁大人就发生在钱业公所,商会里无人不晓,如果推荐上去,真还??
“这??”挺举略作迟疑,“请问陈兄,如何推荐为妥?”
“在下更名但不改姓,就叫陈火吧。”
“呵呵呵,”挺举笑道,“好名字哩,没有火,就不会有炯。陈兄写个简历交给我,如果商团事体顺利,在下就向祝叔、鲁叔举荐陈兄!”
众业公所斜对面,苏州河边,是一家日本人开的高档宾馆。
宾馆顶楼有一套宽绰、奢华的客房,麦基面窗而坐,专心致志地瞭望远处的苏州河与黄浦江水景。水是浑浊的,江面汽船如梭,不时有汽笛传来,嘹亮而悠长。
玛格丽特坐在一张书桌后面,面前摆着一台打字机。
里查得站在麦基背后,手里拿着一厚摞材料,目光虽也跟随麦基,但对远处的漂亮水景显然并无兴趣。
“You've made a very good start, Richard.(里查得,你开出个好头了。)”麦基说道。
“Thank you, sir.(谢谢,先生。)”
“Now, listen to me,(现在,请听我说,)”麦基仍旧给他个背,两眼望着水面,“according to our plan, to go on with the game,three things need to be done. The first is...(按照计划,游戏再玩下去,就当去做三件事,其一??)”听到打字机响,摆手止住玛格丽特,“to have the Announcement of HSBC get published on all the local newspapers, the second is to have the Chinese get mad with the rubber shares, and the third is,”略略一顿,“to have Maosheng highly involved in the rubber shares.(将汇丰银行的公告刊登在各大报纸上;其二,让中国人为橡皮股票发狂;其三,让茂升深度卷入。)”
“Mr. Lu feels a little concerned according to Mr. Fu.(听傅讲,鲁有点儿紧张。)”
“I see, he has a hard Wu.(是哩,他背后有个难对付的伍。)”
“How to deal with Wu?(如何对付伍?)”
“Leave him to me. (留给我吧。)”
“Thank you, (多谢,)”里查得给麦基个笑,“the only problem at present is, how to erase Lu's concern?(眼下还有一个问题,如何消除鲁的疑虑?)”
“Get in touch with Lu's rival.(联系鲁的对手。)”
“Lu's rival?(鲁的对手?)”里查得一怔,“You mean, Mr. Peng?(你的意思是,彭先生?)”
“That's right.(正是。)”
“Great idea!(妙啊!)”
“Anything else?(还有事吗?)”
“Nothing else, sir.(没有了。)”
“Good luck to you.(祝你好运!)”
里查得扬手道声拜拜,匆匆开门出去。玛格丽特送到门口,看着他走远,锁上房门,返回打字机前坐下。
“Dear Miss Margret, (玛格丽特小姐,)”麦基转过身子,面对玛格丽特打个响指,“it's your turn now. Let's go on with our exciting stories about the God-given Rubber, the most magic material in the world! (现在该你了。来,让我们继续书写橡皮的动人故事吧,它可真是上帝赐予这个世界的最富魔力的物质啊!)”
“Mr. McKim, (麦基先生,)”玛格丽特忽闪几下大大的蓝眼睛,“Can I ask a question?(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Of course you can.(当然可以。)”
“What shall we do if the Chinese have no belief in our stories and no interest in our rubber shares?(假使中国人不相信我们的故事,对我们的橡皮股票不感兴趣,该怎么办?)”
“Haha(呵呵),”麦基冲她竖下大拇指,笑了,“a very good question. If so, for you, the best choice is perhaps to get a gentleman, to marry him, to bear children with him, and to build a happy family. For me,”转过身去,指向远处的江水,“the most romantic way is to swim there, to dive deeply right under the yellow water.(很好的问题哟。假使如此,于你,最好的选择也许是寻到一个绅士,嫁给他,生儿育女,构建一个幸福家庭。至于我,最浪漫的方式是游到那儿,深深潜入那片黄水之下。)”
离开麦基,里查得赶到汇丰银行,拉上大班助理来到申报馆,约定于头版核心位置刊登汇丰银行公告,之后又马不停蹄地驰往茂升,将顺安约出,将橡皮股的“核心机密”略略剧透一些。让茂升“深度卷入”的现实一步,是让那余下的一万五千两银子贷款变为股票,再由茂升钱庄来承办中国人购股。
这些日子下来,里查得越来越叹服麦基的思路,中国人好奇,爱学,争不足而弃有余,服从但不信任洋人,让中国人来买橡皮股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中国人自己来卖,而在让中国人来卖之前,又必须让中国人从内心深处相信这个神话,且让他们“眼见为实”。
翌日,上海《申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一整版的汇丰银行公告。公告分中英文两块,中文一块里赫然写道,汇丰银行为华森橡皮作保,任何华森橡皮股票的持有者,皆可持股票前往汇丰银行柜台抵押相同数值的银行现钞。
当顺安将公告呈送鲁俊逸时,俊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真如汇丰所言,橡皮股票就不再是虚的,而是等同于庄票的实物!
鲁俊逸不敢怠慢,再次召集各大把头前来议事厅谋议。
“鲁叔,潘叔,诸位同仁,”顺安将华森拓殖公司折算的三千股华森股票摆在桌案上,又将《申报》公告摊开,声音富有磁性,“这些股票是我们钱庄用一万五千两银子换回来的,从今天开始,我们随时可以拿着它们到汇丰银行兑回一万五千两银子!”
众人面面相觑。
“诸位同仁,”顺安目光落在一直反对此事的大把头身上,“据密斯托里查得所讲,到目前为止,在这上海滩上,在全中国,华森橡皮股票只有三家拥有:一是众业公所,股票是他们印出来的;二是华森公司,股票是他们发行的;三是我们钱庄!”
“晓迪呀,”老潘不相信地望着他,“你是讲,连洋人们也没有?”
“潘叔呀,”顺安回他个笑,“你想想看,这股票还没发行呢,洋人哪能有哩?”
“那??啥辰光发行?”
“报纸上写着哩,”顺安拿过报纸,指着一处日期,“从这个月十五日开始,凡是想买华森股票的,就到众业公所和华森拓殖公司领取认购券,认领三日!十八日,持认购券到汇丰银行兑换股票!”
“啥叫认购券?”大把头显然没有听过这东西。
“顾名思义,”顺安指着这几个字,“就是认领购买股票的券呀。”又压低声音,目光落在鲁俊逸身上,“鲁叔,听里查得讲,股票一般是发给洋人,供应较足,不用认购券。这次不同,也发给中国人,中国人多,有意购买的人自然也多,而股票总量是一定的,票少人多,或会产生拥挤,产生不公,产生欺诈。为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华森公司先发认购券,只有拿到认购券的人,在开盘之际,才有资格购买股票!”
俊逸微微点头。显然,顺安不是瞎讲,众业公所的股票的确未曾发卖给中国人,此番售卖,难保不出现拥挤,洋人未雨绸缪亦非无稽之谈。
“晓迪,”俊逸看向他,“照这公告上讲,发行价是每股八两,你这讲讲,啥意思?”
“就是到十八日开市,每股卖八两银子,我们是原始股,五两。”顺安压低声音,“鲁叔呀,无论如何,前后不过熬几日,待十八日一到,三千股出手,就是九千两呀,介好的生意,天底下哪儿寻去?”又拿出另外一万五千两的贷款凭据,摆于几案,“依晓迪之见,时不我待,趁机会尚在,将这一万五千两也折作股票!”
“可这??上次没折算,今朝却去折算,叫里查得哪能个想哩?”
“鲁叔呀,这事体不关里查得,是麦总董看上咱家钱庄了,再说,鲁叔还是洋行首席江摆渡哩,这点面子,里查得哪能不给哩?”
“诸位,”俊逸吸口长气,看向众人,“晓迪提议将这一万五千两再折作股票,你们有何异议?”
众把头互望一阵,无不看向老潘。
“晓迪的话,我信,”老潘先给顺安一个肯定,接着话锋一转,“洋人的话,我不全信,尤其是这个麦基。上次庄票的事体,就是麦基他们干的,早晚想起来,我这身上就出鸡皮疙瘩。”
老潘的话,无疑代表了其他把头。见是师父否定,顺安不好再讲,嘴巴吧咂几下,无奈地看向挺举。
挺举正将一张股票拿在手里,仔细读着上面的文字。
“挺举呀,”俊逸看过来,笑笑,“你看到什么了?”
“是洋文,看不懂哩。”挺举回他个笑。
“嘿,洋人也真是糊涂,”俊逸苦笑一声,“既然要卖给咱中国人,就该写上中文,总得让人看明白才是!”转对顺安,“晓迪呀,你潘叔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就听你潘叔的吧。不过,这事体也得留个后手,你先告诉里查得,让他把股票给咱留着!”
“这??”顺安现出难色。
“你寻个托词,把事体推在鲁叔身上,就讲鲁叔有半月没在钱庄了,这事体要待鲁叔回来才能决定!”
“欧凯。”
南京路华森拓殖公司的大门外面,围着数百看热闹的中国人。
左右两侧各放一张桌子,有人在免费发放认购券。大门敞开,但门口竖枪般站着四个印度阿三,在四个阿三中间,是一张巨大的告示板,上面写道:“凡认购五百股以上者,可进拓殖公司一观!”
一个负责外场的中年汉子站在公司气派的大理石台阶上大声吆喝,招揽路人:“女士们,先生们,领券不收钱,领五百股者,可进此门,一睹橡皮风采。在下看过了,当真是世界瑰宝,让人眼花缭乱啊!”
按照开市每股八两折算,购买五百股就需要四千两,绝不是一笔小数,是以围观的华人越聚越多,却没有一人敢领此数,进大门一睹风采。
一个有钱人实在忍不住好奇,牙关一咬,走到前面:“奶奶的,豁出去了,不就是四千两银子嘛,我就领他五百股,能有什么大不了的?”
公司职员询问过他,为他登记造册,将五张一百股的认购券双手递到他手里。一个印度阿三走过来,迎入大门。
所有观众无不伸长脖子,候他出来。
时光于此时突然间长得烦人。感觉过有不晓得多少辰光,那人才从大门里走出,一脸的满意与惊诧。
众人纷纷围上,七嘴八舌:
“喂,这位哥们,看到啥宝贝了?”
“快讲讲看,橡皮都是啥样子?”
“橡皮好吃不?”
??
“啧啧啧,”那人连声惊叹,“真他娘的开眼界哩,我这讲给你们听呀??”
几个有钱人没再听他多讲,直接走向桌边。
十七日晚,日租界一家艺伎馆里,里查得与章虎盘腿坐在榻榻米上,几个日本艺伎或斟茶,或操琴瑟琵琶,或唱,或舞,欢声笑语不绝。
一曲终了,里查得摆手,几个艺伎退出。
里查得将一张八百两的庄票摆在几上,又拿出一张一百股的华森橡皮股票摆在旁边。
章虎不动声色地看着里查得。
“章先生,”里查得盯住章虎,“这是预付酬金,两样东西等值,由你任选。无论你选什么,在事情办妥之后,我都将另外支付同等数额。”
章虎的手毫不迟疑地伸向股票。
“章先生,”待他拿起,里查得微微一笑,“讲讲看,你为什么选择股票?”
“章某是个赌徒!”章虎回他一笑。
“好,”里查得竖起拇指,“我喜欢赌徒!”
“请问洋先生,”章虎将股票纳入袋中,“你要章某做些什么?”
“玩几日游戏!”
“呵呵呵,”章虎看向里查得,“章某此生最爱玩的就是游戏,洋先生,请讲,这游戏是哪能个玩法?”
“从今朝开始,你须听我安排!”里查得讲完,推过一只箱子,“我们的首批股票将由汇丰银行承办,认购券已经发放不少,这里是三万股,你全拿去,安排你的徒众前往汇丰银行兑买股票。”
“就做这事体?”章虎大是惊讶。
“呵呵呵,明朝就是这事体!”里查得笑应一句,“章先生,明日早晨,汇丰银行热闹不热闹,就看章先生的演出了!”
“洋先生,你想哪能个热闹法儿?”
“随你怎么热闹都成,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抢劫、偷窃,公然违犯大英租界法律!”
“呵呵呵,”章虎将箱子划拉过来,踏在脚下,“洋先生放心,我们都是大清朝的守法良民!请洋先生传话给汇丰银行,让他们将大门换个结实点儿的,甭让我那八十个弟子挤爆才是!”
“八十弟子!”里查得先是一怔,继而合不拢口了,冲他竖拇指大赞,“太好了,不愧是傅先生的朋友!”
“洋先生,”章虎将里查得给他的一百股橡皮股票拿出来,掂了几掂,“我出八十人,要为你忙活几日,只有这些纸头,怕是??”
“我明白,”里查得笑笑,指下他的箱子,“你可以炒卖这箱纸头!”
“哪能个卖法?”章虎怔了。
里查得招手,章虎凑过来,听他耳语有顷,乐得合不拢口,连道:“欧凯欧凯!”
次日凌晨的外滩,汇丰银行大门还未打开,章虎一伙就拿着认购券在附近的街道上蹿来跑去,呼七唤八,闹得沸沸扬扬。部分拿到认购券的陆续赶来,但并没有几个是真心拿银子来换股票的,多为瞧个热闹。
太阳出来时,汇丰银行大门前面已集聚起一百多号人,有人呼叫排队,有人开始插队,几个印度阿三在现场维持秩序。章虎的人纷纷赶过来,开始挤队,场面变得闹哄、纷乱。领到认购券的人越来越多,现场黑压压的。
场地一角靠墙处摆着两张桌子,华森公司几个职员仍在发放认购券。闻讯赶到的人越来越多,经过多日报刊的张扬,上海人大都晓得橡皮股了,又逢首日开市,轧闹猛的人纷至沓来,商会里也有不少商人前来观望。街道开始拥堵,有人因挤队打起架来,秩序愈加混乱。部分观望者触景生情,反而害怕错失机会,也去华森职员那儿领取认购券,挤去排队。
要领认购券的人多起来,有人呼叫排队。
一个在附近大街上睡觉的老乞丐被人们吵醒,晕头晕脑地跑来看热闹。
章虎瞄见,恶作剧的念头油然升起,便走到老乞丐跟前:“讨饭的,辰光介早哩,你这就来讨生活了?”
老乞丐望着黑压压的人群:“他们这是做啥哩?”
“抢认购券哩,”章虎指着前面的桌子,“快去领吧,再晚就没了。”
“认购券是啥物事?”老乞丐一脸懵懂。
“好物事哩,好换馒头,快过去排队!”
“嘿,能换馒头,这倒是好哩!”老乞丐赶忙过去排队。
好不容易轮到老乞丐了,发券者瞄他一眼,皱起眉头:“去去去,你个讨饭的,要这个好做啥?”
“换馒头呀!”老乞丐挠挠头皮,大是不解,扭头见章虎跟过来,急道,“他们不给!”
章虎凑到发券者跟前,悄声:“人不可貌相,甭小瞧这个老头,看似乞丐,实则是个大富翁哩!”
“晓得了。”发券者瞄他一眼,递给老乞丐一张百股认购券。
老乞丐拿到认购券,转问章虎:“馒头在哪儿换?”
“拿这个纸头到那个大门里领!”章虎指着排向银行大门的队伍,悄声,“往前面挤,排在后面,怕就轮不上你哩。”
看到人山人海,老乞丐二话没说,迈开老腿直向大门挤去。
远远望去,汇丰银行大门外,众头攒动,人声鼎沸。太阳一竹竿高时,银行大门开启,队形早被冲乱,人群拥入,章虎一伙更是发挥超常,怒骂撕扯,引发一个个冲突,有几个更在营业厅里互相撕打,使场面愈加混乱。
一队持枪巡捕在王探长的引领下急赶过来,吹着哨子,冲进营业大厅,将所有人员赶出银行大门。接着,吱呀一声,银行大门紧紧关闭。
众人正自错愕,银行里有人走出偏门,朝大门贴公告,是中文的。
众人纷纷挤过来阅读公告,有人大声朗读:“鉴于华森橡皮股票融资、缴款过于踊跃,本银行暂停营业一日。橡皮股票何时可以兑换,敬候通告。”
又是中饭辰光,老乞丐拿着一只黑碗,走在一条偏僻的街巷里,挨门讨要吃的。
两个人指指画画地追寻过来,其中一个盯他一会儿,兴奋地对另一人道:“兄弟,看样子就是这个老家伙了!”
另一人点下头,冲老乞丐叫道:“喂,老要饭的!”
老乞丐怔了下,盯过来。
“前天早晨在外滩,听说你领过一张纸头,那张纸头哩?”
老乞丐果然在怀里掏摸一阵儿,摸出一张认购券。
“老人家,”另一个年岁略大些,朝背后扫一眼,见阿黄与一个记者模样的走过来,紧忙改过语气,“这张纸头反正你也派不上用场,送给我,好不?”
老乞丐摇头。
“哎呀,老人家,你这讲讲,你要这张纸头好做啥?”
老乞丐将认购券小心翼翼地藏回怀里:“换馒头吃!”
“这倒是哩!”年岁大的朝同来的小伙子努下嘴,“还不快去买些馒头来。”
小伙子转身,不一会儿,拿着一包五只大白馒头飞跑过来。
“老人家,”年岁大的将馒头在他眼前晃晃,笑容可掬,“五只大白馒头换你一张纸头,成不?”
老乞丐两眼发直,连连点头,从怀里掏出纸头。
年岁大的将馒头递过去,从老乞丐手中拿走认购券。老乞丐显然害怕对方反悔,急不可待地将五只馒头各啃一口,紧紧抱在怀里。
跟在阿黄身边的那人看个真切,按动快门。
翌日上午,顺安拿着几张报纸匆匆走进鲁俊逸的经理室,不无兴奋道:“鲁叔,你看!”
“我已经看过了。”俊逸扫一眼,将报纸放到一侧,从案头一沓子报纸里取出一张,“正要寻你哩。”
“鲁叔呀,”顺安不无遗憾,“昨天在汇丰,我是从头看到尾,嘿,那个阵势,简直就像是开庙会,刚开始,汇丰还有红头阿三维持队伍,到后来,阿三一个也不见了,不晓得被挤到哪儿去了,若不是王探长带着人马来,不定银行的大门就被挤爆了呢!”
“唉,”俊逸长叹一声,“看来你是对的,鲁叔失算了。”指向报纸上刊出的华森公司公告,“你听听,‘为满足所有领取认购券者的投资心愿,经华森公司董事会议决,认购不足百股者,可持现款直接前往众业公所,实购30%,认购百股以上者,实购20%,凡是没有领取认购券者,不得购股。购股地址由汇丰银行改为众业公所,购股日期由众业公所另行公告。’”扔下报纸,苦笑一声,轻轻摇头,“真正没想到哩!”
“是哩,华森这个公告出来,听说市面疯了,反过来争抢认购券。鲁叔请看,”顺安将另外一张报纸拿出来,指着上面一个乞丐老头,“免费发放时没人愿领,乞丐都能领,这辰光,听说黑市上一张百股认购券得花五两银子去买,看这行情,再过几日,怕是五两也打不住哩!”
俊逸看向报纸上那张照片,见一个老乞丐抱着五只大馒头,另一人手中扬着一张百股认购券,标题赫然是“五两银子换五只馒头,老乞丐乐得合不拢口”。
俊逸却乐不出来,两手紧紧按在额角上,表情痛楚。
“鲁叔?”顺安急了。
“许是伤风了,头有点儿痛。”俊逸给他个苦笑。
“要紧不?要不,小侄这陪鲁叔看看大夫?”
“不打紧哩。”俊逸松开额头,笑笑,“晓迪呀,麻烦你去趟华森,见见里查得,将那一万五千两也折算股票!”
“鲁叔呀,我要的就是您这句话哩!”说罢,顺安转个身,飞跑出去。
半个时辰后,顺安回到钱庄。
见他脸上沮丧,俊逸心里一沉:“没见到他?”
“见到了。”顺安嗫嚅道,“可里查得说,这辰光不行了,他做不了主!”
“咦?”俊逸急了,“你没讲我在忙商会的事体?”
“讲了,”顺安苦笑一声,“晓迪能讲的全都讲了,可你晓得,洋人就是洋人,不听解释。鲁叔呀,晓迪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哦?”
“听里查得讲,华森橡皮过几日正式在众业公所开盘,由于想买股票的人实在太多,华森公司与众业公所将开盘价由原来的八两上调到十两。唉,鲁叔呀,三千股,整整一万五千两银子,眨眼工夫,这就没了!”
俊逸再次吸口冷气,一手按住一边额角,有顷,抬头:“这事体完全办不成了吗?”
“不晓得哩,”顺安应道,“里查得只是说,他做不了主,看样子,要想办成,得寻麦基!”眼珠子一转,“对了,让挺举阿哥求求麦小姐,由麦小姐出面,保准能成!”
听他提到麦小姐,俊逸脸色一沉,摆手:“算了吧,不就是少赚一万五千两银子吗,舍这个脸做啥?”略顿,“对了,晓迪呀,从今朝开始,啥事体你也不要做了,盯住橡皮股票!”
“好咧!”
开盘之日,众业公所内人头攒动,两个窗口上分别写着华森橡皮,其中一窗是洋人,另一窗是华人。洋人队伍较短,有二十多人,秩序井然,华人队伍却排很长,一直排到外面大街上。无论是洋人还是华人,每人都拿着认购券。
手续办理很慢,每一个人都要折腾至少几分钟甚至超过一刻钟辰光,这无疑使排在后面的更是焦急。
顺安远远靠在大门外面的梧桐树上,时不时地瞥一眼购票长队,目光落在杂在队中的阿黄身上。顺安晓得他已买过三轮了,这是第四轮,便会意地朝他笑笑。阿黄朝他扬下手中的认购券,打出一个响指。
许多上海人聚在大门两侧看热闹,其中一个是庆泽。
自到上海之后,庆泽就跟老潘学做钱庄生意,养尊处优惯了,其他生意既看不上,也做不来。倒卖私货的事情发生之后,上海钱业容不下他了。老家宁波他无脸回去,就改名换姓前往苏州闯荡。然而,在他这把年纪,学徒人家不收,而要应聘把头,他就必须报上师父名号,而已被老潘除名的他,不敢造次,在那儿闲逛月余,不无失落地回到上海。
时光一天一天过去,庆泽晓得坐吃山空,但干着急寻不到活路。
就在此时,上海滩上出现了橡皮股票。
可以说,这只股票开始宣传时,庆泽根本就不看好。尤其是得知华森拓殖就是原来的麦基洋行时,庆泽愈加小心。他晓得麦基,晓得里查得,更晓得他们的生意并没有想象中的好,因而,在华森公司免费发放认购券时,他就在人群里站着,没有上前领取。
然而,事实并未如他所料,股票尚未开盘,股价就一路走高,连一张乞丐都可领取的认购券竟在黑市上疯卖到十两银子,真让庆泽始料不及。直到这日开盘,亲眼见到排队盛况,庆泽方才后悔莫及,走到大门口,对维持秩序的印度阿三讲几句英语,说他进去寻人。阿三见他能讲英语,摆手放行。庆泽阔步进厅,目光巡视一周,落在旁边股价标牌上。
标牌上赫然写的是:“华森股票,票值每股十先令,开盘价每股十两规银,凭认购券购买,认购券每百股许购十股!所有认购券,三日内有效,过时作废!”
“乖乖,”庆泽暗暗打个算盘,吧咂几下舌头,“十先令是五两,一开盘就是十两!”眼珠子又转几转,“只是,如果这些股票在手中,没人来买岂不是白搭进去了?无论如何,银子是银子,股票是股票!”
庆泽在厅中晃悠一圈,走出来,正在寻思应对,远远望见顺安站在梧桐树下东张西望,眼睛一亮,疾步过去,想向他打听个实情。就在此时,两辆黄包车停下,俊逸、老潘跳下车子。顺安显然是在巴望二人,迎上去边打招呼边将车夫的钱一并付了。庆泽没脸去见他俩,紧忙拉下帽檐,隐没在人堆里。
顺安引俊逸二人进厅观看一会儿,复走出来,重新叫过三辆黄包车,直投南京路,在麦基洋行楼前停下。
望着焕然一新的华森拓殖大门,俊逸、老潘皆是感叹。顺安走向门口,与印度阿三说了几句话,阿三进去通报,不一会儿,里查得匆匆下楼,迎接俊逸进门。
在公司大厅,里查得引导俊逸、老潘参观展厅,逐一解释这些橡胶产品的性能与功用,让他们一一抚摸。
耳闻目睹加手触,二人嗟叹不已。
“鲁叔,师父,”顺安凑上来,不无自豪道,“晓迪没有虚说吧!”
“唉,我来迟了!”俊逸长叹一声,转对里查得,“我想求见麦总董,敬请引见!”
“非常遗憾,”里查得摊开双手,“麦总董今朝不在,一大早就去花旗、麦加利两家银行洽谈业务去了。”
“这??”俊逸看一眼老潘,老潘看向顺安。
“密斯托里查得,”顺安给出个笑,“鲁叔、潘叔此来,是想谈一下折算??”
“我晓得了,”里查得打断他,转对俊逸,“鲁先生,昨日,麦总董夜半给我电话,说是华森公司董事局刚刚开完董事会,鉴于此前与茂升钱庄的友好合作关系,董事会同意将余款一万五千两折算成股票,但每股不能是五两了。”
“是多少?”老潘急了,“不会是??十两吧?”
“也不是十两,是八两。八两是开会前的盘价,十两是开会后的盘价。麦总董是在开会前提出这事体的,后来涨价时,其他总董对此提出异议,是麦总董坚持,才最后定下了。”
俊逸、老潘相视一眼,各自嘘出一口气。
“谢谢您,谢谢麦总董!”顺安拱手谢过,压低声音,“请问密斯托,花旗、麦加利两大银行请麦总董去,又有大事体了?”
“呵呵呵,是哩,”里查得亦压低声音,“不瞒诸位,麦总董是与他们商谈股票抵押诸事。华森股票业务眼下全由汇丰承办,单是佣金就是一笔可观收入,两家银行有意分享。一则业务太多,汇丰银行忙不过来,二则麦总董不希望汇丰一家独享。无论如何,就生意而言,竞争总是好事体,对不?”
“真是好事体,”俊逸呵呵笑几声,接过话,“请问密斯托,华商购股也是汇丰承办吗?”
“眼下暂时由他们承办,但股票销售火爆,另外,我们新近又买了一个更大的橡胶园,不久之后,可能发放新的股票,汇丰银行一家肯定承接不了。麦总董早已定下,银行只承接洋人股票,华股仍由中国钱庄承接。”
“太好了!”鲁俊逸喜道,“今朝我与潘协理来,就是商议这桩事体。前番听晓迪讲,麦总董已将华股承办权授予我们茂升钱庄,何时可以签约?”
“非常遗憾,”里查得耸几下肩,“麦总董确实讲过此话,只是,我们一直未能等到鲁先生的回话,以为茂升钱庄不愿承接,就找善义源了,听总董讲,已经谈妥,就这几日签约。”
“这这这,”俊逸震惊,拱手致歉,“实在对不起,前些辰光在下只顾忙于商会事体,就将此事交给晓迪了!”说着转向顺安,声音严厉,“晓迪,你是哪能讲哩?”话音落处,向他使个眼色。
顺安会意,一拍脑袋,朝里查得不无懊悔道:“哎哟哟,瞧我这记性,鲁叔的确讲过要我给麦总董一个回话的,说是愿意承办,可我??”夸张地捶打几下自己,转对里查得,连连拱手,“密斯托里查得,一切都是晓迪的错,请您务必转告麦大人,要不然,我这??呜??”眼泪立时涌出,抽咽几声,拿袖子抹去。
顺安是演戏的出身,表演功夫几乎是天生的。里查得真的让他蒙住了,冲他连连摇头:“No crying!(不要哭!)”又转对俊逸,“我向麦总董再提申请,明日给你答复,OK?”
三人谢过,忐忑不安地走出洋行。
送走几人,里查得反身踏上三楼,敲开总董室,对麦基道:“It's OK. They are gone!(一切顺利,他们走了。)”
麦基挪动椅子,探身窗前,隔玻璃望着鲁俊逸三人正沿南京路晃晃悠悠,渐去渐远,冲里查得打个响指:“Now, go to 520yd.com.(你可去见彭先生了。)”
从华森回来,鲁俊逸立马将所有把头召到一起,商议承办华股事宜。
“唉,”俊逸长叹一声,“这次橡皮股票,”看向顺安,“我对晓迪的建议未予重视,现在看来,是赶不上趟了。”
“老爷,不能怪你,”老潘苦笑一声,揽下责任,“一切都怪我,是我赶不上趟,晓迪苦苦劝我,都让我压住了。”又转向众人,“不瞒诸位,今朝我与晓迪跟从老爷到众业公所和华森拓殖公司走了一趟,大开眼界。原来以为报纸上是瞎吹,现在看来,真还讲不清爽哩,没准这未来世界,真就是个橡皮世界!你们有空,也可以分头过去看看,开开眼界。上海滩哪,真就是一日三变,我们都得放开眼光哪!”
见俊逸与老潘都这么讲,众把头谁也不再多话,纷纷看向顺安,觉得他是这个钱庄里眼界最开阔的人了。
“鲁叔,师父,”顺安不失时机地站起来,“要说责任,是我最大。这事体鲁叔早就交给我了,从麦基洋行到华森拓殖,都是我一人在跑,对这次橡皮股票,我一开始就清爽,就晓得是个大机会,可是,我没能将这些向鲁叔和师父表述清爽,也未能坚持己见,未能坚决要求将一万五千两贷款转化成股票,致使钱庄在短短几日里损失九千两,这个责任,我负!”
顺安这几句,表面是揽责,实则是表功,但此时他光环在身,没谁来计较这个,纷纷出言夸他。
热闹一阵,俊逸摆手止住,郑重宣布:“我决定,只要华森拓殖公司正式授权,我们就倾尽全力,承办华股。”又转向老潘,“老潘,还有多少库银?”
老潘看向库房把头。
“回禀老爷,连压库储备算进来,约三十五万两。”
“除去压库储备,”俊逸眉头微皱,“若是承办,这点儿钱就不够了。”对老潘,“你再清算一下,把所有资金都算上,看看可以动用的究底有多少。我这就寻老爷子去。”
广肇会馆内,刚从牢狱之灾解脱出来的彭伟伦动作缓慢地温水煮茶。他的对面坐着马克刘,时不时地端起茶盏品啜一口。
“唉,”彭伟伦放下温壶,长叹一声,看向马克刘,“时事变迁,风云难料,我给查老头子来了个大闹天宫,查老头子还我一个五指压顶,在下本想在那五指山下守满五百年,岂料又让他祝合义保释出来,人生真他妈的如戏啊!”
“彭哥,”马克刘恨道,“这笔账非算不可,这口气非出不可,老弟这都一一记着哩!”
彭伟伦没有理睬他,顾自怅然:“这个祝合义不仅保在下出来,又让在下出任商会的列席议董和列席总董,虽说没有表决权,却也算是抬举彭某了。”
“哼,他这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真也好,假也好,彭某都得领他这个情。听说为保在下出来,祝合义几番出入道台府不说,又躬身南京求告两江总督!能够打出这一拳,此人好功夫嗬!”
“彭哥,”马克刘气恨难平,“就算姓祝的能有这点儿人味,那个老东西也太霸道了!彭哥呀,你有所不知,那日查老头子突然召开议董会,突然发难,那叫个气势汹汹啊!他算什么东西,连个议董也不是,竟然到商会里指手画脚,颐指气使!我都给他记着哩,彭哥,你出来了,老弟也就无所顾忌了,这就给他个color see see(颜色看看)。”
“你这个color,早晚要让他们see see,只是眼下不可。”
“彭哥?”马克刘怔了,“我们??就这样忍气吞声?”
“唉,”彭伟伦长叹一声,“不忍能有什么办法呢?韬光养晦,君子之道啊。”
“Why?(为什么?)”
彭伟伦拿出一信摆在桌上:“老弟看看,这信是打河南安阳来的。袁大人下野还乡,穆先生陪大人这在河南安阳的洹上村头垂钓呢。袁大人尚且如此,你我又能如何?”
“这??”马克刘倒吸一口气,“要是袁大人一直钓鱼,我们岂不永无出头之日了?”
“坐以观变吧。朝堂历来为翻云覆雨之地,只要袁大人不死,一切就都难说。”
马克刘正待接话,广肇会馆的襄理由外面匆匆走进,小声禀报:“老爷,钱庄沈协理求见!”
“叫他进来。”
“老爷,”善义源协理进来,哈腰禀报,“麦基洋行的里查得先生今朝到访,说是华森橡皮股票正式在众业公所上市,麦基先生有意让善义源承办部分业务。由于麦基洋行先行不义,小的没有允准,但给了他个活口,特来请示老爷定夺。”
“麦基?华森橡皮?”彭伟伦转对马克刘,“老弟,你哪能看待这事体哩?”
马克刘想也没想,当即回道:“可做。”
“哦?”彭伟伦身体前倾,目光征询。
“美国到处都建汽车厂,橡胶涨价,伦敦股市橡皮股票疯涨,麦基刚好赶到这个点儿上,真还把生意做大了。不瞒彭哥,连我们洋行也搅和进去。就这几日,洋行总董与麦基频频约见,几乎天天都在一起喝咖啡呢。”
“老沈,”彭伟伦凝思一会儿,转对协理,“为何只有部分业务?”
“另外部分给了老客户茂升钱庄。”
“哦?”彭伟伦长吸一口气,劲头上来了,“应允里查得!”待沈协理离开,转对马克刘苦笑一声,“嘿,真就叫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又与那姓鲁的碰上了!”
“彭哥,”马克刘恨道,“这次咱们摽个劲儿,整死他!什么狗屁东西,连个议董也不是,更没经过补选程序,就凭老家伙一句话,他竟就堂而皇之地把彭哥的缺给霸去了!”
“哈哈哈哈,”彭伟伦长笑几声,“老弟总是快言快语啊!对了,”看向马克刘,“听你前面提到商会要搞什么商团,讲讲看,什么意思?”
“是祝合义讲的,说是商会打算模仿租界里的万国商团,搞一个武装组织,由各家商帮行会出人出钱,忙时做生意,闲暇训练,说是可以加强商帮行会之间的相互了解,万一出个啥事体??”
彭伟伦微闭双目,陷入沉思。
“彭哥,”马克刘话锋陡转,“我打探过了,这主意不是祝合义的,是姓鲁的提议的。”
“呵呵呵呵,”彭伟伦睁开眼睛,豁然洞明,“姓鲁的提不出这个议,能够提出的只有一个人!”
“伍挺举?”马克刘脱口而出。
“是哩。”彭伟伦微微点头,“刘老弟,对这个事体,你是哪能个看法?”
“彭哥,”马克刘恨恨说道,“无论是何人提议,我们都不能跟着跑。四明掌握了钱把子,这又鼓捣枪把子,却让我们出钱出力,想得美哩!”
“老弟呀,”彭伟伦轻轻摇头,轻叹一声,“如果是挺举提议,他就比我们看得远哪。万国商团你是晓得的,自成立到现在,没见他们放过一枪,可老弟想想,哪个中国人不怕这个商团?为啥怕它?它的旗下有几百号子人,有几百杆子枪。没有这个商团在眼前晃来晃去,洋人的腰杆子就不会挺得那么直啊!”
“彭哥,他们靠的是兵舰!”
“呵呵呵,”彭伟伦笑了,“他们是有兵舰,可兵舰在全世界的大洋里到处游荡,没有一艘停靠在这黄浦江上,莫说是中国老百姓看不见,即使洋人想看一眼也是难啊!”
“彭哥是说,我们赞成?”马克刘小声问道。
“如果真能搞出这么个好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呢?再说,商会不是四明一家的,它属于上海各家商帮,风水轮流转,这钱把子、枪把子今朝握在他们手里,明朝呢?只要那个章程还在,商会里的那把大椅子就不会只由同一个人坐,是不?”
商会总理室的三人沙发上,并排坐着俊逸和挺举。
“挺举呀,”祝合义将商团组建方案拿在手里,看向挺举,“你这个方案我都看过了,也送呈老爷子审过,老爷子赞不绝口哩。”
“谢老爷子和祝叔抬爱!”
“其他没啥问题,只是??五千个人,五千条枪,这个阵势有点儿大,怕是通不过,我与你鲁叔商量过了,也征得老爷子同意,先从二千人开始,然后慢慢扩大,你意下如何?”
“听祝叔的。”挺举点头,“其实,五千人是个总体目标,刚开始,有一千人即可。”
“那就先从一千人、一千条枪开始,人越少越不扎眼,官府那儿也越好讲话,人多枪多,官府或会生二心哪!”
“是哩。”
“再有,我们都是经商的,这舞枪弄棒的,不懂行哪能成哩?”合义皱起眉头。
“是哩,我也在琢磨此事。”俊逸附和。
“这个我想过了,”挺举笑道,“自古迄今,兵在将,将在旗号。只要我们撑起大旗,有人有枪有钱,招个统兵教头就可以了!”
“是呀,”合义回他个笑,“我们缺的就是这个统兵教头。此人必须知兵,必须忠勇双全,必须人品端正,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哪!”
“祝叔,鲁叔,”挺举觉得辰光到了,拱手道,“若是此说,小侄倒是认识一人,或适合此任。”
“是何来路?”俊逸问道。
“此人姓陈名火,吴县人,书香世家,自幼却欢喜枪棒,几年前东赴日本,在日本一所陆军学校就读,接受东洋正规军事训练。此人胸怀大志,人品也还不错,是个帅才。”挺举简要讲过,掏出一份简历,“不瞒祝叔、鲁叔,这个方案就是此人提议并草拟的,在下不过是击鼓传花而已!”
合义看俊逸一眼,转向挺举:“你是哪能结识他的?”
挺举将他赴杭州大比结识陈炯的过程讲了个大要,道:“那夜我与陈兄都喝高了,谈起家国天下,列邦欺凌,尽皆感愤,交为知己,同路来沪。到沪之后,我投鲁叔,陈兄则东赴日本,决心修习日本军事,以武救国。不久前,陈兄学成归来,有同学劝他去天津投袁,他看不上袁,加之根基皆在南方,就回沪了。”
“如此甚好,”合义放下心来,“既是你的朋友,就用他做总教头。教练人手若是不够,我再到万国商团,请中华体操队派几个过来。”转对俊逸,“你安排一下,通知所有议董,明日晚七时开议董大会,就此事体进行表决!”
“好。”俊逸应过,略顿,看向合义,“还有桩事体,我吃不太准,这想听听你的意思。”
“啥事体?”
“华森橡皮股票,”俊逸说道,“这事体是麦基搞起来的,眼下闹成个景了。近些日子,听晓迪讲,麦基有意让我承办华股,我是麦基的首席江摆渡,前面合作虽有摩擦,也还过得去,如果不做,就怕磨不开面子,如果做,心里却又打鼓。”
“呵呵呵,”合义笑道,“洋人的事体,你比我强,不瞒你讲,商会里也都在议论此事,都要我拿主意,我还打算问你哩!”
“呵呵呵,你高抬我了。”
“俊逸呀,”合义敛住笑,长叹一声,“这事体我也不是没想过。不知怎的,一提到股票,我总会联想起二十多年前的阜康之灾!”转对挺举,“挺举呀,你思路清,对这事体是哪能个想哩?”
“祝叔,”挺举拱手,“我查询过了,洋人喜欢抱团,做生意多是靠发行股票起家,用股票将生意与东家分开。这有个好处,就是能把生意做大,比咱这里的单打独斗强。我没搞明白的是这橡皮,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都还是华森公司的一面之词,生意也是他们独一份。”
“是哩。”合义吸口长气,转对俊逸,“挺举所言在理,你既要承办,就是大事体,不可不慎重哪!”
“晓得了。”
议董会对商团议案的表决进行得意外顺利。沪上甬、粤两大商帮皆无异议,其他商帮也都见风使舵,几乎是一面倒地投下赞成票。
“诸位议董,”在众议董具名画押后,祝合义将正式定案放到案上,淡淡说道,“这个方案,包括商团组织的相关章程,于今晚全票通过,明朝就由商会出面,向道台、租界递交商团设立申请书。如获批准,商会将依此方案并章程筹建商团,届时,还望诸位动员各个商家出人出钱,积极训练。”
离开会馆,俊逸叫住挺举,跳上马车,郑重问道:“商团事体告一段落,我们叔侄得把心思移到钱庄里来。眼下钱庄最大的事体是橡皮股票,鲁叔实意问你,对这玩意儿,你究底哪能个看法?”
“鲁叔呀,”挺举笑笑,“昨日祝叔问起这事体,我全都讲了。就我所知,西人做生意,本钱多靠发股票,这个没问题,眼下我吃不准的是这橡皮,过去没见过哩。”
“呵呵呵,”俊逸也笑了,“没见过不怕,我初到上海滩,跟你和晓迪一样,啥都新鲜,啥都没见过,后来却用它们赚下不少铜钿哩。”敛住笑,“要照这说,股票可做,鲁叔打算豁出去,赌它一票!”
“鲁叔不是已经赌上了吗?”挺举又笑了,“三万两银子,全买股票了。”
“是全力承办华股!”俊逸转头吩咐车夫,“查老爷子府宅!”
听闻挺举也来了,查敬轩分外高兴,亲自迎出,扔下俊逸不顾,只一把拉住挺举的手,携手径至客厅,将他按坐在自己对面,凝视他良久,重重点头:“伍挺举,挺而后举!我四明后继无虞矣!”
挺举起身,拱手:“前辈偏爱,晚辈愧不敢当!”
“俊逸呀,”查敬轩转对俊逸,“来上海这些年,你也算做下不少事体。可无论你做下多少事体,查叔的眼都没热过。唯得挺举,查叔是暗生妒心哪!讲讲看,你是哪能发掘出挺举这个大才的?”
“呵呵呵,”俊逸咧嘴笑笑,“不瞒查叔,讲起这事体,俊逸是得益于您老了!”
“哦?”查敬轩倾身向前。
“自来上海滩后,俊逸一直以查叔为楷模。跟来学去,俊逸自叹弗如。俊逸暗叹,唉,看来,此生此世,查叔的生意经是难学到了。后来琢磨多了,俊逸终于悟出一个道道。”
“什么道道?”
“人哪!”俊逸看向坐在他身边的查锦莱,笑道,“查叔您是人精,又得锦莱兄这个人杰,如虎添翼。我呢,是猪八戒背个破箱笼,要人没人,要货没货,哪能攀比查叔您哩。唉,俊逸是越想越气馁,夜夜求告观世音菩萨。菩萨果然显灵,给我送来了挺举。呵呵呵,没想到竟然震到查叔您了!”
几人皆笑起来,挺举脸红,把头低下。
“呵呵呵,”查敬轩乐得合不拢口,指俊逸道,“你这嘴巴越来越润滑了!”
“查叔呀,”俊逸敛起笑,拱手道,“俊逸此来,是想再让查叔帮个忙。”
“你讲。”
“此地没外人,俊逸就向查叔托底了,”俊逸略略一顿,一脸真诚,“橡皮股票越闹越大,牵涉俊逸的钱庄了。橡皮股票是麦基洋行搞起来的,麦基与茂升是老交情,前不久,麦基又把俊逸聘为首席江摆渡,这几日,股票发行,麦基提出让俊逸承办华股,俊逸磨不过这个面子,只能承接,可承办华股,没实力吃不下来,俊逸回来盘算一下库存,自觉底气不足,思来想去,别无他途,只能来求查叔!”
“说吧,你要多少?”
“二十万两。”
“呵呵呵,”查敬轩连笑几声,“我还以为是二百万两呢!”转对查锦莱,“莱儿,给俊逸二十万两,再为俊逸储备三十万两,以防不测!”
“俊逸,”查锦莱笑笑,“待会儿我就打个电话,你安排人随时可到钱庄办理票汇!”
“查叔,锦莱兄??”俊逸朝二人连连拱手,甚是感动。
“俊逸呀,还有啥事体是查叔能够为你做的?”
“没了。”俊逸起身,“谢查叔!谢锦莱兄!”
送走俊逸二人,锦莱急切地看向查敬轩。
“莱儿,”查敬轩一字一顿,“马上安排人手,盯住橡皮股票,适时参与!”
“好哩。”
桌面上摆着一摞一摞的报纸,陈炯聚精会神地伏在案上,一张一张地翻看,边看边圈画。
任炳祺推门进来,正欲讲话,见他这般专注,忙又止住,但显然压抑不住亢奋心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边走边搓手。
“炳祺呀,”陈炯住笔,瞥他一眼,笑道,“你晃悠个啥哩,让人眼晕!”
“呵呵呵,”任炳祺凑过来,“师叔,您看完报纸了?”
“看样子,是有好事体哩?”
“是哩,”炳祺不无得意,“不瞒师叔,这几日倒腾华森橡皮认购券,白赚二千多,比闹腾码头来钱快多了。照此下去,再过半月,徒子保准稳赚五千两!”
“哦?”陈炯大是惊愕,“对了,今朝股票涨到多少了?”
“打烊辰光,是十五两七钱!”
“乖乖!”陈炯越发惊愕,情不自禁地吧咂几下嘴皮子。
“师叔,”炳祺凑前一步,“我咋觉得不靠谱哩,你说,就这一张破纸头,哪能介值钱哩?听人说,这橡皮啥都能做,还能炒来吃哩!奶奶个熊,那玩意儿要是能当肉吃,打死我也不信!”
“呵呵呵,”陈炯指他笑道,“你呀,听风就是雨。”
“师叔呀,”炳祺也搔头笑了,“要是这玩意儿真是宝贝,奶奶个熊哩,干脆咱们也去买点儿!”
“万一砸锅呢?”
“天塌压大家嘛,怕个鸟!”任炳祺耸耸肩,“徒子在上海滩待久了,晓得底细。尤其是这上海人,买东西都要买个稀奇。眼下啥也没有橡皮稀奇,所有人都去买了。人们都去买,哪怕是泡狗屎蛋儿,照样赚钱!再说,我这耳目多去了,即使有个啥动静,也是我们先逃呀!”
“我再琢磨琢磨。”陈炯指着一堆报纸,“照这报上说,橡皮是从树里长出来的。按照常理,十年树木。无论何树,没有十年八年,就长不成材料。”
“师叔是说,”任炳祺心里打个咯噔,“这事体有诈?”
“师叔也是吃不准哪!”
“哦,对了!”任炳祺一拍脑袋,“那日在汇丰银行,我瞄见章虎一伙鼓捣起哄。我敢打保票,只要那个人搅在其中,一定有猫腻!”
“炳祺呀,你方才讲到点子上了,上海人爱的是轧闹猛,大家都来轧闹猛,狗屎蛋儿也能赚钱。”陈炯看向桌上的报纸,“眼睁睁地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不赚,却四处化缘求钱,非智者所为,何况是我们这些革命志士!”
“师叔,要是这说,我们这就轧闹猛去,奶奶的,把咱这家底全赌上!”
“咱的家底可以赌上,革命的家底不能赌哦!”陈炯闭目沉思,有顷,眉头一动,“有了,炳祺,速去约见大小姐,就说陈炯有紧急事体求告师太!”
“嘻嘻,”炳祺乐了,压低声音,“徒子得令,这就为师叔约见师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