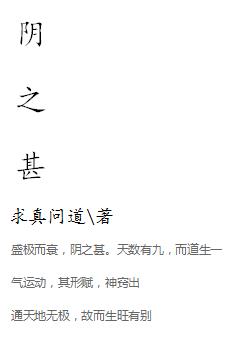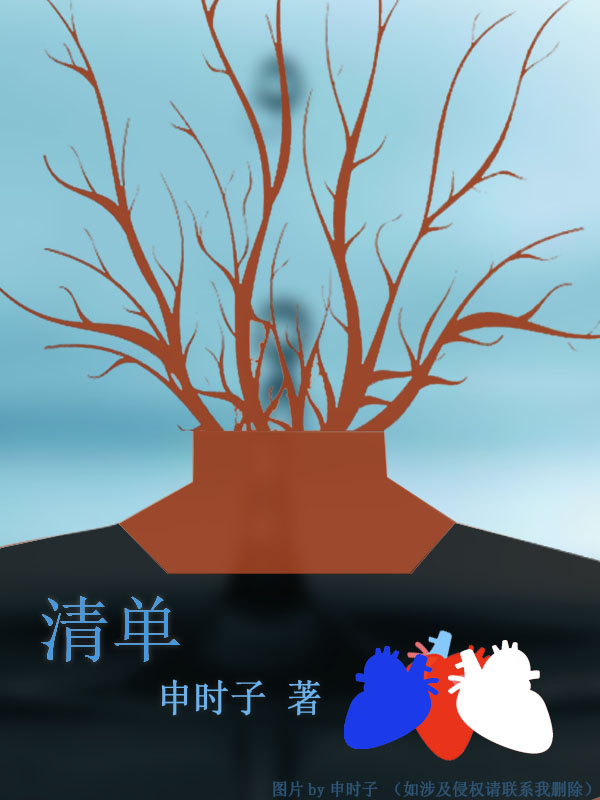村里死了人,全村人都需要到广场上进行仪式。
等乌兰大爷出门后,白老鬼通过刚才的谈话,大致了解到一些信息,反而让他安心下来。
白老鬼想起临走时祭司对他说的话,难道会是与自己谈关于墓的事吗?
这次仪式他们都没出去,已经看过一次祭祀仪式后,已经失去了兴致,并没有去凑热闹,白老鬼而是在房间里写起了笔记。
白老鬼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走到哪,发生一些稀奇的事,都喜欢记录下来。
今天的晚饭很晚,乌兰大爷参加完村里祭祀才做的饭。
饭后都各自回屋睡觉,牛家山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更没有娱乐活动,单调的生活却也带着惬意。
也不知过了多久,白老鬼已经迷迷糊糊睡下,屋外的几句说话声再次让他醒了过来。
由远至近的脚步声,正朝着房间这边走来。
脚步声在房门前停下,随后响起了敲门声。
“小白!睡了吗?快开开门!”
乌兰大爷的声音在门外传来,他后面还站着一个人。
“大叔,马上就来!”白老鬼应了一声,他从床上下来去开门,路过白江蜃和光腚子睡的地方用脚踢醒两人,他知道这时候来的人应该是祭司。
房门打开后,乌兰大爷站在门口,白老鬼一眼就看到大爷身后穿上怪异祭祀服的祭司,白老鬼朝着祭司微微点了下头,然后侧过身把路让出,看着乌兰大爷说:“大叔,进来坐会吗?”
乌兰大爷摇头,说:“不了,祭司大人找你,你们聊,我去给你们倒水!”
白老鬼谢绝大爷的好意,他可不想麻烦这位淳朴的老人,说:“大叔你去歇息吧,不用管我们,我们在你家已经够给你添麻烦了,祭司找我聊聊一些事。”
随后他做出请的手势,等祭司进屋后,便关上了房门。
白老鬼指着房间里唯一一把快散架的椅子说:“还请不要见怪,出门在外,只有委屈一下你,还请坐。”
祭司也没客气,直接坐下开门见山,少了之前的拐弯抹角,说道:“这次来我希望与您开诚布公的谈谈,我从您身上感觉到一种不同的气息,那种气息与几天前来村里那几人的气息相近,我想你们应该同类人。”
闻言,白老鬼面色不改,摸爬滚打多年,在没有弄清楚来意,绝对不会流出半点,说:“我想这大晚上的,祭司绝不只是来找白某谈心的吧?”
白老鬼话里并没承认也没否认,而是让祭司说明来意。
祭司见白老鬼并没打算承认,反而是与自己打太极,看来得说点有用的才行,他决定摊牌了。
祭司嗅了嗅,说:“您是不是觉得屋里的土腥味很重!”
祭司不想绕弯子,这句话算得上直接挑明白老鬼一行人身份。
白老鬼眼皮一跳,额头微微邹起,祭司的话已经表明,他已经知道了几人的身份。
让白老鬼不明白的是祭司是如何知道他们的身份,自认为来村里的这几天并未漏出马脚,如何被识破的?
“祭司的眼力真让在下佩服!”
既然对方已经挑明,白老鬼也没必要再装下去,算是承认了。
“还请祭司明言,如何如此肯定!”他询问祭司,想知道自己哪里出了纰漏。
祭司倒也直接,看着白老鬼说:“在今天之前我还不敢断定,但下午与您们见了后,才证实了我的猜测。”
“哦?”白老鬼侥有兴趣,示意继续说。
“在献灵祭地里我只是猜测出你们身份,但还不能确定。”
这时祭司看向坐在地铺上的白江蜃和光腚子,继续说道:“想必这两位兄弟已经给您讲了在献灵祭地发生的事,他们被鲛人的发丝所伤,鲛人一直在尸池里,发丝早已布满尸毒。
“所以我让乌兰大爷给他们带回解尸毒的药,并没有说明使用方法,常人对尸毒根本不了解,上药无非是内服或者外敷,但解尸毒的方法不同,虽然有药没有特定的方法根本解不了。”
祭司难得一口气说出这么多话,但也从中看出这位祭司的心思和城府不简单。
就连白老鬼也露出赞赏的目光,不过单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
祭司像是看出白老虎想法,说:“当然,这一点只是我证实的一部分,你们下午来我家才是让我彻底确定的主要原因。”
他把目光收回,习惯性扶了下脸上面具,解释道:“当时我与您谈话虽一直在试探性问着您,可您一直都是避而不谈,过于谨慎,一般的商人可不会这样小心谨慎。最主要的还是您的手,你端茶杯时我仔细观察过您的手,常年掘土摸尸的手怎么会与常人相同,加上前面我对你们的种种猜测,所以我更加确信了你们的身份!”
祭司说完后便没有再出声,房里突然陷入安静。
刚才白老鬼要是对祭司还处于赞赏,那么现在不得不开始重视起来了,白老鬼心里叹了口气,觉得低估了此人。
白老鬼坦然道:“祭司猜得不错,我也打开天窗说亮话,明眼人说明眼话,我们是北方掘金中朗将一脉,来这里主要是寻找一处北魏时期大墓!”
“可有眉目了?”
白老鬼说出身份,祭司就迫不及待的问道。
在听完白老鬼的话后,他一点都不惊讶,反而面具遮住的脸上显得有些激动,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急切。
“还没有!”白老鬼看出祭司对这个墓很上心,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乌兰大爷说祭司之前组织过两批人去山上挖过墓,结果都空手而归。
在得到回答后,祭司失望,他沉默了。
大概过了几分钟,祭司埋着头开口说话了,也不知道是讲给白老鬼几人听还是自言自语,但更像是在讲故事。
房间里几人都没说话,只有祭司的声音,他们都安静的听着。
房间里祭司的声音响起:“我们家世代都是村里祭司,父亲去世后,我也就继承了祭司,记得有一天雨下得很大很大,在雨水的冲击下,家里的墙体坍塌了一部分,一包用油纸包得紧紧的包裹随着坍塌的墙面露了出来,我打开一层又一层的油纸,直到最后里面包着一张羊皮卷,当我看了羊皮卷上的内容后,我感觉到悲哀,内心甚至充满了深深恐惧,或许更多的是无力的愤怒!”
“呵!”祭司自嘲了一声,随即说道:“从那以后我仿佛觉得生命没有了意义,你们明白那种感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