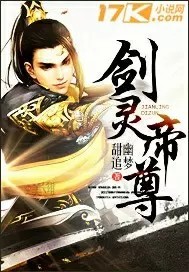从前,她从来不相信什么命中注定,可是这一刻她终于明白了。这世间存在着太多太多的变数,许多事情的发展,都在她的意料之外。她本以为今夜会在晚宴上看到炎澈,并优雅把他错愕的表情尽收眼中。她没有想到会在长廊遇见这个男人,还再一次被他主导了局面!!
“有刺客……”邪恶一笑,熙颜大声呼道。既然炎澈要行刺皇上,那么他必定会潜伏在莞夷国皇宫里寻找机会下手。既然是这样,她又何不与炎澈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呢?!战战兢兢,惶恐不安,她也要让炎澈品尝品尝这种滋味!
听闻熙颜这话,士兵们匆匆赶到熙颜身边,细声问道:“君主,刺客在哪里?”警惕的环顾着长廊四周,士兵们利剑出鞘,个个神情凝竣。这深宫内院的,要是刺客伤了人,他们就是有十条命也不够死啊!其中一个士兵缓缓走到那宫女旁边,探了探宫女的气息,轻声道:“统领,她只是昏了过去。”
云袖轻扬,熙颜指向海棠怒放处,悠悠说道:“刺客好像往那边去了。”精致的眉眼始终凝着一抹冷笑,熙颜捋了捋自己被风吹乱的发。
为首的士兵指了指两名士兵,说道:“你们随公主一起去泓庆殿,其余的人跟本统领来。”低眉敛目,统领退到一旁。
藏匿在海棠花深处的炎澈再也不能多加停留,只能向皇宫偏僻之地走去。现在的心悦,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何那些士兵们都对心悦毕恭毕敬的?!他已经确定这披金戴银的女子就是心悦了,虽然他们之间隔着花影重重,而且月色凄迷,但,他还是清晰的看到了心悦唇角那抹最熟悉不过的笑意。
庆功晚宴于熙颜而言是索然无味的,尤其是那一张张笑得狂妄的面孔,更是让熙颜心生厌恶。酒过三巡,熙颜便推托不胜酒意回了绮华宫。知道这晚宴对熙颜来说确实很是乏味,太后只是柔声询问了几句,便让熙颜回去了。
始终是坐立不安,炎焕的脑海里总是掠过种种血腥的画面。见熙颜这么快就回来了,炎焕很想问熙颜有没有见到炎澈,但挣扎了很久,炎焕终究还是沉默着。
知道炎焕沉默是因为顾虑着她的感受,熙颜突然抱紧了炎焕,轻声说道:“焕,你知道吗,他没有死,也没有被擒……”不知道为何这一刻自己会分外忧伤,熙颜下意识的依恋炎焕温暖的怀抱。
炎澈没有死,也没有被抓,这就好,这就好!提了许久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炎焕轻柔抚摸着熙颜的发,柔声问道:“熙颜,你见到他了吗?”熙颜应该见到炎澈了的,不然熙颜怎么看起来如此脆弱,脆弱得让人心痛。
“是的,我见到他了,而且如今他就藏匿在皇宫里,准备等待时机行刺皇上……”幽幽说出这话来,熙颜如星的眸子里,有清晰可见的恨意。现在的炎澈,一定万分恐慌吧?!因为她不但有了一片栖身之地,还有了一个尊崇的身份!她后悔,后悔方才怎么没有狠狠煽这魔鬼般的男人几个耳光!
在熙颜发间逗留的指突然僵住,炎焕明亮的眼眸,骤然添了许多落寞。熙颜此刻的忧伤,果然是因炎澈而来,苦涩笑笑,炎焕不知道他该说些什么。
轻柔离开炎焕的怀抱,熙颜缓缓说道:“焕,我真的很想把他的心掏出来,看看那一颗冷漠至极的心,到底是什么颜色……”知道是自己让炎焕也染上了忧伤,熙颜牵强笑笑,那笑容里竟凄迷得刺痛人心。
定定凝视着这张烙在了他心底的脸,炎焕轻轻叹了一口气,问道:“如果你和炎澈之间的一切伤害,都是误会,那么熙颜,你会和炎澈重新来过吗?”有多么深情的爱,必定就会有多么浓重的恨,到了现在,熙颜还是爱着炎澈的吧?!
听闻炎焕这话,熙颜长眉紧触,脸色骤然阴沉下来。冷漠转过身去,熙颜漫步走回房间。
怔怔看着熙颜的背影,炎焕的眸子里,浮一层薄薄的雾气。熙颜在他心中走过,却终究只给他留下一个忧伤的背影。
刚踏入房间大门,熙颜的手便被人用力握住,随后而来的,是几近疯狂的吻!
还没有待熙颜反应过来,她已被人打横抱起,在梦魇里出现过无数次的面孔再一次出现在她面前,而且是近在咫尺!
“焕,救……”还没有发出声来,熙颜的唇再一次被狂乱的吻堵上。恶魔又来了,只可惜现在的她,已经不再害怕恶魔了!扯下发间的珠钗,熙颜狠狠把珠钗插入炎澈肩膀。
剧烈的疼痛让炎澈剑眉紧皱,冷然放下熙颜。炎澈满脸的哀伤。他的心悦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和炎焕在一起,还毫不犹豫的刺伤他?!
“心悦,你怎么会在这里?!”拔下深深陷入他肩胛骨的珠钗,炎澈冷然问道。这一切,都让他找不到头绪,看来心悦不是那昏君的妃嫔,那么在这莞夷国皇宫里,心悦和炎焕是什么身份?!
“我不是什么心悦!请你马上给我滚出绮华宫,否则我就不客气了!”愤怒注视着炎澈,熙颜纤细的十指紧握成拳。
她不是心悦?!她不承认是么?!深邃眸子里掠过许多忧伤,炎澈掏出一直放在怀里的胭脂塞到熙颜手中。难怪心悦会这般淡漠的,当初是他把心悦的心生生撕碎了。只是心悦知不知道,在她痛着的同时,他的心也在滴着血!
秀气的胭脂盒仍带着炎澈的体温,看着手中的胭脂盒,熙颜先是怔了怔,随后冷冷把胭脂盒摔在地上。
“带着你的东西滚出去,立即!马上!”纯美的脸上除了愤怒便再看不到其他,熙颜眉眼之间写满不屑。
现在这算什么?!是在表明他有多么怀念她么?!
胭脂盒裂成两半,淡粉的胭脂撒了一地,很是凄凉。
凝视着地上的脂粉,炎澈只觉得他的心,似钢刀刮过一般,痛得快要不能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