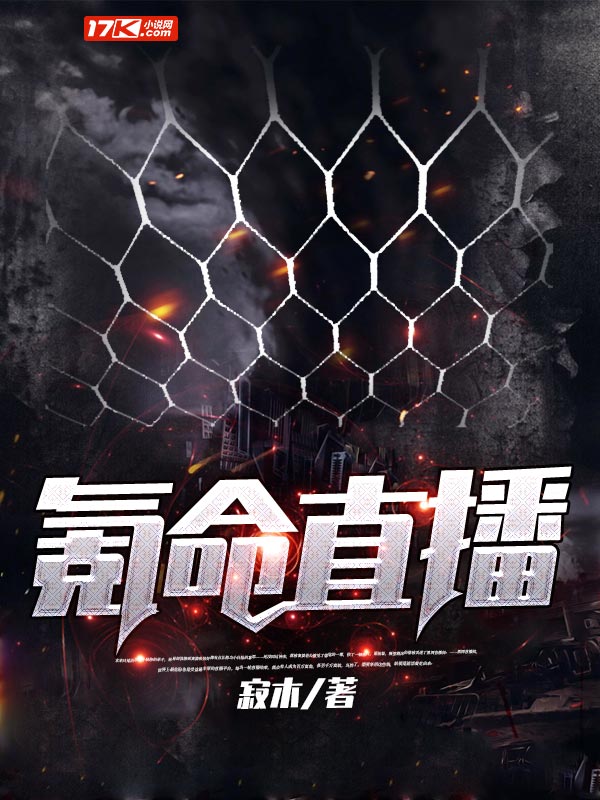咸阳城,在靠近西门的东南角落里有一处冷清萧瑟的大府邸,朱漆大门上一副镶金边的大匾额上述两个秦篆大字“韩府”。有心的看管兴许便已猜到了,没错,这是原秦国丞相韩谈的府邸。这座府邸是刘邦重建咸阳之时,按照朝中重臣的府邸规格建造的,一共六进,还有一个占地近百亩带着一个小湖的后花园。虽然比不上韩谈原来的丞相府,但在这座经历过浩劫而又重建的咸阳城来说,也算是颇为气派了。
深夜时分,一轮有些朦胧的月亮隐在层层叠叠的乌云之后,依稀地洒下几缕薄薄的月色。在韩府后花园的那个小湖边上,有一座小茅亭,亭里此刻正坐着一位须发皓白的老者。老者的目光深邃而又悠长,凝望着湖面泛起的阵阵波光,似乎正在思索着些什么。他便是那位在咸阳城即将陷落之时,逃城叛国的秦国最后一任丞相韩谈。
此刻,这位貌似睿智的老者,心下却是有些混乱。再次经历咸阳城陷城危机,老韩谈不由得有些懊恼命运为何如此对他。在上一次咸阳城即将被项羽、刘邦等叛军攻破之时,身为秦国丞相的他,在城破的前夕独自弃城叛国,出逃到刘邦势力。而这次,韩谈此时的身份却是模糊的令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自打投到刘邦麾下之后,刘邦除了刚刚见到韩谈之时的那份殷勤之后,便似乎有意无意地将他这位给汉军传递了一份重要情报的有功叛臣给遗忘了。韩谈也曾想在刘邦麾下重新建一份功业,哪怕只是谋划之功。然而,在多次求见刘邦无果的情况下,精于人事的老韩谈明白刘邦似乎并不待见他这位背负叛国罪名的臣子。于是,长长一声叹息之后,韩谈便将自己想要对刘邦说起的大争谋划,尽数咽到肚子里了。从此,韩谈便晃悠着他那颗皓白老头,过起了前朝遗老这样角色的生活起来。
好在刘邦虽然并不重用他,在俸禄府邸等等方面却并不亏待韩谈。虽然韩谈知道刘邦只是为了拿他做幌子,好引得那些期待荣华富贵之人纷纷来投到刘邦麾下。这座韩府,便是刘邦给韩谈一处养老安身之处。既然不愁锦衣玉食,韩谈索性也就装聋作哑起来,一心只享受这份带着些许讽刺意味的尊贵。
本来韩谈打算抱着这种心态就此在咸阳,安然度过自己的晚年余生,然而谁曾料到,一切却又在今日清晨之时发生了变化。一支秦军突然出现在咸阳城外,并顿时将整座咸阳城围得水泄不通。从家老那得知消息的韩谈,顿时被惊得呆如木鸡,只觉得脑中轰然一片炸响开来。
“秦军?哪来的秦军?最后一支秦军不是被刘邦在咸阳西门一口气吃掉了吗?”当时韩谈瞪大那双老眼不可思议地追问家老道。得知确实是秦军之后,韩谈顿时瘫软在座椅之上,竟是半响没回过神。
今日下午,咸阳东门那一阵高过一阵的震天喊杀声,让整座咸阳城都听得一清二楚。老韩谈坐在自己书房内,心惊肉跳地听了一下午,也担心了一下午。他生怕汉军一时支撑不住,让秦军顺利破城,到那个时候,作为曾经秦国叛臣的他将会有何下场,那自然不用多说。商君立下的法度,但凡对叛国投敌者,诛九族,首犯处以极刑。
迷迷糊糊之中,韩谈竟靠在书房坐塌上半梦半醒地睡了过去,又在梦到一队秦军冲进府邸的噩梦中惊醒了过来。晚饭时分,出去打探消息的家老告诉韩谈,东门没有破,不过经历了一场血战,城内现在到处是汉军的伤兵,惨不忍睹啊。
听完家老回报后,韩谈这才微微舒了口气,又无心用饭,索性自己独自走到后花园的小湖旁,便开始思索着自己的退路。韩谈所纠结者,便是自己是否要与汉军张良他们绑在一起同生共灭,还是自己再度出逃另寻出路。看情形,眼下局势是汉军处于劣势,但又不知道汉军援兵何时会开来,张良他们有没有把握能顶住秦军进攻还是另外谋划。自己若是再度出逃,又该如何出城,出城之后又得投到哪方势力去。思来想去,韩谈竟是望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愣怔地发呆起来了。
“老爷,夜深天凉了,该回去休息了!”家老的一声呼唤惊醒了正在茅亭中端坐出神的韩谈。
“老胡快去备辆车!”韩谈醒神过来,回头叮嘱那位姓胡的老家老,揉了揉有些发麻的双腿,便利索地站了起来。
“老爷这么晚了,您要去哪儿啊?”家老关切地问了句。
“你别问了,备车就行了!”韩谈走出茅亭,微微有些不悦地冷声说道。
片刻之后,一辆四面篷布的缁车嘎吱地驶出了韩府偏门,沿着青石街道径直往东行去。小半个时辰之后,这缁车来到张良的丞相府邸,车上的驭手跳下来上前咚咚地敲了几声。风灯闪烁间,一名老仆打开朱漆大门,探头与驭手低声交谈了几句,便又匆匆关上了大门。片刻之后,大门旁的一扇小门吱呀打开,驭手跳上缁车,便驱车进了偏门。
穿过偏门,来到府邸内的车马场后,韩谈下了马车,跟着那名老仆穿过几进回廊,便来到一处灯火通亮的正厅。略略打量了眼厅内摆设,韩谈便自己寻了把座椅坐下,接过一名侍女端来的热茶,刚刚饮了几口便听得屏风后传来张良一阵爽朗的笑声。
“何事竟是惊动韩公夤夜来访,张良有失远迎,望韩公恕罪!”一身白衣锦袍的张良大步绕过屏风,边笑着边拱手对韩谈做礼道。
“韩谈区区一老朽,何敢当丞相出迎,更遑论恕罪了!”韩谈连忙也起身肃然躬身拱手还礼道。
“韩公快请入座!”张良虚手一请客套道。
“丞相请!”韩谈不敢托大,连忙虚手回请道。
说笑间,两人各自按座位坐定,侍女也给张良上了一杯热气腾腾的香茗。几句寒暄过后,韩谈感叹一句道:“丞相为国事操劳、呕心沥血,竟是深夜尚未入睡,老朽甚为佩服啊!”
“得汉王托以重任,良安敢不用命乎!”张良却只是摆摆手回道。他适才刚刚送走董成等一干将领,回到寝屋后竟是左右辗转不能入眠。索性起身来到书房,看起书来,不想却听到家老来报说,韩谈夤夜来访,问丞相是否愿意接见。张良略一沉吟,知道这老狐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更何况是深夜来访,莫不是有重大事情要与自己密谈。沉吟片刻,张良便让家老请韩谈进来,自己又在书房徘徊片刻,这才大步走去正厅。眼下,见韩谈这老狐只海阔天空地客套着,张良也不急于点破,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
“老朽听闻,咸阳城现已被数万敌军重重围困,却不知丞相大人有何破敌良策?”老韩谈久于人世应酬,自然也看出来张良的那些许伎俩,轻叹一声便索性挑明话头道。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张良手里现在时兵少将寡,何来良策可施?”张良心下一动,顿时明白这老狐原来是跑自己这儿来打探消息查看风头来的,面上却装出一副痛心疾首之状,问韩谈道:“韩公曾为秦国丞相,定是对秦军知之甚深,张良敢请韩公教我!”虽然口中说着请教,张良的屁股却始终粘着座椅不动,丝毫没有一点诚心求教的意思,反倒是揶揄讽刺意味更浓一些。
见张良将话头踢了回来,又带着讽刺与不屑的意味,韩谈心下微微有些气愤,但仍是装出一副惶恐之样,拱手说道:“丞相莫要羞煞老朽了!韩谈是做个几天秦国丞相,然而,那都是秦国国君感念老朽辅佐之恩,才赏赐于老朽的。老朽怎敢与丞相相提并论,更遑论相教一说。不过,老朽对丞相大才久有耳闻,世人都说丞相非但是治国理民的圣手,更是精通兵事的帅才。老朽有心为汉王出力,却又不知该如何着手,迫不得已这才打扰丞相歇息,求教于丞相。”
韩谈一席话说得合情合理,又是拐弯抹角地拍着张良的马屁,曲折转承之间却又将难题重新踢给了张良,引得张良心下不由得不佩服这个精于人事周旋的老狐。“张良不过偶得一部兵书,粗略通读了几眼,怎敢当韩公如此谬赞!”张良那张白皙的脸上似乎始终都挂着那一抹和善的笑意。说罢,张良却突兀地收起笑容,露出一副担忧之色,低声叹道:“不敢相瞒韩公,张良对眼下局势着实是无计可施了。”
“敢问丞相,咸阳城目下是何局势?”韩谈闻言装出一副惊讶之色问道。
“实说了吧,城外秦军兵力多于我军数十倍,兼之战力又强,仅仅今日下午一战,我军便已伤亡惨重,咸阳城怕是有陷城之危了。”张良心下一动,索性继续说道:“张良眼下,正为如何坚守咸阳发愁,若韩公有何良策,还望不吝赐教于张良啊!”
“如此说来,咸阳旦夕便有破城之险?”韩谈这次却是真的惊讶了,忍不住失声说道。话一出口,韩谈便又恍然过来,知道自己说漏嘴了,连忙又诚惶诚恐地问道:“那,那汉王是否知晓咸阳危急,是否已经派出援兵来救急?”
“汉王早已得到军报,援兵也已在几日前派出,只要我等在坚守上些许时日,咸阳城当有望能守得住!”张良心下冷冷一笑,面上却是一本正经地说道。
“如此甚好,咸阳便有救了!”韩谈连忙拱手对着厅外天空赞一句道:“汉王英明,定能解救我等于危城之中!”说罢,便又与张良东扯西谈地说了起来,不过只字片语之间,却有意无意地想打探张良等人具体的下一步行动。张良心下清楚,嘴上却也不道破,只是一味地与韩谈打着太极,惹得韩谈心下发急却又无计可施。
“夜色已深,老朽就不打扰丞相大人歇息了,若有用得老朽之处,请丞相尽管吩咐便是了!”韩谈抬头装作望了望厅外天色,回头起身拱手对张良说道。
“也好,韩公也早些休息,保重身体要紧!若有大事,张良定事先知会韩公,少不得叨扰了!”张良连忙也起身笑着拱手道。
送走韩谈之后,张良冷冷一笑骂道:“哼,这老狐,怕是又不安分了!”说罢,唤来家老低声嘱咐了一通,这才回自己寝屋歇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