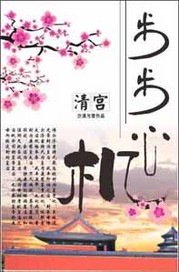她面有忧容,声音却婉转如黄莺,闹在我的心里悄悄绽放的春日。
说罢,她盈盈拜退。
望着她的身影消退在浓墨般化不开的夜色中,我瘫坐在床上,我这一生唯一的朋友,瞒了我整整七年,骗了我七年,终于还是离我而去。
此生此世,又有谁可以相亲相爱、相护相知?
我怎能不心痛!怎能不悲伤!
寒风悠悠将窗帘漫卷,一阵清丽的箫声随之而来,回旋婉转,影影绰绰。
我起身推窗,幽窗默默,小院深深。皓月中天,寒星遍野。
箫声远远传来,在黑夜中更加浓冽,一股凄凉萧索之意涌上心头。
不知是谁,于重重府门之外,以箫声作引,漫吟一首《有狐》⑴。
有狐绥绥,在彼淇梁。
心之忧矣,之子无裳。
有狐绥绥,在彼淇厉。
心之忧矣,之子无带。
有狐绥绥,在彼淇侧。
心之忧矣, 之子无服。
箫声忽高忽低,忽轻忽响,呜呜咽咽,如泣如诉。低到极处之际,蓦地高潮迭起,复而又低沉下去,那声音极低极细,似有说不出的愁绪惘然,道不尽的孤独悲伤。宛若一只在野的孤狐,孑然一身,没落飘零。“心之忧矣,之子无裳。”是那吹箫的人也在怜惜我此刻孤独无依的痛苦吗?箫声如梦似幻,飘渺流离,是耶非耶?终归于湮没。
一曲终了,荡气回肠。我心之忧,不能奋飞。
忽然想起那个自称谢风的黑衣少年,那双桀骜如狐的重瞳里,是否也如我一般藏匿着如狐的孤独?
念及此,我才惊觉,我已经数日没有好好睡一觉了。要想好好活着,是容不得你有丝毫喘息的,今夜,我必须养足精神,以应对来日种种变数。
置身床榻,又辗转反侧,良久,才于夜色迷蒙之中缓缓入睡。
睡至寒夜未央,我被一个没有由头的噩梦惊醒,长身而起,才知道终是一场无痕愁梦。
我轻轻拂落心头的悸动,双眸微转,竟对上一对泛着幽光狐狸眼睛。
那黑衣少年,不,谢风,此刻正斜卧于窗棂之上,托着腮端详着我。
“怎么是你?”我慌忙地拿外袍盖住自己。
“嘘——不要动。”他怅然道:“都说女孩子在睡梦中最美。我只想看看梦中的你是否亦如此?”
我又好气又好笑:“就为了这?你坐在那里多久了?”
他跳下窗来,一步一步地逼近我:“你走后,我就去找如烟。”
我茫然道:“如烟是谁?”
“冀南第一名妓,国色天香,笑语如烟。她拥有足以令每个男人都魂牵梦绕的一切,卖艺不卖身,千金一掷尚难买得佳人一笑。”
果然是登徒浪子,我心中竟有些酸涩:“这与我何关?”
他已走到我面前,一双重瞳凝视着我:“我只是好奇,当她心甘情愿躺在我怀里的时候,为何我心里想到的却是你?”
我微感愕然,他已伏在我身上,在我的额头轻轻的印了一记吻。
他的唇柔软而温热,像春日里拂柳而来的风,轻柔地拂过我的心。
这次,我没有反抗,只是侧过头去,道:“你说完了?”
他面对着我,缓缓站好,道:“说完了。”
我不去看他,冷冷道:“说完就走吧。”
他沉默片晌,道:“我以后能不能再来找你。”
我垂首默默,心中柔肠百转。
他笑道:“你不说,即是默认了。”
我用力绞着被褥上一朵凌乱的荷花,暗下决心,回头直视着他:“韩府不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
他眉心一跳,深深凝望着我的双眼,眼里有莫名的伤痛。
我被他瞧他的心头一刺,越发不敢抬头相对。
我们只见过一面,即便曾经生死与共又如何?他不是曾说,他有过不少女人,他眼里的深情也不知给过多少女子,我又何必耿耿于怀。
何况,他是如此的深不可测。
“很好。”他凄笑一声,跳上窗棂,又转头问道:“告诉我,你有没有想过我?”
我心虚,却终是松开被我揉成一团的被褥,抬头迎上他的眸子,道:“你是我不该想也不会想起的人。”
他眼中有厉色一闪而过,旋风般掠窗而出。
一切又宁静如常,只有窗纱被风吹动的呼呼声。仿佛方才并没有人来过,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
“请小姐千万不要轻信那日救你之人。”
我默然坐立,珠儿的话反复在脑海中沉浮。
谢风谢风,你果然来去如风,恍然若梦。
直到许多年以后,我依然不明白自己为何会沉醉于这场仓促袭来的梦幻中。也许是那个从天而降的少年,为我敲碎了高耸环绕于深闺多年的庭院围墙,让我第一次领悟到红砖绿瓦之外广阔自由的大千世界。我多么希望自己是一只振翅而飞的鸟儿,再也不用理会命运于我的重重枷锁,而是跟随如风般的他展羽遨游。
只是,梦,总该有醒的时候。
注:⑴有狐,出自《诗经·国风·卫风》,大意为一只衣不蔽体的孤独狐狸在踽踽行走。意为灵魂高贵出众的人,完全可能因为种种不幸而落入窘困的境地,但窘困的境地掩不住他高贵灵魂的光芒。此处被我断章取义的拈来。
(弱弱的建了一个群,群号:139942270 欢迎各位读者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