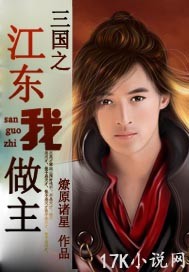天涯茫茫,长路漫漫,两匹飞骑,万里追风。
一路上,他骑白马,我骑黑马。他胯下的白马和他一样飘逸脱尘,丝毫不逊色于黑曜,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阿亮要恨他,因为他实在太完美,太优秀,从外到内,叫人挑不出一点毛病。
高处不胜寒。一个人若是太完美,太优秀,岂非也太孤独?
可他似乎永远有着淡然的笑容,宁静的面庞,睿智从容的目光和悲悯苍生的胸怀。
而他越是淡然宁静,睿智从容,就越发让人嫉妒。而这些都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他的心,虚怀若谷,胸有沟壑,他能包容你的一切,却更让你无地自容。
我若是有这么一个哥哥,只怕也要嫉妒的很。
一路上,流光曳梦,风吹山岚,良辰美景奈何天,却道断肠又是谁?
我与他披星戴月地疾驰了整整一夜,方到安徽境内。此刻,人困马亦乏,然而,我无法让自己停止,因为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都像刀子一下下地剜在我的心口。
沿途又听到不少风声,说是颍上有人起兵造反,那些人头蒙红头巾,向天下宣扬“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告文,又竖起“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号召天下仁人志士加入义军,驱除鞑虏,四海归心。
听到这些时,我与一尘面面相觑,终是晚了一步。
念及此,我已忧心如焚,更是快马加鞭。
暮色将至之时,我们已到达颍上城外。
远远望去,狼烟四起,旗靡辙乱。不知为何,连上天也变了颜色,阴云密布,一片肃杀之气。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眼前,却是满目的断壁残垣,破甲遗兵,尸横遍野。
一尘翻身下马,面露痛色,低声叹道:“阿弥陀佛,苍生何辜?”
我颤抖着从马上跃下,一步步走进百里血光之中,惊愕的说不出话来。
我毕竟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如何经得起过这种场面!那一瞬间,我终于明白为何爹总是如此沉重而忧愁,这条复国之路,要用多少义士的白骨才能铺就?那高悬的战旗,又要用多少战士的鲜血来染红?
令人惨不忍睹的断肢截体到处都是,鲜血向河水一样淌满了大地,那样突兀而可怖的一切,见证了之前那场战役何其惨烈,也让我的心彻底冻结。
城墙上无兵,而里面杀声震天,想必城内并有一场恶战,也许爹就在里面。
还有林儿,我的弟弟,那个永远文文弱弱,毫无心机的白玉般的少年,他要如何面对这可怕的一切?
“爹!”我突然低呼一声,往城中跑去。
一尘见我奔去,叫道:“不可!”
我不听他多言,凭着一腔悲愤向狂奔着。
“阿棠!”
我怔住,恍惚中,仿佛又是那个漫天飞雪的夜晚,一个狐狸般狡黠的俊朗少年轻声唤着我“阿棠”。
霹雳一声,暴雨骤然倾盆而下。
蓦然回首,依旧是一袭黑衣,那熟悉的面容有着深深的无措和怜悯,
“阿棠,你怎么来了?”他的语气似是关切似是担忧。
我茫然望着他,却怎么也看不清他的面容。
突然电光一闪,将他的面容清清楚楚的印在我面前,却说不出的阴森冰冷,触目惊心。
又一声凭空炸雷不期而至,我周身一震,如梦初醒,冲他喊道:“我爹呢?林儿呢?”
暴雨里看不清他的神色,只听得他的声音:“阿棠,你爹他……已经阵亡了。”
惊雷又起,纷乱了他的声音,我叫道:“你说什么?”
他大声喊道:“你爹死了!刘福通正在南门接应韩林儿!你快跑吧,里面危险!”
死了!爹死了!
暴雨如注,在我看来,整个世界却死一般的漆黑,死一般的寂静,再没有什么光亮能注入我的眼睛,再没有什么声音能传入我的耳朵,也再没有什么人事能勾起我的心神。
若有,也只有恨!冰寒冷彻的恨,销肌损骨的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