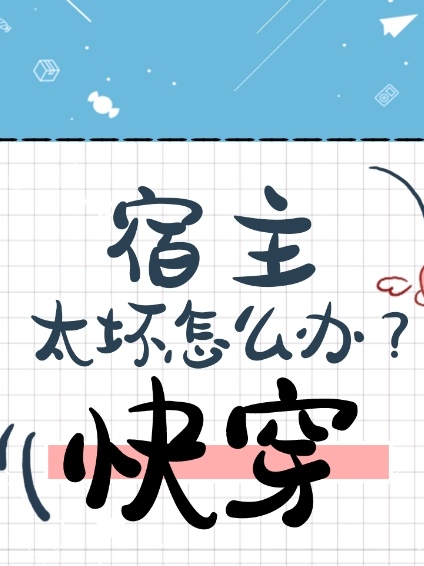陈友谅纵声大笑,笑得张狂而可怕,忽然快步将善儿抱过来,伸长了双臂,将善儿悬空于眼前跳跃的烛灯上。
“不要!”我惊恐地看向他,失声尖叫,“你疯了!他是你儿子!”
陈友谅的目光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危险,他松开一只手,冷冷道:“他是我的儿子?他真的是我的儿子吗?”
“哇……娘娘……娘娘抱抱。”善儿哭得更汹涌,那尖锐的啼叫如利剑般绞住我的心窝。
我登时泪如雨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目光哀伤而恳切:“求求你,不要……”
“皇上三思啊!他是您的太子啊!”鸢儿被这骤然发生的一切吓坏了,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求饶,白皙的额头都渗出血来。
春儿听到声响后急匆匆地跑进来,她趁着陈友谅不注意,猛地扑向那盏火灯,滚落的烈火疯狂地舔舐着她的衣衫。
我蓦地捂住嘴,春儿来不及惊叫,痛得在地上反复打滚,好将身上的火扑灭。
陈友谅冷哼一声,将善儿丢到鸢儿怀里,狠狠扬起我的下巴道:“你现在知道了,你永远也不可能斗得过我。”
孩子,是我永远的软肋。
我冷漠地盯住他尖锐的双眸,忽然心痛得无法呼吸,我抹掉眼角的泪水,失神道:“你羞辱完了,可以走了。”
陈友谅轻蔑的笑,接着用力甩开我,从鸢儿手中拽走善儿,头也不回的阔步走去。
“娘娘……我要娘娘!”善儿在陈友谅的怀中不住地挣扎着,小小的手儿拼命地冲我挥舞着。
我再也忍不住,坐在地上失声痛哭,鸢儿无措的摇着头,喃喃道:“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春儿捂着自己烫伤的双臂,抓住鸢儿道:“不是怎样的?”
鸢儿看向我们,早已泪流满面:“刚才,皇上抱着太子来,明明说要接小姐回宫团聚。怎么,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回宫团聚?”我愣住,忽然凄然一笑,冰凉的泪水无声的淌下,绝望而悲凉。
陈友谅,为什么你给我带来的总是伤害!无休无止的伤害!
我恨你,恨你!永远恨你!
———————————————————————————————————————————
“爱他时似爱初生月,喜他时似眉梢月,想他时道几首西江月,盼他时似盼辰钩月。
当初意儿别,今日相抛撇,要相逢似水底捞明月。”
夜色已笼罩大地,谁的歌声正在甜得发腻的芳香里缠绵。空气里飘满鲜花和烈酒的味道,它们一起被一种孤独的欲/望点燃,在无边的黑暗里以燎原之势凶猛地燃烧着。
酒楼内外是嬉闹的人群,他们一个个都鲜衣怒马,仪表堂堂,他们看起来是那么欢乐,那么满足,也那么年轻。也是,像他们这种衣食无忧、前途光明的将门子弟,本就有足够的理由比别人更快乐。
然而,今夜的快乐却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然拥有或必将继承的那份财富、权利以及荣誉。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被唤作“棠姑娘”的红衣女人。
她是那样热烈、妖娆而又忧郁,她有时离你很近,有时又离你很远,她来无影、去无踪,仿佛是天上的仙子,又好像是来自地狱的魑魅。当然,唯有喝酒的时候,她才会骤然出现,并且毫无顾忌地将任何男人当做自己的“朋友”。
“她是谁呢?”有人问。
“一个伤心人,一个寻欢作乐的伤心人罢了。”我缓缓踏上青石桥,穿过一个锦衣青年的身边时,淡淡的说,然后,那句清浅的话便乘着偏走的西风归去。
五天后,我又一次踏进这间酒楼,吵闹的大厅蓦地安静下来。
纵有满室少年如玉,我也无法不注意到那个坐在角落里,穿着月牙白的长袍,连鬓角都修饰得一丝不苟的清俊少年。
那个叫做陶凯的、既固执又莫名其妙的大男孩。
我忽然觉得很可笑,我居然还是记住了他的名字。
我想了想,缓缓走向他,长长的红色披风拖在地上,发出沙沙的响声。
陶凯始终注视着我,眼神专注而又耐人寻味,仿佛周遭再没有其他可以入目的风景。等我走到他身边,他文雅地拉开木椅:“棠姑娘,你来了。”
我顺势坐下,皱眉道:“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陶凯深深凝望着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一定会再见到你。”
我不经意间避开他那锁定的目光,饶有兴趣道:“为什么?”
陶凯倒了一杯茶,这是上好的碧螺春,柔软的叶子漂浮在茶杯里,溢出出尘的恬淡香气:“因为我每天晚上都会在这里等,直到你来为止。”
这样的话语由一个年轻英俊、玉树临风的少年郎说出来,本该是很动人的。
可我却无动于衷,这种想法很可怕,为什么我会不在乎呢?
是不是因为,心麻木了,就对什么都不在乎了?
我没有接,垂下眸子微笑道:“我只喝酒,不喝茶。”
陶凯的手定格在半空中,没有收回,也没有勉强,只是倔强而诚挚的看着我。
我忽然发觉他那白玉般无暇的纯净面容,竟和当年的林儿十分酷肖,也在那一瞬间,我心软了,鬼使神差地端起茶杯品饮:“下不为例。”
林儿,多年不见,你过得好不好呢?
“你有十九了吧。”我见他头上无冠,突然开口道。
陶凯愣了一下,诚实地点头道:“不错。”
我掩嘴娇笑,随口说道:“叫我姐姐吧,你还是个小公子呢。”
陶凯面容微怔,随后绽放出相见以来的第一个笑容,好似天上皎洁的明月:“姐姐。”
心底某个柔软的地方被深深的触动,我忽然笑不出了,相反竟然鼻头微酸,眼圈也红了起来。
我迅速背过身,深吸一口气,再度展颜而笑,头也不回走入闹哄哄的人群中。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
狂酒不过遣怀,声色皆是犬马,我大笑着、一杯又一杯,旋转于无数寻欢作乐的人中间,自始至终,陶凯都一言不发的坐在那幽暗的一角,神色黯然地盯着我。
对他,我始终是有一丝警惕和不解的。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夜夜笙歌,就是要败坏自己的名声,趁机拉拢或离间新汉政权的君臣关系。然后,我会回到陈友谅身边,让他成为众矢之的,让他英名尽毁、人心向背。
这座小小的酒楼,几乎聚集了汉王朝所有要员的子弟,唯独他,这个名唤陶凯的少年,是来路不明的。
他究竟是谁?又为什么要闯入我精心设计的这盘棋局中呢?
也许,他只是和眼前这些狂妄轻浮的少年一样,禁不起女子的美色魅惑而已。
可是,他的眼神非但清澈无欲,仿佛还泛着浅浅的哀愁,一点也不像流连花丛的纨绔子弟。
一夜的狂欢过后,我摇摇晃晃地走入深沉如墨的夜色里,和往常一样。
身后有人遥遥地跟着我,我蹙眉驻足,轻轻道:“为什么要跟着我?”
陶凯也停住,他淡淡道:“你跟他们不一样。”
我霍然回首,挑眉道:“哦?哪里不一样呢?”
陶凯走近我,目光幽亮:“你的眼神里满是痛苦和哀伤,还有深深的疲倦,仿佛这世上再没有什么事能勾起你的兴趣和热情。而他们,不过是一群不谙世事、幼稚无知的浪荡少年而已。”
我沉默,渐渐笑了:“是吗?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发现?”
陶凯看着我,轻轻叹了口气:“不,正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你的与众不同,才会趋之若鹜地追求着你。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人总是对忧郁和出离有着莫名的眷恋和向往。”
“也就是说,他们爱上了我的忧伤,”我笑得更妩媚,“那你呢?”
陶凯垂了垂动人的眼帘,却遮不住眸子里清澈潋滟的光华:“我只是想了解你。”
我收敛了笑容,紧绷着脸,故作严肃道:“原来是好奇,有人曾对我说,好奇是一种无休止的欲望,是奔腾不息的火焰,它能吞噬一个人的心智,蒙昧他的双眼,让他的身体不自觉的做出背叛自己的行为。好奇实在太危险,陶公子,千万不要把你的好奇轻易地表露给对方,那会让你玩火自焚。”
说完,我转身离开,却被一只有力而又白皙的手紧紧拉住,少年人独有的清淡气息扑鼻而来。
我紧抿下唇,盯着他的手臂道:“别再跟着我了。”
陶凯蓦地松开我的衣袖,白净的面容上泛起淡淡红晕,却依旧认认真真道:“姐姐,我能感觉的到你心底的恐惧,你需要人保护。”
“我需要人保护?”我弯腰笑起来,指着他道,“谁来保护?你吗?”
陶凯一瞬不瞬地看着我:“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愣住,片刻后,后退一步和他保持距离,转身道:“走吧,离我远些,才是对我、对你自己最好的保护。”
陶凯不再勉强,但他的声音却从背后飘来:“姐姐,我还能再见你吗?”
这声“姐姐”,令我徒然眼眶微湿,我径直往前黑暗里走,淡淡道,“如果我有空,你有空,为什么不能呢?”
夜色如歌,晕开在多情人的眼眸里,却是一种无情的伤痛。
不要问,穿林的风是否解得叶的风情。
风,本就是人生中抓不到,留不住的奢侈。
身后再没有任何声响,空留下醉生梦死后那份寂静而深刻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