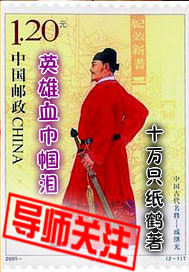清晨梳妆的时候,我坐在铜镜前,转身对春儿道:“我自己来吧。”
春儿点头,将犀角梳递在我手中,双手相接的那一刹那,我迅速地在她掌心划了个“滁”字。
她愣了一下,有些迟疑地将手收回,静默而恭谨地立侍于一旁。
我注视着铜镜里温柔凝望于我的清俊面容,微微一笑,执起梳子开始编发,边做边道:“春儿,我和王爷要出趟远门,你留在江州好好照看世子,鸢儿跟我去就行了。”
春儿温顺地垂下头,顺道敛去眸子的光华,毫无异议道:“是。”
转瞬间,一个简单的飞云髻已经盘好,我正在寻思将手中这支嵌着白玉的珠钗插在哪里好,陈友谅已走上前,随手将其插进斜角,他握住我的手道:“这样就很好,时候不早了,走吧。”
我点点头,随着他站起来,俯身亲了亲善儿的小脸,喃喃道:“宝宝,娘也不想离开你,娘这么做也是不得已。”
善儿睡得正香,自然不会回答我,但他的小脚却轻轻踢了我一下,仿佛是种回应。
陈友谅好笑道:“又不是生离死别,你们女人家就是麻烦。”
“怎么?”我扬起脸,不满道:“你又嫌我麻烦了吗?”
他大笑,拉住我的手,向外阔步走着,出门前意味深长地瞟了春儿一眼。
刚走出来,沈卿怜已抱着陈理盈盈立在门口,她一身素淡的襦衫碧云裙,声音清幽:“王爷,卿怜带着理儿来送您一程。”
陈友谅的笑容僵住,瞟了我一眼后,伸手从沈卿怜怀里抱过陈理。陈理憨憨地笑着,不时拿小手扯扯陈友谅的袖子,模样十分可爱。
陈友谅瞧着喜欢,抱着哄了两下,沈卿怜看时候差不多了,就叫奶娘将小王子接走。陈友谅注视着她,目光温和,语气则意味深长:“我们该走了,这里就交给你。”
“妾身一定不负王爷所托。”沈卿怜屈膝拜礼,垂眸相送,举手投足间都流露出大家闺秀的风仪和矜持。
这也是个可怜的女人,她和我都一样,只是男人争权夺利的工具,政治风云中的筹码而已。
我操着复杂的笑容看了她一眼,便转身跟陈友谅并肩而去。
————————————————————————————————————————————
我们一路随军而行,不知踏过多少迤逦的山川。
然而走得越远,我的眉头却皱的更深,只因我发现,这条路根本就不是去滁州的路。
夜晚,我们在中途扎营休息,我静坐在军帐外的篝火旁,陈友谅和徐寿辉等人正在里面如火如荼地讨论着进攻路线。
四月的月光是那样憔悴,月光下的野花却更憔悴。
我掐掉一朵蔫掉的花儿,心底猜想着:陈友谅明明说是要去滁州,为什么军队却往采石的方向去呢?而且沿途故意拖延,仿佛在等待什么一样。难道说,他是骗我的?可他为什么骗我?我应该没有露出什么马脚的,这几个月,我一直慎之又慎,他没道理怀疑我呀。
也许是我多想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故意兜着弯子走,好让朱元璋的军队察觉不到。
想到朱元璋,也不知道春儿是否能明白我的意思,又能不能顺利地将消息传达给朱元璋。
柔软的草地已被寒凉的露水所润湿,从什么时候起,夜色更加深沉。
注视着眼前在风中飘摇的烛火,我忽然觉得疲倦而孤独,人也有些松懈了。就在这松懈的一瞬间,身后传来破空的风声,迅疾而精准,直击我脊背上的命脉。
我霍然清醒,身子一缩,翻掌滚向旁边,堪堪避过了那致命的一击。
只听“笃、笃、笃”几声急促的响声,十几点寒星已暴雨般钉在草地里。
我刚稳住身形,立刻既看到森寒闪烁的刀光。
“妖女!”伴随着一声大喝,快刀闪电般劈下,砍向我的腰,似乎想要将我一刀劈成两截。
我深吸一口气,身子斜贴着刀光冲上去,刀刃划破了我的衣衫,贴着肌肤向里刺入,激起寒凉的触感。
“嘭——”
我反手一抬,刀被斜斜地抛出,落在篝火里,火光四溅。
与此同时,执刀的人一个踉跄跌往草地上。这人是一名戎装大汉,想来是天完军的某个部下,他惊愕之余,大声啐骂道:“你居然会功夫,果然是妖女!”
说罢,他便挥着拳头再度冲上来,我仔细听着帐中的动静,皱着眉正在犹豫要不要还手,“咻”的一声,一柄乌黑的利剑流星般从我耳畔迅速擦过,直贯那人的胸膛。
我下意识地扭头,看到陈友谅、徐寿辉和张定边等人都掀帐而出,掷剑的正是陈友谅。
陈友谅快步走至我身旁,稳稳扶住我有些颤抖的身子。
那人仰面倒下,鲜妍的血色晕开他的衣衫,他目眦尽裂,口中还愤恨道:“佞臣、妖女,你们……你们不得好死。”
陈友谅握住我的手力道突然加紧,格的我骨肉生疼,我忍住不做声,他则沉声道:“拖下去,五马分尸!”
此话一出,立马有几个士兵领命,拖住那人的尸首离开。我扭头不忍再瞧,深深呼吸着,思索着现在的状况。
“汉王未免操之过急了些,”徐寿辉走上前,眯着眼睛道,“为何不问问他是谁派来的?”
我装作惊慌不已的样子,躲在陈友谅身后,偷偷瞄着徐寿辉的脸色。
陈友谅转眸冷笑:“皇上不必担心,无论是谁,够胆的就让他来,看看是本王的命硬,还是他的命硬。”
“我只怕王妃的命不如汉王那般硬呢!”徐寿辉笑意深沉,向前走了一步。
忽然,他“咦”了一声,俯身从草地中拈起一根寒芒闪烁的银针,嗟叹道:“这人的手法当真是差劲,十几发的暴雨针没有一发打中的。”
我紧张起来,手心沁满汗珠,再看向陈友谅时,发现他泛着褐色的重瞳中闪现出银针般的寒芒。
我深吸一口气,大着胆子看向徐寿辉,毫不客气道:“怎么?皇上很希望臣妾被打中吗?”
“这怎么会?”徐寿辉笑了,炙热地双眸直勾勾地盯着我,仿佛要将我从里到外都看透,“朕可比汉王更心疼你。”
“你……皇上言重了!”我脸色微红,不知是因为愤怒还是别的,眼睛瞅向别处恨恨地道。
陈友谅脸色一沉,似乎要发怒,可最终只是嘴角抿了抿,斜睨着徐寿辉道:“拙荆受了惊吓,需要休息,恕本王概不奉陪了。”
——————————————————————————————————————
军帐内,我注视着桌子上那些被烛光洗得发亮的银针,顿觉如寒芒在背。
陈友谅是不是在怀疑什么,不然,为何要将这些银针摆在我面前呢?
还有军营重地,怎会发生刺杀这样的事?我在江州那么久,都没有人来杀我,偏偏一出门,就出了事。这未免太巧合了些吧?
难道说,这是一种试探?
想到这里,我执起犀角梳,缓慢而仔细地梳着洒满肩头的乌丝,努力让自己静下心来,以好好缕清自己同样纷乱的思路。
忽然,耳畔有热气扑朔,陈友谅轻轻拥住我,探问道:“有没有受伤?”
我顺势小鹿般缩在他怀里,摇摇头:“幸亏你们来的及时,不然我就惨了。”
陈友谅环着我的腰肢,嗓音沙哑,夹带着一丝歉意:“是我疏忽了。”
我咬着牙关,反复呼吸,问道:“那人是谁?”
陈友谅蓦然愣住,低笑一声,淡淡道:“赵普胜的旧部。”
听到赵普胜,我心中愈发刺痛,眸子不觉含了星雾,陈友谅停顿片刻,又迟疑道:“其实老赵他……”
我忍住泪水,转头冲他嫣然一笑,伸手抚上他的眉眼,柔声道:“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陈友谅欲言又止,终于还是点点头,下意识地握住我的手,疑惑道:“方才,你是怎么躲过那些银针的?”
他果真在怀疑我了。
我垂下头,慌张起来,像是手足无措的孩子:“我……我也不知道,自然而然地就侧身翻过去了。阿谅,是不是我以前懂功夫呢?”
“嗯,会一些防身的,”陈友谅低声沉吟,眸色渐渐转深,他从桌子上端起一个瓷碗,温声道,“什么都别想了,喝完参汤压压惊。”
我犹豫了下,抬头探向他深潭般的眸子,接过瓷碗,将参汤仰头喝下。
不久,我就感到周身像是散了架般,软软地瘫入陈友谅的怀里,我焦急地抓住他的衣襟,想问个究竟,却发现自己疲惫的说不出话来。
“睡吧,你太累了。”陈友谅凑近我,雪亮而忧郁的眸子令我感到不适,我偏过头避开他灼人的目光,可那声音却似有魔力般,令我愈发昏昏欲睡。
感觉到自己被人抱起来,我缓缓阖上眼睛,黑暗中,狐狸一般闪亮的眼睛却始终在我眼前浮动。
仿佛有阴冷的风刮过,那是一种透到心脏的冰凉!
这种冰凉刺激了我混沌的六识,我极力想要睁开眼睛,和眼前这慑人的黑暗作出最后的反抗与斗争。
“睡吧……睡吧……”有人低声在我耳畔反复地轻吐,我终于发起挣扎,释放自己脑海中的最后一丝清明。
黑暗,就此扼住了我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