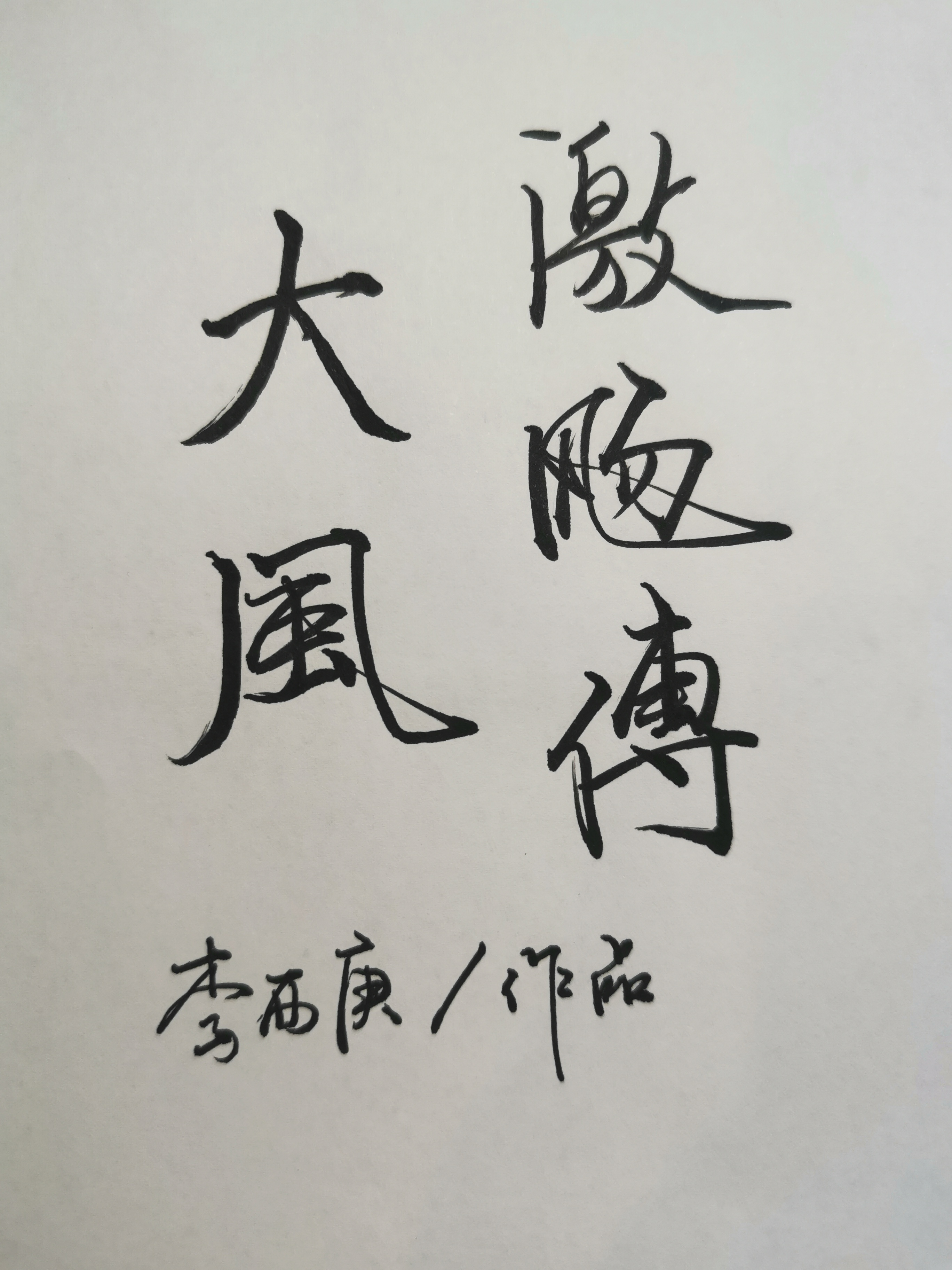“哎哟……”小太监几乎是跌了个狗吃屎,忙忙乱乱爬了起来,一看撞的是近日皇上跟前的红人,顿时又吓得跌道在地:“奴才狗眼昏花,因误了时辰赶着出宫,故而冲撞了先生,望先生恕罪啊!”
“无妨,你起来吧。”慕容子华伸手欲拉他,那小太监却吓得连连后退:“不敢、不敢劳动先生,奴婢这就告退、告退!”
说着,他便一溜烟地跑了。大约是走得太急,跑到不远处,又跌了一回。慕容子华见他的样子,不禁失笑,袖笼中的手握紧刚才小太监撞到他时给他的小竹筒,面色如常地回到了他的小院。
“密林十万,应约而至,静候佳音。”慕容子华无声地念完,嘴角微微上扬成一个完美的弧线,随即将纸条和小竹筒投入火炉,静静看着它们焚烧燃尽。他起身到窗前,看着青白而辽阔的天空,无风,无鸟,无云,空气中尽是寒冷而干燥的气息,天地之间尽是白茫茫的一片,看久了,甚至有种窒息的感觉。自他来到长青宫,人前人后,每分每秒,他不敢放松半分;每个夜深人静的独处时刻,珍妃的叮嘱总会一次次、一遍遍覆上心头,他时刻不敢忘记,那个人虽是自己的血缘至亲,但更是抛弃欺骗利用他母亲、亲手灭他母亲全族的死敌。此仇此恨,这么多年来深入骨髓,无以为消。从他见到那人的第一眼至今,他没有过犹豫,甚至连一丝恍惚都未曾有过,可正因为此,慕容子华有时甚至会觉得一丝恐惧——
他即将弑父。
大逆不道,弑父。
闽国,奥园,天章院。
褚令铁青着脸,拨弄着煎完药剩下的药渣,偌大的寝殿里都是难闻的药味和一股湿热之气甚至馊味,五月的闽国已是相当炎热,尤其是中午时分,若是屋里没有置冰,恐怕是呆不下人的。可此刻的寝殿中,不仅没有冰,而且所有的窗户需都按着褚令的要求紧闭着,这间屋子犹如一个密封罐头,里面的人都快要捂馊了。
阳樱按着闽国皇族新妇的礼制,头戴一套攒金点翠牡丹花饰,着一身白底正红的“百纱裙”。所谓百纱当然不是说真的有一百层纱,只是选用最上乘的轻薄纱料,最底一层为正红色,上面逐渐颜色变浅,最外一层是浅白透明色,且每一层上皆绣着位置不一的金银丝线,数十层穿上身上,却毫无臃肿之感,只觉高贵动人,行动之间,更是光彩熠熠。但在这闷热的屋子里,身着五六层纱的侍女尚觉闷热难当,时不时偷偷擦去额上和胸前的沁出的细密汗珠,阳樱却仍然从早到晚伺候在龙榻之旁,除了端药送水为闽王擦汗,她几乎是一直是跪着的。
“孩子,你去吧。纵然是三王妃本人,也不必如此伺候孤的。”闽王淡淡地说着,他的双目如同快要干涸的泉水,茫然地看着床顶的层层帷帐。
“既是公公身体有恙,儿媳伺疾也是自然的。阳樱有幸替公主尽孝,是阳樱的福气。”阳樱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坚定而冷静,她转脸看了看褚令,又朝闽王微笑道:“有褚先生在,王上很快就会大好的,那时公主受了那么重的伤,先生不过针灸了几次,用了一副药,也就好了。”
闽王微微侧脸,看了看这个温柔可爱的女孩,勉力挤出一个笑容:“好孩子,你说的对,会好的。”
“等靖侍卫将珍妃娘娘寻回来,王上便会好得更快了。”阳樱伸手探了探闽王的手背,仍旧是冰冷,到底伺候了这个老人几日,他对她又是慈眉善目,连大婚典礼后发现她不是公主,都没有责骂过一句。阳樱心中一酸,脸上却仍是笑着:“太子殿下差不多时辰要来侍疾了,阳樱出去看看。”
说罢,她便缓缓起身走出了寝殿。长长的裙尾拂过一层层台阶,轻飘飘地,犹如她的心一直悬在空中,紧张而不安。
“闽太子为什么这几日都不来侍疾,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王上的亲儿子!”阳樱焦急地拉着龙婉的手,两人走到寝殿外的一处树下僻静之地,“自己亲爹中毒病重至此,褚先生说了,只能尽力,什么都保证不了。他既是太子,又是王上现下唯一的儿子,居然人都不在奥园,到底在忙些什么……”
“赵大人昨日走时告诫我们务必小心此人,说他本来试图联姻追山族的王女,但未能成功,如今狗急跳墙,什么事都做的出来。”
“王上既已封他做了太子,他还有什么可急的——”阳樱话未说话,却抬眼见慕容靖矫健的身姿疾步过来,不禁面上一红,便撇了脸侧到一边。
“龙姑娘,王上今日如何?”慕容靖走近二人身边,也不去看阳樱,只是对龙婉略一抱拳。
“并无起色。”龙婉摇了摇头,见慕容靖面色一暗,又道:“好在也没有恶化的迹象,褚先生说,现在这药暂且能压着毒性,不至流入心脉。”
慕容靖眼中寒光一闪,低声咬牙道:“到底是何人,居然敢害王上!”
“你……”阳樱在一旁鼓足了勇气,终于道:“你寻珍妃娘娘,可有消息?”
“尚无。”慕容靖此刻终于看了一眼阳樱,顿了片刻,道:“你日日替你家公主穿红着绿,又在王上面前伺候汤药、端茶送水,不知道的,倒以为你才是你家公主带来的媵妾,那王府里住着的两个郡主,大概都是闲杂人等。”
此话正说到了阳樱的痛处,她一时脸上由红转白,又由白转红,终究咬着下嘴唇忍了下来,弱弱地说:“你怎样说我都行,只是你既答应了我……”
阳樱话未说完,慕容靖已经拂袖朝寝殿走去,看着他气冲冲离去的背影,她眼中的泪珠立刻滚滚而落,“龙姐姐,你说我是不是个下贱的女人?你看他从那日至今,从不肯正眼看我一次……”
龙婉无声地叹了口气,握起阳樱的手,“你每一日都要问我这个问题。阳樱,你若是心系慕容三殿下,就该心志坚定,只要能为殿下成就大事,你自然可得偿所愿;可你若是日日为着慕容靖那日骂你的那些话神伤心碎,那你真的要好好想想,你心中在乎之人,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阳樱的泪珠犹挂在脸颊,她嫣红色的唇被咬出了一个血印,有些慌张地望着寝殿的门口,想起慕容靖那一张充满怒意的脸,顿时一片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