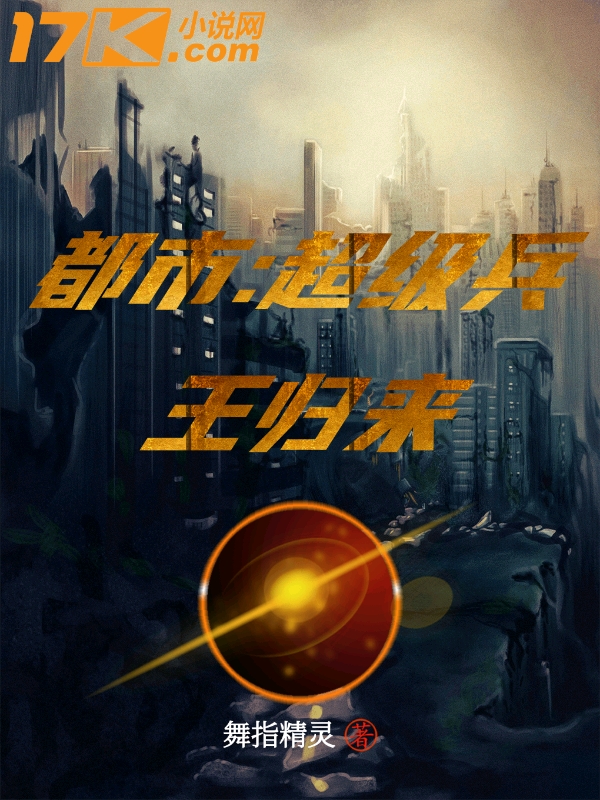宋府中,谢妫正在试新研制的砚墨,只见李画慌慌张张的跑进府,一进门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呼天抢地:“夫人!夫人,不好了!公子出事了!您快去看看吧!”
谢妫一惊,砚台一下子没拿稳,被打翻在地。
砚台落地的声音叫谢妫瞬间清醒,谢妫赶紧上前抓住李画的领子,急切道:“怎么回事?世安他怎么了?!”
“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求求夫人您赶紧去看看吧!”
“那还愣着做什么?带路啊!”
“诶,是!”
此时的李画暗喜,因为谢妫比他想象中的还要着急。
越是着急,越容易失控。一旦失控,就更能按照他计划的轨道走。
而刚出府,两人就迎头撞上了刚回府的宋熠阳。
见自家夫人脸色十分难看,宋熠阳赶紧上前问道:“夫人,你这么急匆匆的是去哪儿?出什么事了?”
谢妫一见到宋熠阳,就像找到了主心骨,立刻上前抓住宋熠阳的胳膊,急切道:“老爷,世安出事了,你快随我去看看!”
见谢妫如此急切,宋熠阳也不敢耽搁,招呼几个家丁就陪着谢妫朝城外赶去。
到了树林,李画佯装小心翼翼的为宋熠阳夫妇指路,那模样叫宋熠阳和谢妫一路都是提心吊胆的。
等到了事发之地,看着满地的狼藉,谢妫心早已跌落到谷底。
此情此景,哪怕是个傻子也能猜到个七八分。
谢妫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世安……在哪儿……”
声音是哪怕再努力控制,都无法抑制的颤抖。
“夫人,在这儿……”
李画则是假装声音颤抖,仿佛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一样,叫人不得不感叹一句演技超群。
谢妫在宋熠阳的搀扶下,走到那个宋世安的葬身之处。
只见宋世安静静的躺在泥坑里,满身泥污,面色蜡黄,狼狈不堪。
“……世安?”谢妫紧紧抓着宋熠阳的手,小心翼翼的唤了一声,却没有任何回应。
宋熠阳严肃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一言不发。
良久,谢妫才放开宋熠阳的手,缓缓朝着宋世安走去。
旁人皆敛声屏气,生怕刺激到了谢妫。
谢妫一步步的走过去,顺着下坡的时候划伤了手都仿佛没有感觉,满眼只有她的儿子。
“世安……”
谢妫把宋世安扶起来靠在自己的怀里,一边低声呼唤着,一边细细的替宋世安擦去脸上的泥污。
眼睛逐渐变得通红,却死撑着没落下一滴泪,只是一遍遍的唤着宋世安的名字,好像这样,宋世安就能醒过来回应她了一般。
正在李画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推动宋家夫妇报仇时,宋熠阳突然开口询问道:“李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画暗道机会来了,赶紧扑通一声跪地,“老爷,是我对不起你!只敢眼睁睁的看着公子被害,却不敢去拼命啊!”
宋熠阳一听,果然有隐情,怒喝道:“说!前因后果都给我说清楚!”
“是!”李画装作悲愤的模样,道:“我今日本来打算出城去看看有没有商队卖茶,好替老爷买上几饼,却正好看到公子和一个姑娘在说话,他们话还没说两句就又急匆匆的出城了。我见公子刚进城就又出城,觉得奇怪,就跟上去看了,没想到……没想到……”
李画说到此处,哽咽着快要说不下去了,惹得宋熠阳又是一声大喝:“到底如何,快说!”
“是,老爷!没想到那姑娘就是寒山寺的桃澈!而且那桃澈还是一个男人假扮的!”
“什么?”
不光宋熠阳震惊了,连悲痛中的谢妫都抬头看向了李画。
“那男人,其实就是寒山寺的清延!那个男人是个妖怪!他变化成了桃澈的模样,把公子骗到这个地方,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公子给……”
李画说道这儿,很自觉的噤声了,后面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谢妫一滴眼泪滑落,抱着宋世安的胳膊不自觉的又缩紧几分。
“李画,我问你,你可是亲眼所见?”宋熠阳似乎并不相信清延一个佛门中人会做这样的事。
“是,是我亲眼所见的!”李画连忙点头,“而且,据我当时听见的对话,似乎是因为公子和桃澈姑娘有私情,而清延对桃澈也……这才心生不轨,对公子动手的。”
李画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添油加醋道:“对了!那清延还专门带了两瓶酒,把公子害了后,还往公子嘴里灌酒,还踢到了那个泥坑里,怕是想伪装成公子醉酒失足摔死的!老爷,你一定要替公子做主啊!”
听到这儿悲愤交加的谢妫终于忍不住抱着宋世安大哭起来:“世安!我的儿啊,你受委屈了啊!”
“寒山寺……清延……”宋熠阳也是红了眼圈,拳头捏的死紧,“李画!你立刻回去召集所有人,还要报官,我要亲自上寒山寺讨个说法!”
“是!”
计划达成的李画立刻欢欢喜喜的跑回城了,不一会儿几乎全城人都知道了宋家公子死了,而凶手……就是寒山寺明殊方丈之义子——清延。
李画走后,宋熠阳跳下泥坑,把宋世安和谢妫母子二人都圈在自己的怀里,吻了吻谢妫的头发道:“夫人,咱们带着世安,回家吧……”
“老爷……老爷啊!”
谢妫缩在宋熠阳怀里哭的像个孩子,宋熠阳只能把谢妫搂的更紧,无声叹息。
另一边的寒山寺上,一个小和尚慌慌张张的跑到了明殊门口,一见房门大开着,也顾不了那么多,径直闯了进去,“方丈!方丈不好了!”
这时明殊正在静心抄写着佛经,被这一嗓子这么一喊,手一抖,一页佛经就白抄了。
“阿弥陀佛,佛祖勿怪。”明殊双手合十念了一声,把那页佛经放到油灯前烧了后,这才道:“怎么了?这般慌张,发生了什么事了?”
“方丈,不好了,清延师弟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