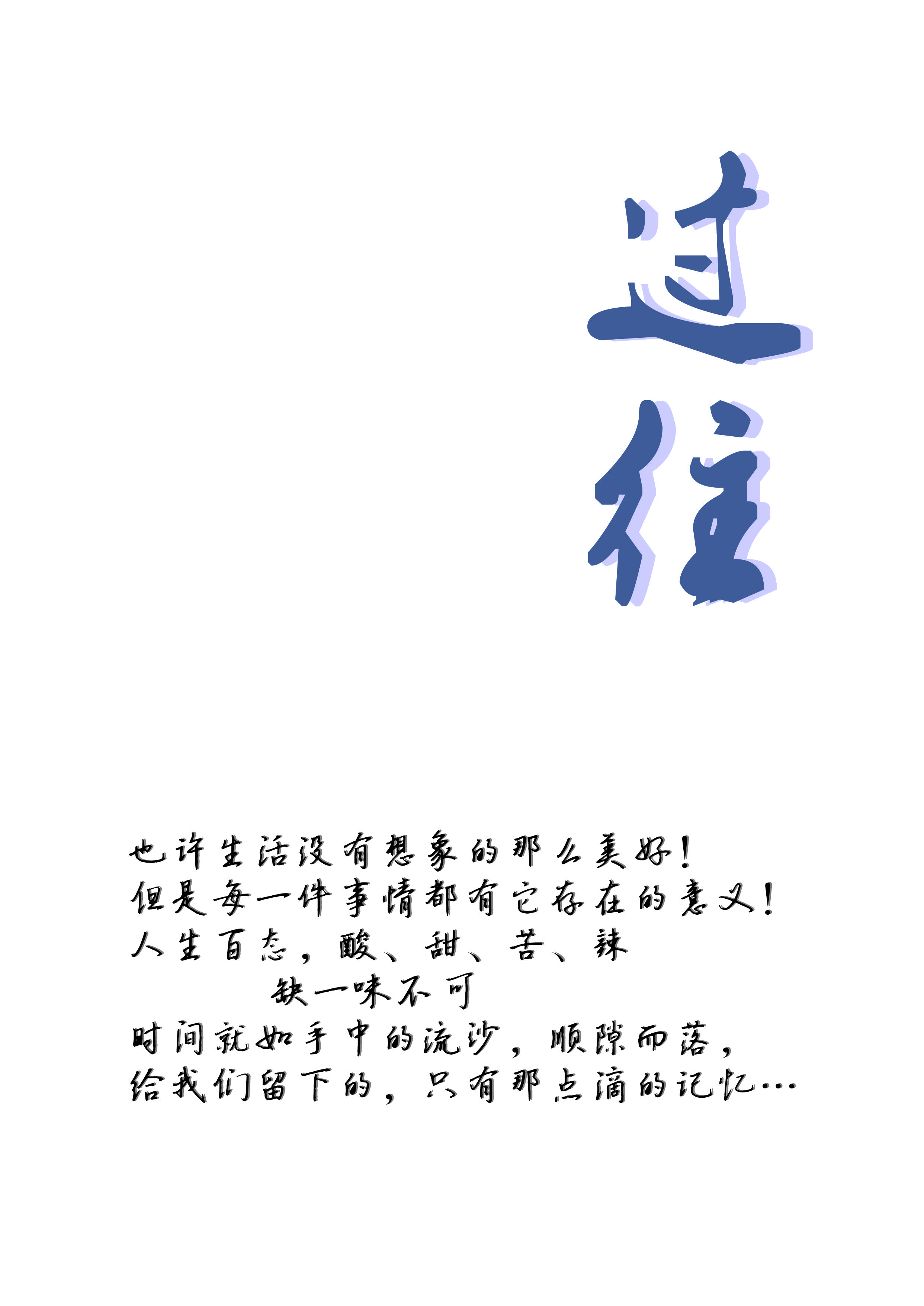路安现在,越来越像一枚鲜艳可口的苹果。和那根细细的红线一起,悬在面前。
可是,只能看,不能碰。碰了会上瘾。阿京从自己莫名的心跳中开始明白,对路安那双静静凝视的眼晴 ,她没有一点儿免疫力。所以,不能碰,更不能尝,尝了,会死人吧?因为那是毒苹果。
人贵有自知之明啊。知道前面是陷阱,跌进去桃色深深,要怎么办?惹不起却还能躲得起。除了这每天 不得不面对的晨练,阿京开始躲着路安了。
早点却是仍不得不共享的,有一天阿京试着提出胃口不好,练完功后想脚底抹油开溜,路子善立刻发威 了。吹胡子瞪眼,老头儿向和颜悦色,这会儿突然变了脸,还是吓人的。
阿京立刻不敢吱声,乖乖坐下来,端起碗心惊胆战瞥了这乖僻的师父一眼。不就是个早点么?和练功有 什么重要牵连?不吃岂不是还多省一口?
但得罪老人家的事情阿京是万万不敢做的,且不说尊老爱幼的美好传统,老头儿好歹也是每日里督促着 练坐看红绳大法的严谨师父,更是阿京现在的衣食父母。别忘记了,她还是老头儿名目下的助理呢。虽然偶 尔让买本书,削个水果,钉个扣眼儿,尽做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据老头儿有意没意地提点,阿京知道那点 儿薪资是不菲的。
路子善看阿京被他一呼喝之下立刻乖得如同家养的小狗一样乖乖坐下来一起用早餐,这才有些得意地呵 呵直笑。笑话。他每天都借了阿京的名义,敲诈着自己手艺不俗的侄儿做出美味又多样的早餐,怎么能让这 丫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开溜,坏了他老人家的的吃福?
若不是顶了阿京的名义,小安子八成也要如了他的愿,做了给他吃,但无论如何都做不出这样的风味。 轻轻淡淡,不曾点破,却又迷离不舍,暖昧环生,饱含了这样情愫在内的早餐,吃了可是要益寿延年的。估 计他温雅帅气的侄子,也就这会儿着了魔,能做出这样的美味。这温馨的时日一过,改日有了进展,因了心 意流转,做出来的饭菜便也变了,若饱含了爱意和欢喜,或者饱含了伤痛和幽怨,他老头儿便消受不起了, 那个,前者吃了上火,后者吃了伤脾,都万万比不得现在的温吞养胃啊。
老头儿边吃边乐呵。他是神算子,眯了眼晴,望一眼面堂,便知人是好运歹运。若是看姻缘,便如看风 景,或有穷山恶水,或有歧途末路,或有锦秀山河,或有山高水长。总之世间的情意两字,总是摸不透缠不 请。老头儿最不耐看这个,伤身又费神,还极易因要沉下心来以心头一双慧眼去识,反污了自己的清台明镜 。
可是面前这一对儿,往那儿一坐,便仿佛在两人周身,展开了一幅清浅幽雅的水山画。青山葱翠,流水 潺潺,这样一幅高山流水图,理应是一对好姻缘。只是这中间却又有一道坎儿。这画儿越是消楚,这情事便越 是坎坷。
老头儿也是年过半百的人,对这个向来不大以为然。不辛苦,哪能外练筋骨皮,内练坚贞气?不过这事 儿事关自己心爱的侄子,便只是因了乔珍当年那一句话,也是要不辞辛劳,插手来管一回,扶一把的。虽然 还不至动用了慧眼,老头儿却也吃出味来了:这丫头,一百个不自在,一千个不安心,想要逃呢。他嘿嘿笑 着,只不做声。心里乐得跳:好戏好戏。两个终于要开战了,俏徒儿要和好侄儿斗法了!
路安也察出阿京的不对劲了。
不过一个早餐,两周多来每天都是吃光喝净抹嘴走人,怎么好端端去了一回川城,就别扭起来了?如果 不吃,回了对面房间,小睛上夜班辛苦,这会儿还睡着,还不是要自己做?
他清楚阿京。这么多年,似乎总是一个人胡来,有一顿没一顿,如果不是有小晴,她会把自己喂得如旧 社会的长工,只有皮包骨了吧?虽说看起来风光,不大会做饭了,便去下馆子,但吃得总是不营养也不卫生 。这么大的女孩子,何曾想过要精心照顿自己?想到这里,路安又想到杨本虎。心里泛起的不是醋意,竟是 恨意。二十岁到二十五岁,应该是一个女子最美妙的年华吧?他和她一起,侵占了她那些美丽的年华,他又 为她做过什么?甚至,竟不曾走进她的心里,去抚摸最柔弱伤痛的那一角。
心痛她的过去,也庆幸过去已经成为过去!
路安淡淡地看了阿京一眼。她低着头,吃得匆忙。试图掩饰什么,但因了这份匆忙与略微的无措反露出 可疑来了。
微微地笑在路安的嘴角浮现。她那张小脸,简直就是一张表情符。是喜是愁,全写在脸上。这样子不安 ,打的什么主意呢?
阿京抬头,无意见到路安微低着头的笑,顿时愣了一下。他一个人笑什么?
再一抬眼,墙上有一幅画,装裱精美。黑色的镜框中,是一望无垠的雪原。一棵粉妆玉彻的小树下,站 着一只几乎和雪一样白的迷路小兔,微微立着身子,红色的眼晴如宝石一般闪着光,正在迷茫的雪原上寻找 着方向。
阿京垂下眼来,几不可闻地叹气:我的方向,又在哪里?
路安默不做声,将她这一切暗暗看在眼里。
阿京吃完,匆匆向路子善告个安,逃也似地出来。路子善似笑非笑地斜了路安一眼。路安神清气爽站起 ,看一看时间,不紧不慢朝门外走。
阿京把自己陷在沙发里。照着平常,洗一洗,是照例要去补个回笼觉的。这会儿却有些心神不宁。感觉 自己说起不要和师父一起吃早餐这事儿,似乎做得不妥了。似乎有欲盖弥彰之嫌。路安还笑。边吃边笑。他 笑什么呢。
阿京烦恼地撑着额头。又为自己的多事生气。他笑什么关我什么事呢?怎么会为了一个笑这样惴惴不安 ?
门轻轻响了,路安推了门进来。阿京瞄他一眼,更深地缩进沙发里。刚刚进来慌乱得很,忘记锁门了。 不然,便假装睡了。眼前这个大活人,竟突然变成了烦心之物了。
“今天不睡了?”路安坐下来。
“要睡。马上就睡了。”
“下午做什么?”
“呢……阿锦约了我逛街。”
信口编瞎话。反正,不要和路安去做什么。不要和他在一起。趁着还清醒时,离远一点。
不为成为那些流言的口实,也不让自己再搅进伤人的漩涡。
“哦,阿叶说今天平子说陪老婆去看看老泰山,说是阿锦小侄子生日。要带他去儿童乐园。”
路安不咸不淡地说。
阿京的脸立刻红了。不带这样儿的,不露一点儿声色,当场就把白话给戳穿了。
“我去睡觉了。我哪儿都不去。”
阿京有些赌气。声气也硬了。开始耍赖皮。垂着眼帘,眼观鼻,鼻观心。脸却微微地红了。
路安好笑地看着她。垂下的眼紧盯着自己的鼻尖,小脸上有红晕,犹似一个没有得到玩具而生气的耍赖 的孩子。粉嫩的脸白里透红,他有忍不住想咬一口的冲动。这丫头简直是他的克星,随意的一个小动作,就 惹得他蠢蠢欲动了。
路安也的确动了,走到沙发边凑近了阿京,鼻子快抵到她额头上了,声音里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宠溺:“ 小屁娃儿,你为什么骗人?”
阿京的脸更红了。他凑得这样近!他凑这样近做什么?身上的气息,带着淡淡的香皂清香,温热的鼻息 喷在她脸上。他就像一个巨大的热磁场。紧紧地逼在身例。阿京陡然地紧张起来,嗓子发干,身上也开始发 热。她几乎是从沙发上弹跳起来,慌乱地嚷:“我去睡觉!”
动作跳得那么猛,路安来不及闪避,鼻头便被阿京的头结结实实撞了一下。往后退了一步,啊了一声, 摸着鼻子皱起眉头来。
阿京在门口呆了一会儿,心里有些懊恼自己的不小心,却又不愿拉下脸过去看看他撞得重不重,矛盾犹 豫中,恨恨地一跺脚,说道:“你离我远一点儿!”
说着转身用力一甩,砰一声大响,把门给重重关起来了。
路安靠在沙发边摸着鼻子苦笑。这姑奶奶哪根筋不对劲了?不过凑近了一点儿,还没带什么威胁,更不 曾把想法付诸实施,就如此大发脾气?还让他离远一点儿?
站了一会儿,听得门里也没什么动静,暗暗摇头,在沙发上坐着沉思了一会儿。她变了。有什么地方变 了,又不大说得清。不过,总是好的,少发呆也少叹气了。不过变得有些喜怒无常。会在他面前使小性子了 !路安微微地笑起来。这才是阿京。小小的柔弱的心要承受那么多的往事,还要套一层面具在脸上的话,便 太累了。他要她从套子里出来,还原本色。离远一点儿吗?她害怕了?不。他会走得更近!
阿京虚弱地坐在床上,捂着脸,眉眼都皱成一堆了。自己这是怎么了?这样的失态?不过是站近了一些 ,怎么就这样紧张,像从没有被男人靠近过的青涩女孩!真是越活越没落了!
坐了半天,郁郁地躺下,听见外面没有动静,过了好一会儿,门被轻轻打开。阿京赶紧闭上眼晴,大气 都不敢出。路安走进来。在床边看了一看,仍旧带了门,一会儿便听见外面门落锁了。
他又进来做什么?不是让他离得远一点儿?阿京有些不耐,却似乎有更多的安心,朦朦胧胧中,做了无 数的梦,纷乱斑斓。
纵是如此,醒过来后的阿京捂着胸,坐在床边,更加害怕。她是不是要陷进去了?没有一点儿防疫力了 吗?趁现在还意识请明,早退步早抽身吧!
阿京下意识的拒绝和躲避让路安有些好笑,也有些惶惑。
她在怕什么?躲什么?
但无论怎样,她依然每天早早地练功,盯着门边的红线与他的身影,乖乖地吃早餐。这样就很好了。只 要她在身边,他就觉得安心。
路安下午通常都会出去录节目,到晚上才能赶回来。阿京上午补瞌睡,下午便在路子善的安排下处理些 资料传真之类,通常都是不大看得懂的隐语,偶尔代路子善回一些邮件。
日子就这么平淡地过着,似乎什么都没变。又似乎有什么悄悄地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