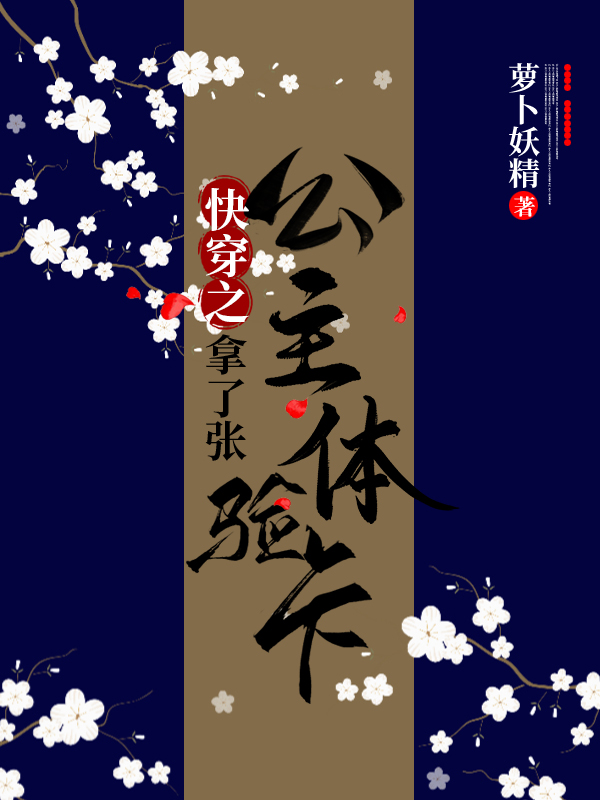阿京从此每天早早穿了这套蓝色的太极服爬到对面房子里的桌子上摆着童子拜观音的盘腿坐姿,一动不 动地盯着垂在墙角的细线。
第一天穿了这套衣服,路子善眉开眼笑:“这才像我的徒弟吗。尊师重道从哪儿看出来?就从这身衣服 上看出来!”
路安望望她,笑了一笑。阿京瘦,穿上这套衣服,撑不起来。细细如棵嫩竹杆俏生生立着。一头黑色的 长发绕在脑后,别了一小朵金灿灿的花。是这房间里最打眼的一道风景。
他不多说话,也不加以评判,笑笑便进了厨房。阿京冲路子善调皮的伸伸舌头。奇怪得很,进了这门, 她不怕师父,反有些惧着路安。似乎这功,在路子善面前不好好练习,是什么都不用担心的。虽然他是师父 。却总少着些师父的威严。但却不敢在路安面前摆出些偷懒怕苦的劲儿。
想想家世雄厚的一个俊雅公子哥儿,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四点便起了,阿京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 被比下去了。
路子善每天就坐在客厅里,也不管阿京是否要静静地练习,大大地开了电视,声音吵得震天响。其实老 头儿也不看,时常眯了眼睛似睡非睡。偶尔兴致好了,便绕到桌子走来走去,讲一些他当年血战沙场的轶事 。中间便随了老头儿的意愿,时不时提一点宋德南的点滴。
房间里戏曲台锣鼓罄敲得隆隆响,阿京不得不努力竖起耳朵听路子善絮絮叨叨说话。尤其提到自己的父 亲,自然希望一个字儿都不放过。虽然断续无章,也从中对父亲当年的事故知道些枝枝叶叶。宋德南当时身 手是极好的,以快疾出名。出手如电,伤人于眨眼间。阿京听得,心里又是欢喜,又是悲伤,又是神往。
可惜路子善说得少,大部分时间吹嘘着自己当年的神勇无敌。阿京有时听着听着便走神了。左耳朵时, 右耳朵出,眼睛望着盘起的膝盖,想着自己的心事。路子善总是在阿京发呆两秒内发现异常,便随手操起桌 上的苍蝇拍,劈头盖脸打下来。阿京老远便被苍蝇拍扇下来时的强风惊醒,举手护头,嘴里惊叫着:“师父 饶命!”
路子善并不真打下来,隔了头皮两三厘米便停了,苍蝇拍就在头上一抖一抖,阿京惊魂不定地摆正了姿 势,路子善便收了苍蝇拍子,贼笑着,居然朝阿京翻白眼!
阿京别的不怕,就怕路子善翻白眼。那一张皱皮巴巴如老树皮的脸,因了上翻露白的眼睛和不怀好意咧 着笑的嘴,竟似乎整个儿变了形,连鼻孔都往上翻起来了。变成完全扭曲的五官,似乎是一张面皮被生生地 扯了倒转过来了。绝对吓得死人的一张鬼脸。
阿京第一次正好大睁了眼睛看到,吓得惊叫起来,伸了手去捂脸,几乎从桌子上跳起来。路安猛然听天 惊叫声,一个箭步窜出门来。见这一老一小的胡闹,淡笑着摇头,到水机边接一杯水,慢悠悠回房去。
好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得不多,自被吓过一次以后,阿京长了些心眼,不敢随意走神。即使走神,眼睛也 死盯着前面。
但后面路子善竟伴着戏曲节目敲敲打打的传统乐器和咿咿呀呀的唱腔,有模有样的拿起一本道德经来念, 而且翻来覆去,每一首都要念上七八遍,他又特意地拉长了音调来读,如同古怪的催眠曲,阿京听得头晕脑 胀,昏昏欲睡,好几回如小鸡啄米一样坐在桌子上直点头。等到被苍蝇拍带来的风惊醒,便有了经验,绝对 不睁开眼睛,只是摆正了姿势,听得路子善嘿嘿乐完了,才眯开一只眼睛看一眼,鬼脸做完了!这才敢大睁 眼睛,继续往前看那根细细的线。
吊着的细线旁边便是路安的房门。他总是在阿京来后不久开门出来,准备完早点后便坐到房间里看书或 者用手提。阿京盯着细线的同时,余光便不免瞟到那个结实宽厚的背影。路安常会转过椅子来,在墙边的书 架上找资料。那一个刚直的侧面,比大理石雕像还要健美锋利。虽然只是余光瞟到,阿京也忍不住会脸红心 跳。若不是有所谓的练功,她纯粹就是坐着直勾勾如花痴一样盯着美色不眨眼了。
好在这样的情况每天都要发生,路安在房间里根本没有察觉,阿京日久也就习惯了。美色养眼,练功之 余偷赏一下,也是一桩乐事。
这样练习了十多天,阿京只要一看到那根线,便觉得眼花。那么细细一根线,盯了这多天,似乎竟在无 形中变粗了。模模糊糊,似乎有筷子大小了。
这一天,路子善跟着红曲自得其乐,摇头晃脑地哼哼。冷不防突然问:“俏徒儿,那根线变粗没?”
“粗了。”阿京随口应着。
“哦?”路子善来了兴趣,走过来:“有多粗?”
阿京竖起手指头比划:“比这个小一点儿。”
“哈哈。”路子善大笑起来,拍着掌在房间里乐:“不错不错,果然是颗好根苗。比我想的还要快了很 多。”
阿京不明白地看着他:什么快了很多?
路子善收了笑,难得正经地问:“虽然大了,清不清楚?”
阿京摇着头:“模糊。看久了,晕得很。”
路子善趿着鞋子,背着手,走来走去:“继续看。看到清楚再说。”
但显而易见老头儿心情是相当愉快,吃早餐时居然弄了一瓶酒来,又嚷着让路安炸了一碟花生米,烤了 一盘叉烧,细嚼慢咽。吃一口饭品一口酒,怡然自得,逍遥得像神仙一样。
阿京心里是越来越佩服路安了。练了那么久,每天都吃路安做的早点。还每天都应了老头儿的心情,换 着花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