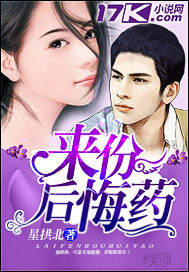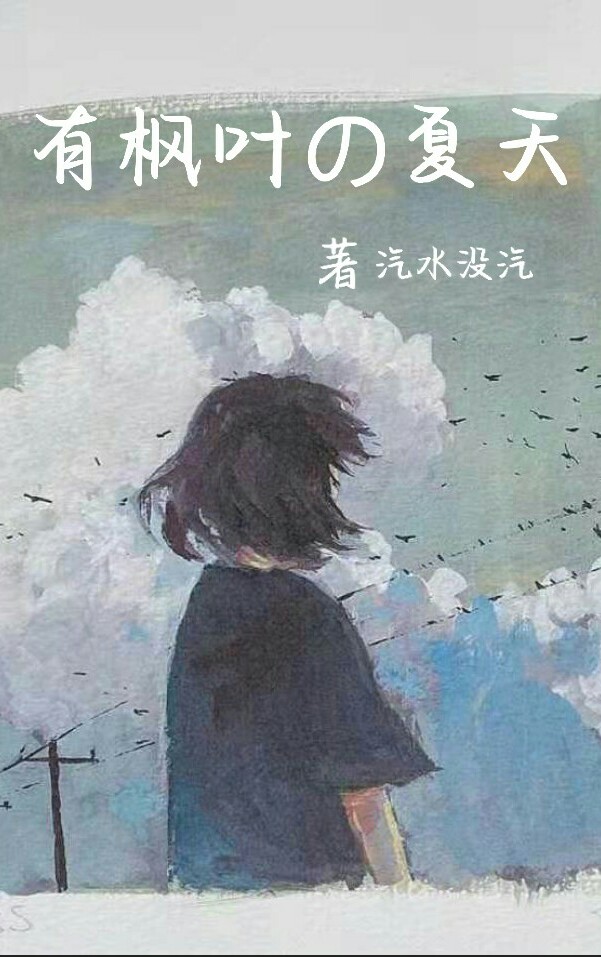我叫陈靖瑶,靖康的靖,是安定、平安的意思,瑶指的是一种美玉,寓意为珍贵美好。四岁的时候,母亲曾告诉我她帮我取“靖瑶”这个名字的含义,她希望我一生美好安定,能被很好的人珍惜。
阿曦总是说我的名字难写,笔画多,她写了很久也写不好看。她不知道,她的“曦”字也很难写,我足足练了两天,才搞清这个字的笔画,想让它规规矩矩地落在字框里,但我总是容易写出格。
很久以后,我才忽而明白,年少时我与何曦互相写对方的名字,竟早已预言了我们两个将来的命运。靖瑶、靖瑶,陈靖瑶的“靖瑶”带着再美好的祝愿,却注定不切实际。而何曦的“曦”,我永远无法把她框在标准的条条框框里,我想紧跟着她的脚步,却跳不出我画给我自己的牢地,反而把我自己困在其中。
将启程去一个新的地方,母亲很开心,晚上她陪着我睡,跟我讲小狐狸的故事时脸上带着笑容,她甚至跟我说狡猾的狐狸看上去诡计多端,可是如果它像狮子一样有力量,它就足够可以自己保护自己,就不会有那些阴谋诡计,人人喊打了。
我半知半懂,那个时候我跟所有的小孩子一样,喜欢正义可爱的动物,我不觉得狐狸有什么可爱的地方。
从A城到B城的那一晚,我们家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不仅庆祝我们一家乔迁新居,也庆祝父亲的升职。那时父亲跟母亲说,他在B城遇到了一个贵人,这个贵人还是母亲认识的人,那便是何曦的母亲何洛卿女士。而此时,何曦的父亲姜仲庭先生已经处于B城权利中心的位置,是我父亲上级的上级。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阿曦,在我未与她见面前,我就已经听过她的名字,不过那时父亲母亲话里话外都叫她小曦,好像这样显得关系多亲近熟稔一般,我一直以为阿曦跟随她父亲姓姜,后来才知道,阿曦是随母姓。
他这样跟我母亲说的时候,我母亲只是凝着眉点了点头,因为她和阿曦的母亲在部队的时候是很要好的朋友,在她嫁给我父亲的两年后她听说了好友下嫁的消息,她当时还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想不到那样高不可攀的将帅之女,居然最后会选择部队里一个小小的文职干部。
在我母亲打算带着我去拜访阿曦母亲的时候,我父亲只是跟我交代让我与阿曦好好相处,因为阿曦是他上级的女儿。可是在我心里,我却并不想去讨好一个我从未见过面的女孩。
我那时候年纪小,不懂得门第之见,世家之分,我只知道,我的父亲是个官,我爷爷也是个官,我外公是非常有名的画家,我母亲也是个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她会唱曲,还会国画。从小我身边的小朋友们都非常羡慕我有那么厉害的爸爸妈妈,这一点让我非常骄傲。我长得像我母亲,亲戚邻居们会夸我长得标致,在学校里,我一直都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我,他们会经常夸赞我,这也让我感觉自己非常优秀。
我一直以来努力想表现得更好,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最棒的孩子,就是为了讨他开心,让他能为我骄傲,可是他什么都看不到,当他说阿曦很聪明的时候,好像她比我更重要一样,这实在是让我伤心。我觉得很不公平,在生气和伤心,以及嫉恨的心情中,我等待这个女孩的出现。
阿曦和她母亲很像,我从第一次见到她起就发现了这个事实,但我指并不是简单的外表上的相似,当然阿曦也有像她母亲的地方,不过她的眉眼含情温柔,细腻动人,更像她的父亲。
阿曦像她母亲的地方在于她那双眼睛和自信果敢的气质,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刻意想表现出聪明的样子,却尽显笨拙和丑态,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精心打扮后推上台表演的舞蹈演员,却在上台的那一刻摔坏了身上的裙子,而阿曦轻一登场就轻而易举亮出了主角的身份,告诉我,替补的群演该退场了。
当她的眼睛带着一种怀疑和审视神情看着我的时候,我将目光转移开了,因为我怕她会看出来我的心虚。当然,我相信阿曦在第一眼见到我的时候,一定也能看出来我们两个人已经在相互较劲,那是出于一种天生的直觉,她应该意识到本质上我们都是自尊心非常要强的孩子,我们渴望被肯定,同时也渴望自己成为独一无二的那个人。
一直到现在我都说不清楚,在阿曦身上到底有什么地方深深吸引我的,让我不自觉就想跟着她。我想也许这就是一个人的气场,一种天生自带的领导者的天赋,阿曦是我认识的同龄人里唯一具备这两种气质的人。而在我们之后长久的关系里,不管我们距离近远,联系深浅,不管我独立于她过我自己的生活,拥有我自己的事业,阿曦她都在我们的关系里处于绝对领导者的位置,而我始终也被她影响着。
起初阿曦对我戒备心强,对我也不是很好,我虽然总是有些小生气,但是第二天我又会原谅她,继续跟在她身后。但我这么做的原因不是因为父亲的反复叮嘱让我跟她搞好关系,而是一方面我被她吸引着,另一方面,我想见识这个女孩到底有什么样的真本事,我想看看她是不是虚有其表,有什么样的弱点。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心怀不轨的坏人,“卧底”在她身边,随时等着她身上的那些光环,恩爱高贵的父母,富足健康的家庭,聪明的头脑,某一天被黑色的光掩盖,失去它的光芒,被暴露出最真实模样。
我和阿曦正式成为好朋友,是在她跟我和解那天,那天我被学校高年级的孩子欺负,是阿曦出面帮了我,她很勇敢跟那些高年级学生对峙,仿佛她一点儿也不怕他们,当然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安嘉树。
我并不是很喜欢安嘉树,我其实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走到一块,因为他们看上去是两个世界的人,但是阿曦很维护他,我经常看到他们在一块学习,一起讨论问题,有时候阿曦会充当一个老师的角色,辅导他的功课。上了初中的之后,安嘉树的成绩突飞猛进,两个人也不在一个班级,不过他们还是经常一起上下学。周末的时候我会按照约定去书店、电影院这种场所找他们。那时候阿曦喜欢上了林语堂的书,我决定开始写小说。
刚开始我写的并不顺利,经常写到一半就进行不下去了,但是阿曦一直都鼓励我,不管我写成什么样子,她好像是唯一知道我想要表达什么的人,我写小说这件事也一直只有她知道。
阿曦身上有一种能让别人坚信力量,就好像不管我跟她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她都会相信,从而让我自己也相信。我跟她一起跟着我母亲的老师学国画的时候,我说我长大后一定会成为一个比我母亲更厉害的画家,阿曦会说,我相信你,阿靖你一定会的。当我开始写小说,我说我将来会成为小说家,阿曦也是这样坚信的。
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见识了我父亲残忍粗暴的一面之后,那些担忧、恐惧、自卑、自怜的情绪吞没了我,而阿曦的话对我来说是一种温柔且坚定的力量。夜里有时候我睡不着,我给阿曦打电话,借口说我又想到要写的故事了,阿曦听得很认真,而那些我临时编撰出来的情节,竟然真的也被我写了下来。
那时候我除了阿曦没有别的朋友,如果能玩到一起的人也算朋友的话,那安嘉树也算一个吧。我在学校里面表现也很优异,但沉默寡言,班里的同学跟我的关系都很一般。父亲总是跟我说,那些孩子跟他们多打什么交道都不会让我学到什么东西,真正值得我用心交往的只有阿曦,所以他对我和阿曦成为好姐妹的结果非常满意,但是其实我并不是听了他的话才会这样的,而是我真心觉得其他人跟阿曦相比起来都不重要,甚至除了我母亲,连他我都不在乎,不关心,我甚至开始厌恶他。
那天是很平常的一天,放学后我留下来准备班里的黑板报活动,我不知道,也许骨肉之间真的存在心灵感应,当我到家的时候,我感觉到胸口一阵闷痛,我喘着粗气,感觉每一口呼吸都像是要从我身上扯下一块肉来,我听到从客厅传过来的东西被砸被摔的声音,当时我害怕的不敢走进去,我一直捂着我的胸口,手指抓紧了肩包的袋子,直到我到了父亲的怒吼声,还有母亲呜咽的求饶声。
我冲进去,亲眼看到了我母亲倒在了地上,门廊处的柜子遮住了她的下半身,我只能看见她蜷缩着抱住自己的手臂。我想跑过去,可是她也看到了我。我母亲留着泪对我摇头,她痛苦的挣扎着,她倒在地上,脸上和手臂伤还有伤,可是她拼命地对我说别过去,她根本发不出什么声音,只能不断地摇头。
我听到摔东西的声音停了,我父亲啐骂了一口,他转过身去,我只看到他半个背影,他穿着一件灰蓝色的衬衫,同色的长裤,正在费力拉扯着系在脖子上的领带。
今天早上他穿着这身衣服出去的时候,我母亲还送他走到门口,他还笑着跟我打了下招呼。可是现在,我完全不认识这个站在我眼前的人,我只能狠狠地盯着他,我希望他马上变成凶恶的狼犬,现出他的原形,这样子,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不是我的父亲,不是那个我一直崇拜着,看作是我的榜样的人。他是妖怪化成的,他不是我的父亲。
我知道我母亲是先让我在他看到我这样赶紧离开,她不希望他知道我撞破了他向我母亲施暴的行径,她是想保护我,不想让我父亲在被激怒的情况下又对做出什么伤害我的事情来,我根本没有力量对抗他,足够保护母亲和我自己。
所有已经遗忘在成长的过程中的那些暴力、让人难过、难堪、恐惧的记忆全部涌现了,我全部记起来了,在我还小的时候,那时候我跟母亲搬来B城不久,他就对我母亲有过施暴的行为,只不过当时我被他关在卧室里,我不知道我被关了多久,我只知道最后是母亲将我从地上抱了起来,她笑着对我说,瑶瑶做噩梦了,我们去床上睡觉好不好。
我完全忘了,完全忘记了这段恐怖的经历
我哭着跑了出去,像不要命一样地跑了出去,我发誓,我从来没有那样恨一个人,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恨,但是那一刻,这个虚伪的刽子手亲自教会了我什么是恨,我在心里狠狠地发誓,有一天当我也亲手把刀刃架在他的脖子上时,他就会知道那种恨是什么感觉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找到阿曦的,在一条小时候我们经常会路过的街道上,路口处有一棵很大的樱花树,以前我们一起上学的时候,那路口附近有一个卖早点的摊子,老板会在樱花树下设一两张桌子,阿曦和我,还有安嘉树,我们会很早的出门,然后就坐在那里吃早餐,褡裢火烧、油条、馄饨、肉包子、芝麻煎饼,每一样老板都做的非常好吃。
自从我搬离那个小区,再这样跟阿曦在一块吃早餐的机会几乎没有,阿曦是一个嘴挑又贪吃的人,有一个对美食比狗还灵的鼻子,总是能找到一些具有特色又很非常好吃的店铺,跟着阿曦吃饭,乐不思蜀。自从我上了另外一所学校,能陪阿曦这样胡吃海喝,大饱口福的机会就归安嘉树一个人了。
我还记得那天我从家里跑出来,我见到阿曦就是在那个路口,安嘉树就站在她身边,替她拿着书包和吃食。他看阿曦的眼神、笑容,还有阿曦看他时眼睛里的光亮,我才发现原来他们站在一起,这样亲近和美好,仿佛与其他无关,任何人都无法去融入、去破坏这样的画面。
我嫉妒安嘉树,一直以来,我害怕失去母亲,也害怕失去阿曦,可是我就要失去母亲了,也要失去阿曦了,我感觉伤心极了。
我没有将发生的事告诉阿曦,晚上我睡在她的房间,阿曦并没有察觉出我的紧张和不安,我不想睡觉,我害怕等我醒了,又掉入到另一个更恐怖的噩梦里。我甚至在想我母亲是不是已经死了,只是我一直在自我逃避和无视,不愿意承认而已。
阿曦睡着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探过她的呼吸,很细很软,和母亲的完全不同。我偷偷爬下床去打电话,在被接起的那几秒钟我放下过很多次,我怕得到任何一个我不想要的结果,却谢天谢地上天听到了我的祈祷。母亲努力笑着,问我,瑶瑶,又是做什么噩梦了吗?
她说,好孩子,快去睡吧,睡醒了,明天就可以见到妈妈了。
如果可以我想相信母亲说的,那天晚上我看到的,我经历的一切只是一场梦而已。我本来就是和阿曦在一起的,因为突然做了这样的噩梦所以醒了,然后母亲告诉我的,是的,瑶瑶,你只是做了一场梦而已。如果可以,我想像小时候一样,相信、忘记,并从中醒来。但是我知道我没有,我还是感觉到难过,因为我知道另一个我已经在被扼杀了,包括我心目中的母亲。
以前我一直以为只要我想得到的东西,我就一定会努力得到的,那是我的野心,也是我的偏执。我从小就希望能成为父亲的骄傲,后来我做到了,我一直嫉妒安嘉树在阿曦心目中的位置,我想取代他,可是我不需要和他竞争,他和阿曦之间一直都存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但只有我和何曦一开始就在彼此身上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
高考结束那一个暑假,阿曦的父母离婚了,阿曦是最后一个知道的,用她的话来讲是被通知,好像与她无关,好像她无关紧要,好像她不是原来的她,也不知道真实的自己。
我从来没有见过阿曦那样,她像一个氢气球完全被放走了气,像一颗玻璃珠没有方向的滚动,没有坚定的眼神,只有糊涂的沉默,好像她长大了,又好像变小了。我从来没有一刻像这样觉得我们俩可怜极了,这样的处境,这样的遭遇,我们的生活莫名其妙,比起那些平凡且快乐的孩子,我们究竟赢了什么。
我同情和可怜阿曦,完全没有我小时候设想的那样得意和高兴,因为我们同病相怜。
那个时候我仍然想着逃离有我父亲的生活,逃离他的暴力、残忍和虚伪,还有我母亲的不幸、懦弱和虚荣的自尊。我忍耐了很久,终于等到了我毕业的这天。我跟阿曦说,我想一个人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读书,如果可能,我就再也不回来了。我跟她说,阿曦,我们一起逃亡吧,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把这里的一切都忘了,永远不要回来了。
我不知道阿曦知道多少,她问我,你要丢下你妈妈不管吗。我对着她点了点头,我说,阿曦,那些抛弃我们的人我们也抛弃了好不好,不是我们先不要的,是他们先不要我们的。
阿曦没有告诉我她的答案,但是我们两个人确实一起逃亡了,没有告诉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也没有告诉安嘉树,就我们两个人,一起从B城逃到我故婆的故乡。我们乘着火车,一路往南,我们什么苦都不怕。
我很惊讶于阿曦的干脆,旅途的过程中,我没有向她提起过安嘉树这个名字,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阿曦没有带上他,也从来不提起他,也许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在心里想,虽然我充满好奇,可是我幸灾乐祸。是的,我打败了他,因为我知道从那天开始,我们三个人以后都将分开走不同的路,不管能否同行,最开始跟阿曦一起走的人是我,即使分岔也走不到一快的,是阿曦和他。
我和阿曦住在我姑婆以前的家,那是一座老房子,房子是木质的,只有一层,四个房间,带一个30平米大的院子。我姑婆在我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只记得小时候她特别地疼我,我以前也跟着她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她去世时将房子钥匙留给了我。
这房子看上去破旧杂乱,跟这个海边的小镇一样带着一种潮湿腐烂的气息,我和何曦实在太累,没等我们收拾完,就扛不住困意先打了个盹。太阳下山之后,我们被饿醒了,拿着兜里剩余不多的钱出门去附件的卤肉店,痛痛快快地来了份卤肉拌饭。余下的钱,我们买了新的被子和床单,还有接下来两天要吃的水和干粮。
我和阿曦两个人出门并没有带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赚钱的办法,也许我们很快会饿肚子,也许我们要下地自己种菜,也许我们可以考虑跟着附近的渔民一起出海,免费给他们当劳工,只要管我们一餐温饱。
未来有太多不可知的事情,但我们没有想过明天会去哪里会做什么,我们只想明天要吃什么。我的心情感到从未有过的愉快和轻松,有阿曦在,一切未知都不可怕,我们是那么年轻,我们是那么幼稚,但我们无畏,只要能让自己开心的,我们称之为勇敢。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们窝在沙发上看书,收拾家里的旧盆旧罐,种上蔬菜,也在清晨跟着渔民一起出海,我们在海上看日出,夜里能看到星星,还能从对面的岛屿上能看到这边的灯塔。
阿曦在我们出来之前给他外公留了信,没有说我们去了哪里,只是让他们别替我们担心,也不用过来找我们。如果我们想要藏起来,我们还以可以走得更远,如果我们放弃了,就可以回去。我们逃避做出这个选择,但我们至始至终都知道,离我们做出那个选择的时间越来越近,只是现在还没走到那个瞬间。
当阿曦早晨过来敲我房间门的时候,我知道这个选择的时机已经到了,而阿曦的眼睛重新出现那种坚定的神色,我知道她已经做好了选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甚至松了一口气,不仅仅是为她,也是因为我自己。
阿曦在回B城的一个星期之后就出国了,和她母亲一起,而我也决定尽早出国,但我要和阿曦做不同的决定,我要斩断一些与过去,与我的父母有关的羁绊,至少要由我先开始。我向我的父母提出要求,希望他们尽快离婚,和我预想的不同,我以为首先站出来反对并大发雷霆的会是父亲,但没想到却是母亲。
她将我叫到她的房间,开始指责我不识好歹,我拆除她的故作坚强和虚荣,她从来没有对我发过那么大的火,我们大吵了一架,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没有任何改变。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悔,坚持要跟我父亲在一起,难道那一次次的暴行和虚假的承诺还不够看清他的真面目吗?是爱吗?如果他们之间是爱,我们之间是爱,为什么我们心会如此的不平静,我们现在会哭成这样,我们会恐惧成这样。那也许是我这辈子我说最狠的话,我说,她从来都没有像一个母亲一样的爱我,保护好我,她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需要什么。
在伦敦生活的四年,我很少会想到我以前的家,我以前的生活,我觉得我已经和过去彻底的告别了,跟阿曦的选择不同,我逃开了,逃到了更远的地方重新开始。
那几年我的性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变得开朗了,我交了好多的朋友,各个国家的,各个阶层的,我喜欢上了Beyonce,喜欢跳舞,也喜欢酒精,我在俱乐部里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觉得那样的生活自由自在极了。除了我的灵魂,除了我偶尔想念阿曦。
我知道安嘉树去了美国,阿曦跟我说过她有一直在跟他联系,只是安嘉树很少主动跟她提起自己。我和安嘉树已经完全没有任何联系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一直很一般,只是因为阿曦,我们才看上去走得比较近。我厌烦安嘉树显得高高在上和冷漠的态度,但是我不会当着阿曦的面说他的坏话,我只是有点吃醋了,我跟阿曦说,你为什么要给他写那么多信,不能给我多写一些吗?
阿曦说,我给你也一直写信啊,而且我还寄给你各个不同地方的明信片,封面都是我亲自拍的。
我说,但那不同对不对,你给我写信是牵挂和联系,给他写是思念和不舍。
我想我在问出口的已经知道了我想要的答案。
阿曦跟我说,她知道他父亲跟安嘉树说过什么,就像她父亲对她母亲造成的伤害一样,她在挽救,也在挽留。
我觉得阿曦太傻了,我生阿曦的气不愿意理她,等我气消了,我也回国遇到了费南,人生中另外一种值得我去追寻和付出的爱,我的生活终于可以真真正正的重新开始,不是因为我失去的那些爱而哀求寻觅,而是因为我得到的崭新的爱而珍惜呵护。
那两三年我过得很充实,我努力工作,努力攒钱,我想在A城买一套房子,可以住三四个人,我想等我买了房之后就换一个工作,和母亲一起回A城去,费南也可以过去和我们一起生活。这些年我和母亲很少说话,我们见面除了一起吵架,就是吵架之后一起哭,我还在气她的固执和愚蠢,但是我想我们都开始新的生活。
我没有料想到她会突然离开,好像她只是给我做了一顿晚餐,然后说出去买点盐,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在想,这些年我们究竟过成了什么样子,因为得到了什么却失去了那么多,时间、家、快乐甚至是生命。我和母亲又因为什么,这样遗憾,这样痛惜的结局,而父亲,他冷眼旁观,宛若他从未进入过我们的生命。
当父亲对我说费南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他信任得过的人的时候,我突然回到小时候,他跟我说,阿曦是姜先生的小女儿,你要好好跟她做朋友知道吗?一切痴心妄想,都是一厢情愿。我恍然明白,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从噩梦中醒过来。
那日我给阿曦写信,我在信中说道:阿曦,你说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原罪,有自己的活法,有面对真相的权利,也有知道真相后挽回的方式,我明白得太晚,当我想要挽救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但我总觉得更应该看清楚真相的还有加罪之人,应该受到惩罚的人将最终戴上枷锁接受裁判。又不知你能否收到这信,但明天我将从梦中醒来。抱歉以这样的方式叫醒我,只有你知道,那一刻我最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