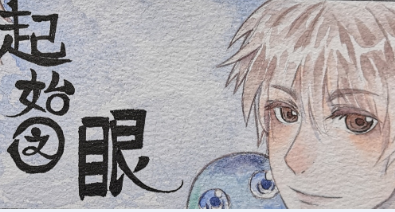我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回国,飞机落地的时候,一缕金色的阳光正好落在窗前。 我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觉,直到天快亮了才睡着,出机场的时候整个人都晕乎乎的。
在停车场看到姜离的时候,我并不感到很意外,他和母亲之前通过电话,我大概能猜到他们通话的内容。
姜离,距离上一次我们见面已经过去一个冬天。那个时候他刚过完三十二岁的生日,再见到时,母亲说既然错过了,那我们再补一个吧,于是我们便一起去Seasons in the Park吃了一顿大餐。
我其实不知道母亲和姜离是什么时候联系上的,在我以为她已经切断国内一切得联系之后。
像她所说的那样,作为母亲,她尽职尽责,并没有任何对不起姜离的地方。而姜离也说,作为儿子,母亲对他尽心照顾,也并无私心。而我们三人又如何走到今天,这中间发生那么多事,大概只有我不是很懂。
姜离是非常了解我的人,我喜欢什么颜色的花,喜欢什么样的餐厅,甚至是起居习惯,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在知道我要回国后,他把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好。晚上我们去以前最常去的特色店吃饭,重温过去的时光,本来也是久别重逢值得高兴的一件事。但那天晚上回来之后,我就因为水土不服而引发肠胃炎吊了整整一夜的水。姜离嘲讽我说是我乐不思蜀,连故乡都不认识了,就连这“胃”也是。但我却想,是故乡先不认识我了还不一定呢。何况物犹如此,人何以堪?
我们好像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亲密无间,他以前也总是整夜都陪着我。我们有时候说会话,玩会游戏;有时候他看他的书,我睡我的觉;后半夜他靠在椅子上打盹,而我已经睡醒了,见快输完了就叫醒他。以前我们之间就算不说话,好像也从来不会无聊,但现在我已经不太习惯了。
不知道姜离是不是也知道我早就不再是那个依赖他的小女孩了。他可以无视我的不习惯或不自在,但以前我们一对视,他会问我‘想要什么’,现在他只会跟我说‘再睡一会吧’。改变了就是改变了吧,有些时候即使我们自己并不承认。
阿靖从来不肯在我面前承认在她母亲过世之后她变了很多的事实,我总担心她给自己过多的负担和压力,这种担心从她母亲去世那晚一直延续到订婚仪式前夕。直到我在礼堂门前看到手捧着白色蔷薇花的她,穿着白色的露肩纱裙,微笑地对我说:“hi ,阿曦,你来啦!”
上帝,我发誓我在那一刻曾拼命地在心里祈祷,请看看这个年轻的善良的姑娘吧,请给她穿上最美丽的婚纱,让她做最幸福的新娘,请赐予她一双携手共度风雨的手,让她余生不再孤单。
我看向与她并肩的那个人,他同她一起站在我面前,他同她相依相偎,却没有执手。
梦境碎了。
Herbert医生慢慢地将诊疗室的灯打开,调到一个他认为满意的亮度,他看见我醒了。
“二十五分钟,你比之前多睡了五分钟,是梦到了什么了吗?”他看了一眼计时器,开口问我。
“没,还是之前一样的梦。”我说。
“一直都是到那里就结束了吗?那这之前,有没有出现新的场景。”
我陷入深度催眠后的疲惫中,仔细想了下才跟他说:“好像有的。”
“是什么场景?”
“都是些以前的事。”
“比如呢?”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起身,利落地穿好鞋子。
Herbert医生也站起来,“Sunny,你得告诉我才好帮你,也许这就是关键。”
我说:“我现在想不起来了,等我想起来了,我再告诉你。”
“Sunny......”
“我保证。”我举手向他做发誓状。
从我就诊以来,因为我这个不配合的病人,他的心理疗法一直疗效甚微,但他还是很有耐心跟着我的节奏进行他的疗愈方案,我就完全地信任了他。是以我跟他保证绝对不会半途而废,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过程会有多长。
Herbert医生总说我能主动来找他,对于“PTSD”的治疗已经是跨出了最重要的一步,而我们的疗程也已经到了最关键性的一步,那就是我要去去直面它和正视它。他一直在等我做好准备,然而我们的催眠治疗一直止步不前,我总是在最后一个画面醒来,然后很难再次陷入沉睡。
医生他也建议我应该将我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告诉我母亲,可是我想母亲大概早已知道,因为我有好几次跟她提到靖瑶,她总是不自然流露一种很担忧的样子。何况她以为我对自己的病情一无所知,我若是告诉了她,反而让她忧心。所以我只好拜托他替我一起瞒着,至少在没有任何起色前,暂时先不要告诉我的母亲。
我记得那一年冬天温哥华的天气罕见的寒冷,屋子里开着暖气,烧着炉火,母亲还是穿着厚厚的睡衣走到阳台上看雪。
来这里两年,这是我们第一见温哥华的雪。大雪覆盖整个城镇,我和母亲围在火炉边一块吃着茶点一边看美国西部电影,直到第二天我们在沙发上睡到自然醒,屋外的雪还没有停。
母亲准备去做早餐,她告诉我天还很早的时候助理打过电话过来,说天气很糟糕,今晚飞伦敦的航班全部取消了,她打算给我定12月27的飞机票。
母亲说:“干脆晚几天吧,你才刚回来,多在家里休息几天。”
我说:“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还要跟举办方商量呢。反正要等圣诞节过了之后。”
“圣诞节就是明天来了。”她烤完面包之后开始准备切水果。
“要来一个苹果吗?”她问我。
我说:“当然”
我和母亲都习惯过国内传统的节日,但是因为在海外,圣诞节那天还是有很多我们的朋友打电话过来庆祝,甚至我们的邻居还过来邀请我们一起和他们庆祝。
我对母亲说:“去感受下节日气氛吧,玩得开心点。”
“那你呢?”
“我还有一点工作要处理,等会就过去。”
事实上即使不飞伦敦,我一样也有很多工作要忙。丹尼发过来很多的图片都需要我再次审核,我还得写上注解,包括这次我在苏州拍的人文照,很多我都还来不及整理。丹尼虽然是个中国痴,但是他对苏州城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少之甚少,每一张照片上的景点我都要查相关的历史背景,然后翻译成英文。
中间Herbert医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他的诊所了,他一直在跟我约下次治疗的时间。不过这次即使他不跟我联系,我也会主动给他打电话的。这两天我都梦到了阿靖,两次都不是催眠的情况下,两次醒来都控制不住的抑郁。我不知道是不是症状更严重了,但是我却不是很担心,事实上我很清楚阿靖为什么会出现,只是每次当我意识到的时候都很难受。
医生很关心我的情况,他问我:“还是在同样的场景醒来?”
我说:“不是,这次完全不一样。”
我跟医生说明,以前一直都是在重复之前的场景,然后在婚礼中醒来,可是这两次梦到的都是阿靖给我写信和打电话,最后一次就是在陈太太去世那一次。
医生说,也许这是好现象,那些我不愿意或者刻意回避的有关阿靖的记忆以梦境的形式呈现在我面前,比我直接无限期地拒绝回忆要好得多。只是如果我真的感觉压抑和悲观,没有办法自我调节和控制,让我一定打电话给他。
我已经很久没有犯病,这段时间忙碌的工作让我几乎都忘记了,所以我对医生的话并不在意。但是没想到几天之后医生一语成谶,而那时候我刚碰到安先生。
这也许是相隔九年的世纪重逢,即使在我看来我和安先生一直都不是真的分开。我只是没想到的我们会在那种情况下见面,我当着他的面抽了支烟,还没来得及装作无所谓地将烟雾吐出来,就被呛住了。呛得一口气差点没背过去,呛得心脏疼,呛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却只看到他发白的脸色。
母亲说对了,我很想他。阿靖也说对了。
阿靖,可此生我喊出这名字的时候再不会有人回应,母亲说过,阿靖已经去世了,当我看到一个月后阿靖寄给我的信,我也知道阿靖是真的已经永远离开了。
在最后的一刻,在枪声响起之前,阿靖说:“阿曦,我原本想带上你一起的,可是你已经有安嘉树了。”
又是一场噩梦,在噩梦中惊醒。
我坐起身,开灯,凌晨四点,身上的睡衣全都湿透了。
非常难受,浑身战栗发抖,冒虚汗,头痛,胃部也痛。我赶紧在床头柜里拿了药,就着冷水灌了进去。
我控制不住身体发冷,抱着自己的胳膊,拼命告诉自己意识还很清醒,一切都会没事。我一直让自己想白天的工作,想美术馆剩下的一堆要处理的破事,想远在加拿大的母亲,想睡在楼下的安先生。没用,依旧浑身疼痛和无力,最后我想抽烟,可是我已经戒烟很久了。
我在心里挣扎了很久,还是决定给Herbert医生打电话,他知道是我的来电,会二十四小时紧急待命。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但是我能听到他在那边放我治疗时常听的安眠曲。医生说,这有助于我静心,然后你只要安心睡下,一切都会像这首曲子一样,在海角对岸春暖花开。
我突然想起那次我去他家里拜访他,Herbert医生见到我十分惊讶,他说,他先前几乎已经确定我不会再去找他。
我告诉他,除了他以外,其他任何医生我都不放心。医生的回答也很直白,他说像我这样年轻有名又有钱的姑娘,对别人戒备心重也是很常见。我不在乎他对我的讽刺,只是看着他笑了一下。他说的一半以上都是实话,我没有什么好否认的。
至于为什么可以信任他呢?我记得我当时说的是:“我是你从现在开始的第一个病人,你需要钱而我可以给你想要的金额。”
Herbert不理会,他只是坚定地看着我:“Sunny,你年轻,还有才华,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等着你去做,就算没有我,你也一定会克服这个病好起来的。”
但他不知道,像他说的那样,我不怕疾病,灾难,和苦痛,可是我怕我自己被我自己打败。而如今听到手机那边音乐声却后悔了,当初,不应该在他面前把话说的那么难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