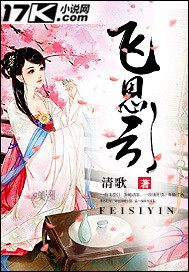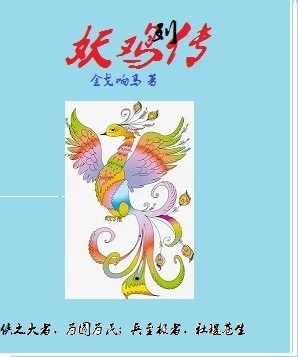第七章 白头吟
皑如天上雪,皎若云中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日沟头水。
躞蹀御沟上,河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摆摆。
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卓文君 白头吟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散了早朝,我应约而来,却见胤祥早已等在御花园边的小石桥上了。他定睛看着我,眼里温柔无限,他仿佛真的看见了古曲中咏唱的女子,素色衣裙,幽立水边一般,脸上的笑意多了几分少有的爱慕。
微风拂过,湘帘轻摆,悠悠荡荡,我缓步而行,不敢发出太重的声响,叮咚叮咚,步摇作响,我的心情豁然开朗。绿草苍苍,白露茫茫。我似乎看见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他就在那等着我,“朔回从之,道阻且长,朔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我巧笑倩兮,微微一福,“十三阿哥吉祥。”
他本欲伸手拉我,去忽然看见有宫人从一旁经过,这才佯装正经的抬了抬手,“起来吧。”
“谢十三阿哥。”我低头窃笑,喜上眉梢。
待人走远了,他才缓缓地说,“我就说,你今日怎么那么老实,竟然毕恭毕敬的行起礼来了。”
“这好歹是在宫里,每时每刻都必须眼光六路耳听八方。”我朝他顽皮的吐了吐舌头,“今儿叫我来何时?”
“给你找了些东西来。”他从身后取出一个包袱递给我。
我一看,原来是给我送书来了。“这么好,给我送熟书。”
“你不是说没事要多读书吗?”他背过身去,“这些书你多看看,都是说诗词的,你应该喜欢。”
我随手一翻,不由的皱起眉头来,“为什么是朱熹注的《诗经》?!”
“怎么?”他奇怪的看着我,“你不是喜欢诗经吗?”
“可是本姑娘最讨厌的就是朱熹。”我忍不住白了他一眼。
“此话怎讲?!”
“好比刚刚咱们年的那首《在水一方》,以你看若放在古人身上,最适合的是谁的故事?”我反问。
“且听姑娘赐教。”他躬身一拜,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依我看,这个故事更像是在诉说初见卓文君的司马相如的心声。”我一手捏着书,一手负在身后,摆出一副老学究的架势。“司马相如的才名远播天下,梁王亲赠绿绮琴,这足可以使天下人为之倾倒。可司马相如真的在乎这些吗?那时候他只在乎湘帘后面的那个人。虽然卓文君将自己藏在了帘子后面,可司马相如仍然窥见,伊人眉似远山,面若芙蓉,远近重叠,像足了一副蜀山蜀水间的一池芙蕖。”
“你这解释倒是新鲜,那么你再说说诗经开篇《关雎》又作何解?”他剑眉一挑,似笑非笑的看着我问。
我转身背向他,“这个嘛,我就更不同意朱夫子说讲了。为了杜绝早恋,非要硬说《关雎》实在歌颂后妃之德,简直扯淡。”
他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些话是谁教的?若让南书房那些个老学究们听见,非要气的当场吐血不可。”
“难道不是吗?”我不屑地说,“朱熹这个人甚是讨厌,不仅阻碍文化自由,还曲解孔子的思想,真不知道坑了中华历史多少年。尤其是到了明朝,一帮文人,瞎起哄,什么叫男女有别,男女大防......虽然男女是有不同,但是也不是他说的那样不堪吧。总之朱熹这个人在我看来,完全就是妄人。”
“你这思想也算是离经叛道了。”他严肃的说着,没了刚刚的喜笑颜开,“这些话断然不是令尊和先生所教,真不知道你是打哪学来的。”
他虽说不上生气,可也并没有接受我的想法,毕竟他是生活在三百年前的人,要他明白三百年后的男女平等,恋爱自由,还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我也觉得朱老夫子的有些理论并不完全正确,就好似之前你说碧珀的一席话,我就决定说的很好。她虽然流落风尘,可洁身自好,对人义薄云天,我们怎可因为她的出身就看轻呢?”他说。
“正所谓,佛曰:终身皆平等。”我笑着回答。
他点了点头,浅浅的笑这问我,“苏麻姑姑说,你认为明代第一散文是归有光的《项脊轩志》?”
我点了点头,“确实。”
他又问,“那么你认为宋代第一词又是哪首呢?”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我轻闭双目,深吸一口气,淡淡的念着这首早已烂熟于心的《江城子》。
“苏轼一向以豪放见称,却在掉忘词上独占鳌头。”
“苏轼一生为情所重,也自多情宽厚,有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快乐烦恼。小时候我总觉得人一辈子能被一个人爱着就是最幸福的,可后来才渐渐明白,多情总被无情恼。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守着,是因为心里留着她的位置,任凭谁也无法取代。爱就应该这般豁达,明亮,而后九曲回肠。”
听完,他笑了,那种蔓延到眼底的笑,带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似乎那一刻他明白了,他的心意我能懂。
“璎儿,下一次我们一起去看天之涯可好?”
“好。”
#####################
Ps:今日小发糖,大家感觉如何?!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