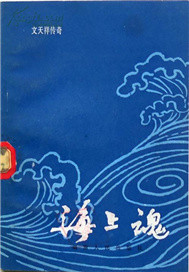古珉罗在江府住了十多日,江秦算是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单从言行举止来看,江秦对他算是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
加之派去安阳郡打探古珉罗身世的人已经回来了,与古珉罗说的并无多大差别,江秦心中的疑虑更是消除了不少。当然,江秦无论如何也不会知道古珉罗还有飞彻崖少主这一身份。
十多日后,在一个清爽的早晨,两人骑着烈马,最终离去了。江秦泪眼朦胧相送,纵有诸多不舍,也无可奈何。
江秦知道这只是权宜之计,但终究有太多的担忧,江湖艰险,而前路又茫茫,想必这一去,风餐露宿,自己的宝贝女儿定是会吃不少的苦头。
不过对于江听雪来说,虽然对自己的父亲有些不舍,但也是满心的激动与欣喜,这也算是完成了自己一个闯荡江湖的梦。
古珉罗告诉过江听雪,这一路东去,他们将缓慢而行,两人将去游览名山大川,领略各地风土人情。虽有些担忧这一路上会遇到仇家追杀,但为了尽量满足江听雪心中的愿望,古珉罗愿意冒险。到时如若危急真的来临,他就算是拼尽全力,也定会护自己心爱之人周全。
江听雪走后,延陵枧又去钱庄寻了她好几次,结果从伙计口中得到了相同的答案,说他们小姐早已离去,而他也看到钱庄的管事已换了人,不再是江听雪。
但他依旧不相信江听雪离去的事实,以为是江听雪故意躲在府中不出来,为了避开他。为此,他特意去了江府,不过依旧没能如愿跨过江府的大门,被守门的奴仆拦了下来。
江叔被惊动出府,看到来人,自然是没有好脸色给他,只简短的回了句:“小姐离去了。”抬手便吩咐奴仆轰人。
延陵枧自然是不信,拦住了江叔的去路,瞧着江叔的神情变化,口气带着试探:“还请告知,听雪她究竟去了何处?”
“一路向北而行,游历去了。”江叔眉头深蹙,话里不含一丝温度。他是厌恶极了这人,如若不是这泼皮日日纠缠,他家小姐又怎会远去,从此过上漂泊的生活,在炎炎夏日里经受风吹日晒之苦。
延陵枧观其对方神色变化,倒不像是在说谎,于是也不再追问,自顾自转身,大摇大摆地走了。
穿行在熙熙攘攘的街上,他心中在暗暗思忖,准备派几人去江府附近暗中观察打探,看那个管家是否在欺瞒于他。如若江听雪真的离开了钱塘,那么他也要清楚她的去向。他想,如若没了江听雪,他待在这钱塘还有何意。
几天后,延陵枧从派去打探的人口中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江听雪是真的离去了,并且有一男子同行,那日有很多人看到两人骑马出了北门。
当然,走北门是江听雪与古珉罗故意为之,待出了北门,他们实则是在向东走,而非向北。两人早已料到,延陵枧不会死心,一定会派人打探她的去向,因此故意留了一手,误导延陵枧。
延陵枧听说江听雪是同一名男子一起离去的,瞬间不淡定了。最终又经过城守府的人一番打探,知道了江听雪有个表哥是中原国人,住在徽州。他将这与江听雪北上联系到了一起,很快便断定江听雪定是去了徽州。
延陵枧可不想便宜了姓古的那男子,凭他多年的经验,一看就知那男子对江听雪的动机不良,于是很果断地做出了决定,要赶去徽州。
临走时,延陵枧不忘自己那个还在受牢狱之苦的侍从,带着一些好酒好菜去见了那人一面,两人聊了很多,可谓是主仆情深,侍从多次提醒延陵枧路途上要多保重,并为不能再护延陵枧的安危而感到愧疚。
半夜的辗转反侧,不是思念,而是焦灼,担忧古珉罗近水楼台先得月。竖日清晨,延陵枧与元文陵匆匆辞别后,带着两个元文陵派出的护卫终是踏上了行程。
能送走那尊大佛,元文陵是求之不得的事。延陵枧足足在他府上待了两个多月,这段时日可没少给延陵枧收拾烂摊子。
而这个时候,陆景行与凌潺已回到陆府好几日了。如今江湖动乱已定,恢复太平,当初被召回府的陆府门人在陆景行归来后也相继离去了,去往原来的居所,偌大的陆府又恢复了以往的冷清安宁。于此同时,被派去寻找陆景行他们的门人也接到了陆府发出的消息,此时陆辞正在往回赶。
凌潺着一身紫色衣裙,坐于膳房外的廊下执卷而读。清风徐徐扫来,额前发丝轻轻颤动,面容依旧略显憔悴,毫无气色。
此次本就伤势过重,又无法及时进行医治,加上路途上的颠簸,还未到府时,她便彻底病倒在了马车里。回来后,调养了五六日才有所好转。如今剑伤虽都已开始愈合,结了痂,但身体内在的伤痛还需慢慢调养。那一夜的淋雨,终究对她的身体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一时难以恢复。
膳房内偶有丝丝缕缕的轻烟从门口飘出,陆景行正独自在里面忙碌,一面在灶台后举炊生火,一面注意着药炉上的动静。这几日见凌潺胃口不好,他便想为她亲自做一碗葱花面。为此,还特意赶走了愉娘她们,命她们晚点再过来准备晚膳。
凌潺望了一眼廊外的午后阳光,搁下了手里已读完的书简。身子依旧有些虚乏无力,她将手肘放在了雕栏上,撑着脑袋,浅浅闭上了双眸。
这几个月来,两人难得有这样清闲的时光,不被外界事物所扰,没有烦忧。凌潺本想进膳房为陆景行打下手,结果刚进去,便被他赶了出来。她想守在他身边,可一时又无事可做,便叫雀儿拿了一卷书简来。如今书简读完,她的药也被他熬得差不多了,浓浓的药草味在空气中四处弥散。
凌潺浅寐了片刻,一道清润的声音裹在袅袅轻烟中自膳房内飘来,在她耳边响起:“小潺,药好了,待会儿进来喝。”
碎发飘动,凌潺从浅梦中醒来,看着廊檐投下的影,眸子逐渐清明,对着门口答了一声:“知道了。”
凌潺望着地面上的阴影发了片刻的愣,然后起身去了膳房门口。
碎步跨进屋子,打眼便见灶台前那颀长的身影正高挽着衣袖,手拿擀面杖在摆弄一张雪白的薄面饼,锅里的水已半开,雾气袅袅。在他身后不远处的桌上,小半碗棕褐色的汤药还在冒着热气,一缕缕在空气中消散,药草味弥漫。
凌潺看到这样宁静而温馨的场景,心里不由得一暖。这是他第二次特意下厨为她做面吃了,这么多年来恐怕还未曾有人特意为了她而做某件事。
陆景行听见轻缓的脚步声,很自然地扭头望去,逆着光,门口那抹紫色的纤影正在愣愣出神,眸子中带着微不可察的光。他狐疑地勾了勾唇角:“怎么了。”
“没事。只是想到一个问题。”凌潺摇摇头,双臂自然垂放,抬步走了过去。
陆景行心生好奇,顿了顿手上的动作,望着离自己渐进的人,挑眉问道:“是何问题?说来听听。”
“你这样惯着我,我怕有一天,我会恃宠而骄。”凌潺微微仰头看他,话音低浅,神情却是认真的。
陆景行听了这话,温和的笑意很快便从唇齿旁爬上了眼角眉梢。他以为是何等重要的问题,竟能使她走了神,却不曾想,竟是如此。
笑容敛去,他轻轻蹙眉,故作沉思状:“嗯……,这是一个问题,该如何是好呢?如若真有那么一天,到时我弥补错误便是了,小潺完全不必担心。”
凌潺知道他是故意如此打趣她,于是微微嗔他一眼,不再接话,转身走向了灶台后,向火势渐弱的灶膛内添了一些柴火。而站在另一面的人又埋下了头,忙碌着手里的活计,最后将大薄饼切成了条,悉数撒进了开水翻滚的锅中。
褐色的汤药已温,凌潺侧站在桌前小心翼翼地从陆景行手中接过了它,很干脆地仰头一饮而尽,随即微微蹙起了眉头:“好苦。”
“这样可好些?”说着,陆景行便低头吻去了她薄唇上的药迹。
这一刻,凌潺双眸有些发直,待回过神时,主动权已牢牢掌握在了他手中,而她竟在不由自主做着回应。这人总是在趁她不备之时做出些令她出乎意料之事来,而她又拿他无计可施。
灶膛内噼里啪啦的柴火燃烧声彻底将凌潺拉回了现实,她轻轻推开了他,两颊发烫,放下手里的碗,用眼神指了指灶膛处:“看着点火,可别让我们两人将厨房给烧了。”
“怎会。”陆景行简单两个字,瞧着她那悄然泛起了两抹红晕的面颊,嘴角的笑意分外深浓。
锅内已有淡淡的面条清香飘出,凌潺不再理他,转身向灶膛口走去了,害怕灶火不去看管,真发生什么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