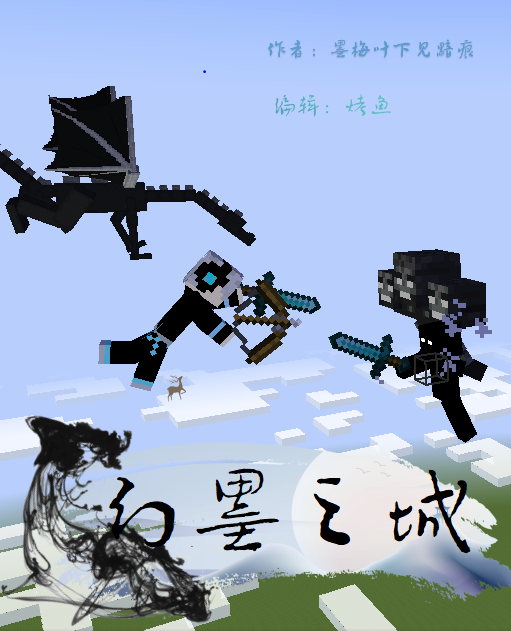我花了三天的时间将我三层楼的全景“小别墅”参观了一圈,的确是清幽雅静,富丽堂皇,骄奢……额,说过了。当初意兴阑珊的追问慕天安这间阁子用处的景象还历历在目,如今时过境迁,也依然物是人非。
我们都活在谎言中。
别人说的话我们都听了,都信了,虽然知道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我们总是在梦想中将自己放的很高,想的太好。最后,却因为爬的抬高,摔得太重,太恍然大悟,自己其实一文不值。
不骄不躁,四字而已,做起来却是何其的苦难。
我的目标?很不明确,好像也不需要我来创业。我连最基本的自由与生活保障都得不到,创业于我无稽之谈。我构想出的虚幻世界,不过是为了麻痹自己减少痛苦。逼迫着自己在现实的情况下变得愈加的麻木,愈加的看不清楚现实。
钟力很守约每天都会按时到我这里,心不甘情不愿不良情绪颇重的陪着我练一些奇奇怪怪的曲子。我记得我们两人的上一轮合作,还是在一次堪比“国宴”的大场合上边,没有想到再一次合作,就走进了娱乐场所,环境真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啊。我选了又选,想了又想,最后还是将曲子定给了《蝴蝶》。那一刻,钟力终于有一种想要杀了我的冲动,按照他的话说,反正最后我也会被我自己给害死,他还不如趁早给我一个痛快。
“你,去给我安排,我这次要从后台飞出来,白衣飘飘仙子下凡不染凡尘。”
我斜躺在美人靠上,有气无力的指着钟力吩咐道。
“姑娘,公子每一次来的时候千妈妈都是小心的担待伺候着。可是小蒙觉得,公子好像总是对姑娘您有所顾忌,言听计从似的呢?”
小蒙看着钟力无奈无辜又无助挣扎着走出去的背影,问出了她深埋心中已久的问题。小丫头片子,眼力不错,终于看出了本姑娘我来头不简单了吧。可是丫头,你可知道他钟力说的没错,要是再让本姑娘这么无法无天的嚣张下去的话,钟大人也帮我顶不了多少时日了。总有一天,他也保护不了我,到时候,你的姑娘说不准会比现在的暮雨混的更加糟糕。
我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呢?
这貌似又牵扯到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了。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我是谁?!我究竟想要什么,我不是林韶言,我还是吗?念安,一个青楼的姑娘而已,我还应该如过去一般潇洒自如的生活不管不顾吗?又或者说,我不应该再这么任性嚣张了呢。
生活时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什么,什么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谁,就会被谁伤害得最深。所以,做事不必太期待,坚持不必太执着;要学会放下,放下不切实际的期待,放下没有结果的执着。所以,凡事要看淡一些,看开一些,看透一些,什么都在失去,什么都留不住,唯有当下的快乐与幸福。
火辣辣的太阳射的我睁不开眼睛,我抬起头来看了看头顶上金灿灿的太阳。有些倦意,阁底流动的水竟然清澈如斯,在太阳的照射下波光粼粼,洒下了一片金子。
小蒙给我端来一杯温开的茶水:“姑娘,外边太阳大了,进去休息吧,今夜还要上台表演呢。”
我懒洋洋的点了点头,却没有任何想动唤的意思,只是将整个人都蜷缩在了窄窄的美人靠上。虽然艳阳高照,依旧有清风拂面。我闭上眼睛,静静的享受着这一刻的宁静。
慕天南,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呢,难道我,今晚果真要上台吗?小蒙说了一些话便退下了,她很乖,从来不会打扰我发呆。
有些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有些失心疯,神经质。对生命的宣泄,在我强颜欢笑的伪装下很少有人能够识破——也未必,他人真的没有那么的在意你。
我看了看这栋楼的高度,不到十米几乎与水同一个深度,一百米外便是绿柳如茵的岸边。这么好的天气,姑娘们大多都躲在自己的阁子中困觉,整间烟雨阁人烟稀少静的出奇。
我再一次的看了看天,我明白,自己又要做疯事了。
扶着柱子站了起来,有些腿软。刚才的坚定也瞬间消减去了大半,正在有一自己该不该跳,便听到底楼正准备从船上上楼的千妈妈惊呼声。我循声望去,小蒙愣了一瞬立马往楼上冲,千妈妈被我吓的腿软,一个劲儿的高喊着让我站在那里别动他们马上上来救我。
我看着他们所有人的表情,觉得很可笑。这一刻,竟然有了遗世独立迎风凌乱的感觉,早已经忘却了刚才一瞬闪过的胆怯。闭上了眼睛,张开双臂,仰头对着天空高呼:“慕天安。”
“咚!”伴随着一声沉闷的重物落水的响声和高高溅起的水花,我感受到身体瞬间下沉,呼吸好像也变的艰难了。我睁开眼睛,看见千妈妈招呼跟着她的那个小厮下来救我,光的折射使得她看起来更加的短,也更加的胖。小厮不会游泳,站在岸上腿软;小蒙晚了一步没有抓住我,却紧跟着我也跳了下来。
我赶紧的使足了吃奶的劲头拼了全力往岸边游去,小蒙在后边紧紧的追着。我们两个人竟然像两个可笑的小丑,一前一后疯狂的往岸边游着。瘫了那么久,我也不知道自己这一刻究竟是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竟然一口气便游到了百米外的岸边。当我心满意足的看着被我远远甩下的小蒙,扔掉自己湿漉漉又很重的外衣,撒丫子乱跑。千妈妈在对岸急的跳脚,一脚狠狠的踹在了小厮的腿上,两人划着穿往岸边驶来。
“小蒙,快点儿啊,要是跟丢了我,钟力会怪罪你的。”我不清楚小蒙是谁的人,我甚至不想去深究她是谁的人。她的确有可能只是如她所说,一个平凡的丫头。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因为我想这么说而已。
我边跑边朝着小蒙大叫着,笑的肆无忌惮。这是我这么久以来笑的最欢快的一次, 人为什么总是要压抑自己,来想究竟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人为什么凭感动生死相许,有时候我想的很多,想的太多。想到最后,竟然有一种超脱,一种我成为禅的时候。什么都已经不想要,不重要,一切皆可抛。
在不断的进化中,我们学会并掌握了压抑自己的天性。人生,不只是眼前,人生还有诗和远方。这句话说的多好啊,我们总是被眼前的小事牵绊出了前进的步伐。我们总是嫌弃自己活得太痛苦,因为我们想的太多,想得到的太多,什么都不愿意放弃,倒也不尽然都是朝三暮四,只不过,一个也不愿意放弃罢了。
我不是林韶言,我也不是念安,我就是我。我不想被人捆住了人,还要捆住心。现在,我要去找暮雨。
“暮雨住在哪儿,不告诉我就把你扔下去。”
被我随手抓住的一个小丫头惊慌失措的看着我,显然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看着河中央的千妈妈,刚刚上岸追着我跑的小蒙和只着了一件湿透了的中衣的我。“哇”的一声吓哭了,手颤颤巍巍的指着一个方向,我抱着她亲了一口,随即还是把她给扔下了水,朝着小径深处跑去。
一路上,我见着人便会抓住问,问完之后就……当做障碍物扔在地上。其中还不乏几个颇有姿色的姑娘睡眼惺忪的对我粗暴的行为骂骂咧咧的,当然最后也被我给踹了一脚扔在了路中央。
“你……小姐怎么会在这里?”
暮雨穿着一套粉红色的纱衣,看上去跟没穿似的。被一个看起来五十多岁的满脸横肉的男子搂着腰走了出来。她一脸震惊的看着我,从一间极不起眼的单层小房间中走了出来。这是她的房间?我还以为是哪家姑娘的侧房呢。
那个男人看见我后,半眯着的眼睛立马绿了起来,甩掉了暮雨便向我走来。我很囧的看了看自己轮廓毕现的身体,再抬头时大叔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
“姑娘是哪家阁子里啊,这么迫不及待的大中午得就到处找爷呢。哟啧啧,爷怎么没见过你呢,生面孔啊生面孔,新来的吧。”
暮雨一步并作两步的冲了上来,挡在了我前面,软言细语的哄着大叔。
“王员外,是暮雨没有把您服侍好吗?怎的这般见异思迁,看见漂亮的年轻姑娘就把暮雨给忘了呢?”
谁知大叔不耐烦的一巴掌甩在了暮雨的脸上,暮雨被打到在地,捂着脸急切的看着我。大叔猥琐的看着我笑了笑,再义正言辞的居高临下的指着暮雨呵斥道:“滚,你这个贱人,你算哪根葱啊?!爷玩你,那是看得起你,你以为你还是过去那一夜千金的京城头牌吗?爷还就告诉你,你他丫的现在算个屁啊,连个进城卖菜的都能要的起你。”
我看着这戏剧化的一幕,不敢猜想过去半年中暮雨究竟过的是怎样同过去天差地别的生活。
大叔说着便又向我走来,暮雨从地上一跃抱住大叔的腿,大叔不耐烦的用脚踹她。
“小姐您快走,快走啊。”
周围阁子中午睡的姑娘都被惊醒,站在自家阁楼中,欣赏着过去在她们眼中不可一世的暮雨任人凌辱。
我才如梦惊醒般的条件反射对着大叔的宝贝狠踹了一脚,大叔一下被踢得弯下了腰。四下看了看,从旁边拾起一块平平展展的石头,照着大叔的头便呼了过去。
大叔捂住血流如注的头,抓住我的手,嘴里骂着,不让我走。
见血之后本来很慌乱的我却在他抓住我手的那一刻镇静了下来,淡定的看着他语气危险的威胁道:“给老娘松手,否则今天让你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直接老婆孩子准备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