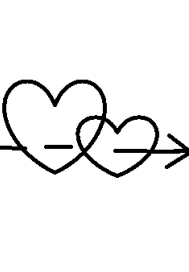此时已经日上三竿。
钱进喊了声“花姐”,没人答应,便披了件衣服起床。昨夜他劳累过度,起得有些晚了。而蚕娘是个勤快人,往常这个点她早已起床忙活去了。
他走到桌旁倒了碗水喝,却一眼瞥见桌上有张字条,旁边还有个香囊。那张纸条上用略显稚嫩但很工整的笔迹写着:
老爷,家中的银两都锁在柜子里,我拿了二百两。那些衣服图样我也抄了份。老爷,恕我不辞而别,勿念。
钱进笑了笑,心说花姐也开始调皮了,一大早便跟他开这种玩笑。他走到院子里连声喊道:“花姐,花姐。”
没人答应。
金台明从屋里出来,疑惑的说道:“花姑娘不是一大早去花间坊里去了吗?”
钱进预感到不妙,急步跑到花间坊,却没发现蚕娘的影子。老范见东家上门,连忙出来招呼,却只来得及看到钱进疾奔的背影。
回到四合院,钱进直接冲进金台明的房间,扣住他的手臂厉声问道:“金台明,你是不是教过花姐写字?”
金台明自认识钱进后,从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气。他拼命想挣脱,奈何力气大不过钱进,情急之中叫到:“是我教的又如何?”
钱进听了这话,整个人便如瘫软了一般。半响之后,他神色萎靡的问道:“教了多久了?”
“我教李良兄妹俩的时候,花姑娘是经常在旁边观看的。有时候她也会问我一些不认识的字。”金台明揉了揉被扯得发疼的手臂,疑惑的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花姐走了……”
“走了,去了哪里?”
“我也不知道。”
金台明思忖片刻,又问道:“最近可曾发现花姑娘有些异样?”
钱进不答话,一个人颓然的回到蚕娘的房间。桌子上,那只红绿相间的香囊正散发着淡淡的香味。他小心打开,里面是两缕缠在一起的头发。
刚来京城没多久时,钱进曾经向蚕娘表露心意要娶她,结果蚕娘声泪俱下,说不想因为自己寡妇的身份而坏了他的前程。事后,蚕娘剪了钱进一缕头发,说以青丝结来全了与自己的情分。
后来,蚕娘虽然开朗了许多,可在她的心里始终横着一座大山,那就是世俗。这个世间的女子若做了寡妇再嫁,是要受千夫所指的。蚕娘虽然当了花间坊的掌柜,可是这观念岂是一时半会就能转变得了的?
自打上次蚕娘听得老钱他们要来京城后,便经常有些神不守舍。钱进也没多留心,以为她是快要见公婆了有些羞怯。其实,蚕娘一直是在意自己的寡妇身份的,她不想自家老爷被人背后指指点点。
可是,她一个弱女子又能去到哪里?
想到这里,钱进冲到后院牵了匹马,也不上马鞍,开了后门便直接骑马冲出去了。二丫走后,钱进买了几匹马,平时给酒坊运送货物。
此时还不到巳时,想来蚕娘一个女人家是走不快的,若是快马加鞭的话兴许还能赶上。
到城门口的时候,钱进不顾守卫高声阻拦,直接策马出了永定门,沿着官道一路向南追去。
一个时辰后,钱进站在一座高岗上。
望着那条一路南下的官道,他喃喃的说道:“花姐,你怎么就这么傻呢?”
此时,一辆马车缓缓行驶在一条南下的小道上。
马车里面坐的是两名清丽女子。其中一名正是钱进苦苦追赶的蚕娘,另一名却是弘远镖局的云三娘。她们二人特意选了走小道,怕的就是钱进追过来。若说这其中因果,倒也不甚复杂。
原来,蚕娘之前听得钱进雇了镖局的人去接父母来京,便依样学样。昨天,她一个人悄悄的去了一趟弘远镖局,托镖局的人护送自己一趟。此时,云老爷子南下尚未归来,镖局大小事务都是云三娘拿主意。
云三娘之前在四合院曾经见过蚕娘,加上被钱进拒婚,便对蚕娘有些冷言冷语。待听得蚕娘要离开京城时,她奇道:“怎么突然要离开?是那个负心汉要你走的?”
蚕娘无法,只得将原委一一说了出来。
云三娘听罢,叹道:“也是个苦命人。罢了,老爷子估摸着也快回来了,我也正好出去走走。”
蚕娘自然是连声道谢。
云三娘又问道:“姐姐既然要我送你一趟,可有想好的去处?”
蚕娘默然。桑木村如今已成了一片废墟,回娘家的话肯定要无故遭受许多冷眼。天大地大,她却成了无主浮萍。
云三娘见状,笑道:“姐姐以后可还想见那负心汉?”
蚕娘摇了摇头,含泪说道:“既然打定主意离开,日后自然是不见为好。”
“既如此,那便去个远点的地方吧。送你去观海城如何?”
“观海城不是老爷的故乡吗,日后岂不是要被发现?”蚕娘惊道。
“话可不能这么说,你难道没听说最危险的地方便最安全吗?”云三娘望着蚕娘的如花容颜,心中暗道:“那负心汉想必很着紧这位姑娘吧,我索性把她送到最南边,且让他多花些时间去找,这样就报了当日拒婚之仇。若是日后被钱进追问,我就以送蚕娘去了他老家为由推脱。”
两人商定好行程,便于次日一大早就约好在城门口相见,只待城门一开便出发前往观海城。
…………
钱进没有寻到蚕娘,整个人如霜打的茄子一般回了四合院。
望着那间熟悉的房间,他的心里感觉空了好大一块。床上的棉被,还留有蚕娘的体香。闭上眼睛,似乎蚕娘就在房间里面走动,耳边还不时响起她的笑声。
整整三天,钱进把自己一个人关在蚕娘的房间里面,一门不出,二门不迈。
众人都有些担忧,便跟金台明商量要他去劝一下。
金台明叹了口气,说道:“心伤要用心来医,给他些时间吧。”
正说话间,老曹进门说门口来了几个人,说是找钱老爷的。
金台明望着蚕娘那间紧闭的房间,摇了摇头,便随老曹到了门口。来人是弘远镖局的云老爷子,后头还跟着仨个人,年龄不等。
云老爷子率先开口说道:“这位先生,钱侍讲可否在家中?”
“在是在家,不过见客怕是有些不方便啊。”金台明面有难色的说道。
旁边一中年汉子站出来说道:“我进去瞧瞧,自己的娃当了状元也不能不认爹啊。”说话的正是老钱。
钱进北上后,老钱一直带着文氏和宝儿住在文天正家。文氏舍不得离开老父,便一直住到了五月。恰好云老爷子快马来报,说钱进高中状元,一家人自然是欢天喜地。略微修整一番,他们便直接随云老爷子坐船沿着大运河北上。到京城花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
金台明一听这话,连忙喜道:“原来是世伯来了,这下老弟有救了。”于是他把钱进这几天茶饭不思的事简短的说了下。
旁边宝儿听了,恨恨的说道:“果然不出艾米莉所料,哥哥在京城有了相好的。”
老钱听了一脸黑线,便示意金台明领着大伙先进屋安顿,他自己便去敲门。
“儿子,你爹来了。”
几息之后,门开了。从屋里头走出来一人,满脸胡子,眼眶发黑,只听他声音有些嘶哑的喊道:“爹,你来了。母亲和宝儿也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