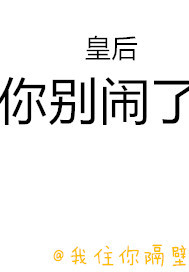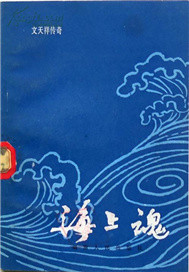我冲他摇了摇头,让他不要为了我而格外提出要求,反正全身已然湿透,也并不在乎这一会儿。
我抹了一把脸颊,见到手上沾染上上妆的颜色,心知定然是妆花了。
“你!还杵在这作甚?轿子都已走了。”掌事公公走过来,我忙低下头称是。
“等等!”他叫住我,我心头一颤,回过了身。
“你的脸怎么了?”他站在我面前沉声问,我缓缓抬头,脸上是一层刚抹的泥:“公公恕罪,奴婢方才不小心沾了泥水。”
“回去赶紧清洗干净,主子见着了像什么样子!”他呵斥说。我点了点头,心稳了半分。
终于回到玉澜堂,我已全然成了水人,衣襟止不住的滴着水脚底带出了一片水渍,见到我糊了一层泥的脸他愣了一会儿。
然而我却只担心面容会显现,赶忙去寻镜子:“皇上,应当从我的脸上看不出什么来吧?若是被发现可就糟了!”
“赶紧去换身衣服,淋了这许久,若不然会入寒气。”他疼惜的对我说,我却毫不在意的笑着:“您不必这么紧张,我没事。”
见到他已蹙眉不悦,我笑说:“好,奴婢这便听从您的指示去换总行了吧。”
看着热气升腾,茶香味随着第二遍温热的开水缓缓浸透出来,然而我却觉鼻子有些不畅,昨日祭天过后今日雨还是照常下着。
我端起盘子,想起从前我力所能及之事便是为他泡一杯茶;那时他无论是在变法期间有多忙都会很给我面子的品上一口夸赞几句,纵然味道兴许及不上那泡茶宫女的一半。
想着,心头便缭绕起淡淡的温暖来,虽然现在再为他泡茶,他的身旁有时会多出来另一个人。
“你送的这本书当真好!朕喜欢极了,在这上头不单将贵族阶级的衰落和资产阶级是如何渐渐占据社会地位给写出来,甚至还提供了法国社会各个领域丰富的生活细节和历史材料。”我听到皇上兴致勃勃的声音。
“就知道您定会满意这本书,书的价值就在于得到它的人能懂它,皇上向来非浅显之人,奴才为这本书倍感荣幸。”德龄莞尔,抬眼看了看窗外。
“不过,听说皇上近日去祭天了,这雨当真下个不停,不知何时才休止呢!”
“这也是朕担心之处,想起杜子美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何尝不是连连大雨之后身在苦难中的黎民百姓的真实写照。”提起几日未曾休止的雨他面露愁思:“其实,有时候,我这个君主当真无能为力,只能做些微薄之事;如果可以,我愿意牺牲一切救他们于水火,只是都是徒劳无功罢了。”
德龄扭头望着壮志难酬却为民真切忧心的他,目光中的那丝倾心不经意间便流露了出来。
我便在此刻忍不住轻咳,打破了空气里头那丝怪异的气氛;德龄这才回过神来,起身向皇上告辞。
“皇上,看样子,您马上便要俘获一颗心。”待她离开后,我半开玩笑的冲他咧嘴一笑,他莫名其妙的望着我。
“您该不会全然不觉吧?德龄望着您的目光,可跟跌进了水里头似的,拔都拔不出来。”
“胡说!”他抿着薄唇,全然不相信。
我摇摇头,果真男性对于感情上实在慢一拍;不过心里头也有些暗喜,这也证明他对德龄从未往它处多想,抵不过便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罢了。
晨露滴落在窗外的树叶上,接连下了十日的雨终于停了下来,初升的阳光照出点点莹光,空气中一片潮湿的泥土味。
然而我却觉头越发沉重,心知不妙,原以为那日入的一点风寒过两日便自然好了,然而却越来越严重。 鼻子虽痒却只能憋着不敢打喷嚏,若被其它太监发现我恐怕得被勒令“休假”,我也不想让他平添担心。
“你怎么瞧着脸色不好?”心细的皇上还是觉出了不对劲来。
“无事,可能这几日没有歇息好吧。”我笑说,转而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对了,当初我教您的那段梦中的婚礼可还记得?”
“梦中的婚礼?”他面露诧异之色,我这才想起当初并未告诉过他那首钢琴曲的名字,瞬间有些尴尬的咧嘴一笑,拉着他到钢琴旁:“您再弹一遍好吗?过了这许久,我这个师傅也该检查徒弟是否将旋律全都给忘了。”
他笑了笑,将纤长的十指放在黑白琴键上,凭借着记忆,那段刚开始还有些磕磕绊绊的旋律又流畅了起来。
我静静的望着他的身影,听着这段乐声轻快却又纠缠着淡淡的心碎,仿佛是泡沫筑成的完美幻境,就连消失成碎片之时都那么五彩斑斓。让我甚至开始有一瞬间怀疑,眼前重拾的美好是否也只不过是一场幻境,我摇摇头驱除了这莫名其妙的想法。
“皇上,其实这个旋律里头有个美好的故事我还未说。”
当落下最后一个音符后,我第一次将这个心碎而又美丽的故事告诉他。
“……那个平凡的男子再次见到他暗恋着的公主时,她恰好要嫁给王子,他原本打算将对她的爱意永远埋藏于心默默祝福;然而却见到人群中对着公主的那支利箭,他义无反顾的冲过去为她挡住……”
“被献血浸染的他睁开眼,恍惚见到她披着婚纱,含笑望着他。在他们身旁,天使正为他们唱着祝福的歌。他不敢相信的问这是梦吗?然后紧紧握住她的手说……有梦,就够了。”轻声说完最后这句,我的眼眶却已渐红,一缕清泪坠落在黑白琴键上,滑下一道痕。
他用温热的手为我抹去泪水,声音有一丝暗哑:“他是幸福的,至少,在他心爱之人将要身亡之时他还能够有机会冲过去救她。”
“皇上……”我哽咽住,他紧紧抱住我,然而却发觉我身子滚烫;蹙眉用手探了探我的额头,顿时心急如焚:“这么烫,你病了为何不告诉朕?我立刻去宣太医!”
我虚弱一笑:“宣太医?您忘了,我现在是芸初,不是珍妃,宫女……不得寻医问药,更不必提太医了。”
他闻言更是满眼焦灼,我支撑着说:“没关系,过几日便自个儿好了。”
“说什么胡话!朕不管,纵然是让太医为朕开风寒之药也得让他们来!”他失去往日的沉稳左右徘徊,我未来得及阻止,他便叫来了他还算信得过的孙太监,让他去请太医。
“皇上,您病了?”那小太监觉突然,忍不住小声问。
“少废话,速去请来。”皇上强硬的话语让他一愣,却还是应声去请。
“珍儿,不必担心,待会朕会和太医说是我入了风寒,命他们开药,你在这等着。”他明白我的担心,对我轻声说完便让我先去内室,以免被看出来。
我有些坐立不安,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到瓷碗在地上碎裂的声响,担忧的走到离御塌较近却又不显眼的一侧竖起耳朵听着。
“让你们开个治风寒之药,你们一个个的却在这和朕打着太极!这是多大的难事么!”皇上愤怒的声音传来。
“皇上,不是臣不肯为您开药,只是药不可乱开;方才为您把脉,您依旧还是气血不畅,肝胃需要调理,但并无风寒之状。 ”那名太医磕了一个头说。
我微微低下头来,见他为我如此,心头很不是滋味。
“你们……”他怒意难道,然而几名太医却都通通跪了下来。
我紧紧咬着唇,想要出去劝他,但是我知道那些太医光看我脸色就知我得了风寒,又无端见皇上闹着让他们开药,难免不起疑心。
我默默回到内室的床榻上,浑身无力的靠着边。又过了许久,我才见皇上进了内室,见他满面不快,我知那些太医定然无论如何都不肯无端开药。
“珍儿,对不起……”他在我身旁缓缓坐下,难掩自责:“朕那天就压根不该让你跟着去遭罪。”
我轻轻握住他的手说:“我方才见到了,您不遗余力让他们开药的模样。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毕竟未查出您有风寒却随意开了这药,他们不敢担这责。”
“您放心,现在的我上过刀山下过油锅,这么一点风寒算什么。”我忍住不适让自己挤出笑容来安慰心情低落的他。
然而,到了夜晚却越来越觉寒意顿生,皇上为我裹上了一层被子,我却还是止不住的开始哆嗦;他紧紧咬着唇出去又搬了褥子来一边问我还冷吗,他手忙脚乱的模样让我心头一动。
“您将自个儿的褥子都搬来了,晚上您可怎么办?”我咳了一声,笑说。
他隔着褥子,紧紧抱住了我:“这样,便不冷了吧。”
心头升腾的暖意驱赶了些许寒冷,他竟然维持着这个姿势直到天明。
我浑浑噩噩的醒来,不忍看他如此,便强烈申请回自己的居所歇息两日,他虽不放心,却又拗不过我。
外头的蝉鸣声一声比一声要响,躺了两日的我嗓子却如燃起了火将要冒烟那般,挣扎着起身倒了一杯水。心里告诫自己这并不算什么,当初独自在冷宫都挺了过来。
我灌了自己好几杯水,却听见外头响起了敲门声。
“芸初,皇上宣召你过去。”是一名宫女的声音,我心生疑惑,以皇上的性格定然会让我多歇息几日,怎会此刻让我过去当差?
拖着混沌的大脑迈入殿内,我见到只有他一人,似乎他又设法摈退了其它人。
“好些了吗?” 见到我来,他忙起身问。
我点了点头,他却端来了一碗药:“这个是治风寒的,快趁热喝下吧。”
我满面诧异:“太医……肯开药了?”
他点了点头,然而我却觉他的面色比之前更显苍白;他体贴入微的舀起一勺汤药来喂我,我依旧止不住心存疑惑的望着他。
“皇上,您是用什么法子竟能说动那些太医?”我还是忍不住问。
“朕的命令……他们不敢不听。”他沉声说,然而面容上却闪过一丝不自然。
我直勾勾的望着他,他却忽视我的目光,坚持将这碗汤药喂我喝完。准备差人将瓷碗撤下之时他背过身去仿佛是抑制不住的抵住唇咳了几声。
我皱着眉,忽然想透了什么,太医之所以能开药的前提只有可能是……他也得了风寒;心头一震,仿佛浑如一锅粥的脑子都瞬间清醒了过来。
“皇上!这是怎么一回事?您怎么也病了。”我起身拉住他的手臂:“您该不会为了我……故意让自己也染上了风寒?”
他在我的目光中沉默不语,我只觉心抽痛一下,抓着他的手臂更紧:“您当真傻!原本就身子不好,怎么能……”
“莫非,让朕看着你继续束手无策下去?”他痛心的望着我缓缓开口,漆黑如墨的眼眸里混杂着深深的自责和不愿往事重演他却总是无能为力的黯痛:“这虽是个愚笨的法子,但也……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