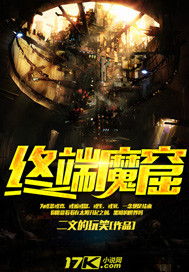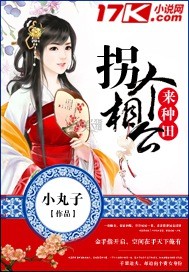前半夜还皓月当空,后半夜天空突然阴沉了下来,雨云从西向东慢慢汇聚,风虽然不猛烈,但在空旷之地也能刮起些许尘土。不久,漫天星辰连同明月被乌云吞噬,工地上一片漆黑。
朦朦胧胧中,工地后墙那道黑影再次现身,他似乎聪明了一些,先把梯子从围墙外边搬到里面,然后顺着梯子进到工地。
没有了月光帮助,那道黑影踉踉跄跄走了几步,差点摔倒,他退回墙根,摸索着向房子移动。很显然,他比上次准备的要充分,竟然带了手电筒。
黑影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竟打开了手电筒,黑夜中手电筒电光格外明亮,光亮后面的人影和黑夜融为了一体,勉强能看到轮廓。
他轻而易举就找到了狗舍,狗没有发出警报,而是摇着尾巴,上蹿下跳。他给狗投喂了一些食物后径直来到房前。
关掉手电筒,他和上次一样,先在每个窗前偷听一会,接着,继续搜索,犹如无人之境。他进到厨房,打开手电筒,寻找许久,并无所获,两手空空出了厨房,还不忘关上门,随后,他在房子周围转悠良久,回头又进到杂物间,打开了手电筒。
自从和二位临时负责人谈过话,左恩费一直心事重重,尽管所想之事匪夷所思,甚至可笑至极,但并不代表没有可能。
最少应该尝试一次,超出认知范围的事,要用超出范围的方法,排除一切可能,那个最不可能的就是答案,哪怕再怎么不可思议,都要接受。
半睡半醒之间,一道光闪过左恩费面门,他猛然惊醒,迅速坐了起来,窗外好像有亮光晃来晃去。他看了看熟睡的翟忠博,没有叫醒他。
左恩费悄悄起身,来到窗前,他透过窗户,看见了外面的人影,光亮正是从那人手中的手电筒发出。
那人在技术员的工棚外,东张西望,鬼鬼祟祟,仔细打量了一番,随即转身又在地面和周围扫视了一遍,然后扬长而去。
左恩费清清楚楚看见那人上了梯子,他骑在墙头搬梯子的时候手电筒咬在嘴里,到了墙外,手电筒依然开着。
确定那个人离开工地,左恩费才坐到床边琢磨,那个背影怎么那么熟悉,似曾相识,却实在想不起在那里见过。
这不是普通毛贼那么简单,小毛贼不会有这么大胆,更不会两次啥也不拿就走了,难道两次不是同一个人?狗没叫,难道狗被毒死了?也许是熟人,狗认识他,熟人的几率很大,即便被发现了也不会拿他怎么样,所以有恃无恐,那么他想找什么呢?此刻不能惊动任何人以免发生意外。
雨水悄然而至,天明时已经万物尽湿,工地根本没有排水设施,院子里面集了水坑,通往工地的道路有一段土路,每次下雨都会泥泞不堪。
厨子披上雨衣,卷起裤腿,推着自行车紧赶慢赶还是来迟了,厨子刚进工地,那条狗便大叫起来,除了狗,没有人责怪厨子,大家反而安慰他。
翟忠博告诉厨子,以后下雨不方便,就不用来了,大家随便做点饭就能对付。厨子是个负责任的好厨子,他说,既然接了活,就是下刀子都得来。
雨越下越大,两位临时负责人和厨子还有技术员玩起了扑克牌,左恩费则和翟忠博喝茶聊天,提起了工地闹贼的这档子事。
翟忠博惊讶道:什么!昨晚又来了?狗!狗,为什么没叫呢?
嗯!我也琢磨这个事,开始以为狗被毒哑了或被毒死了所以没叫,现在我觉得是熟人的几率很大,不但狗没叫,而且那个人的背影我好像在那里见过,可就是想不起来。
要么咱们报警吧!
左恩费道:我想过,这样太冒失,警察介入对咱们也不好,还有就是目前什么也没有丢失,我倒是有点担心。
翟忠博道:没有丢东西反而担心?
就是因为没有丢东西我才觉得蹊跷,那个贼到底是冲什么来的,才是我所担心的事,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翟忠博恍然大悟,道:嗯!我想起伍刚的话,他说自从科考队回来,一切就像是安排好了一样。开始并不觉得,伍刚提醒后我也感到奇怪,从第一次杨一浊邀请被拒绝后,我就失业了,你回来后,咱们就进了公司,一切都很顺利,干什么都没有人反对,包括到了这个地方,仔细想想就是怪怪的,很多事都不符合逻辑。贼!不会是有人指使吧!
放下茶杯,左恩费道: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咱们得尽快了,免得夜长梦多。我想尽快申请一些费用,去坐过山车,最少得试一试。至于闹贼这件事,先和伍刚商量一下最为稳妥。
好!不管怎样我都支持你。
话音刚落,翟中博和左恩费的传呼机同时响了,他们都用汉字显示机型,简单内容可以直接读取,不用回复电话。
消息应该是公司群发,大致内容,某某,某某,两位负责人星期一回公司报道。两位临时负责人所用是数字机型,不能直接看到内容,但不详的预感还是搅扰了牌局。
两位临时负责人唉声叹气,起身就去找翟中博和左左恩费确认消息。他们得到的答案和预想一模一样。留在此地,已无希望,幻想瞬间化为泡影。
见两位临时负责人面色难看,左恩费道:有一件事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帮忙?
什么事?能帮一定帮。
左恩费道:我和翟主管要做一个市场调研,规划一下接下来的工作,至于公司能不能同意还需你们二位帮帮忙。
嗯,是公司调研市场,还是你们调研市场?
翟忠博道:明确的说是我们。
哦,明白,明白,目前倒是有一个方案可以解决。
说说看。
这样啊!咱们工地距离村子较远,距离省道也不近,安装一部电话是势在必行,可是电话公司以没有线路为由拒绝安装,就是说距离太远需要几个电杆。
左恩费抬抬手道:继续讲。
后来,我和电话公司沟通过,装机组说装一部电话栽几个电杆不现实,非要装电话,电杆得自己想办法,栽电杆不是小事,占地,碍事,影响耕种,都是问题,但要解决也不是不可能,无非就是预算大点。我们两个在咱们公司说话根本不起作用,所以就没有管,装与不装也和我们关系不大,所以就搁置了。
哦,现在怎样可以装电话?
简单,你们写报告,该测量,测量,该协商,协商,电杆肯定要从耕地里面过,找村上谈好补偿,该签字的,签字画押,剩下交给我们就行了。
哦,还有一点,你们调研市场需要多少?
听临时负责人胸有成竹,左恩费也不再客气,伸出五个手指。
两位临时负责人相互点头道:问题不大。
下午,左恩费冒雨去了村里,他用村长家电话向公司说明了情况。翟忠博在办公房里面起草报告书。
工地上没有电话是实际情况,先前公司也考虑过,但工地方面没有提,公司也没太重视,一来二去这件事就被忽略了。说完安装电话的要求,他顺便提了一下工地排水还存在诸多问题。
村长是个聪明人,话里话外都能听出活又要来了,村长递上纸烟,左恩费以嗓子不舒服为由没有接。
什么时候栽电杆,往那里栽?村长急切问道。
喔,还说不定,公司还没同意,你先不要往外说,公司通过了我第一个通知你,放心,活还是你们干,到时候可能还要麻烦你协调一下。
好,好,没问题。
说完,左恩费便告辞要走,不巧,正好是晚饭时间,村长非留他吃饭,饭菜已经准备妥当,碗筷也摆放好。
既然如此招待,左恩费不好意思再推辞,否则真成了不知好歹,甚至有些看不起人的嫌疑。村长打开一瓶陈年老酒,片刻,房间内酒香四溢,村长道:酒不算高档但绝对是粮食酒,五十二度,最少放了十五年,仅此一瓶。
村长一脸真诚,左恩费道:既然是老酒,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酒量尚浅,雨天,路不好走,就少喝几杯。
倒满酒杯,村长道:喝多少,算多少,不必为难,喝不喝我都得让人送你回去。只要你常来,不怕你不喝酒,要是放过去我指定和你拜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