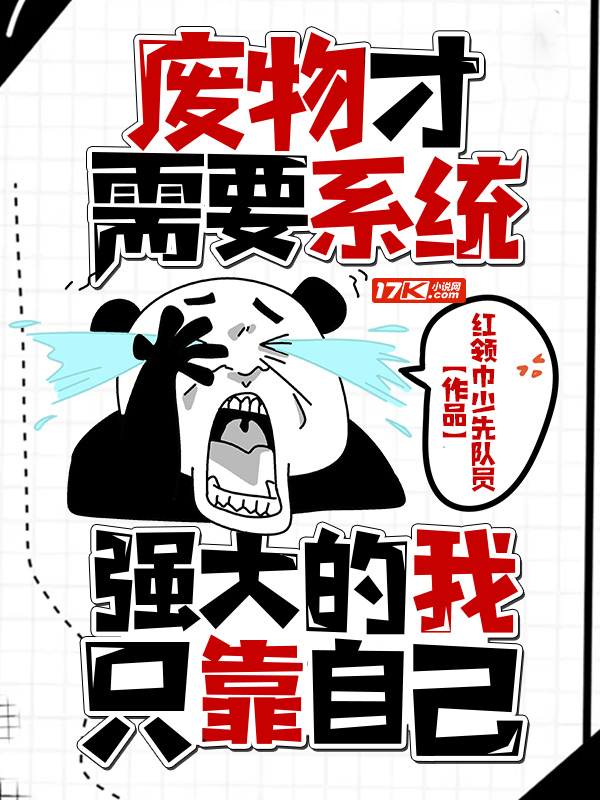林圆萍心里掀起滔天巨浪,却不动声色地问:“孩子,那你妈妈有没有保留什么特别的东西?”
“师祖,您说的特别的东西是什么?”
林圆萍笑了笑说:“比方说女人家佩戴的耳环、头饰之类的东西。”
雷雄见她连番发问,不像是普通的问候,心里疑窦丛生,摇了摇头,说:“师祖,怎么了?待我回去问问我妈妈吧!”
林圆萍双手连摆,说:“不必了,孩子,我只是想,你这么懂事,你的妈妈一定是个特别的女人。”
雷雄释怀,接连打起了几桶水,将木盆里装得满满的,依然捋起袖子。几个姑娘也都过来帮忙,不多时便把菜都洗完了。燕舞虽然心静,但向来就擅长厨艺,这一路从南到北,许多天都没有下过厨房,今天技痒,这些青菜萝卜到了她手里,变出了不少花样。摆在桌上,琳琅满目。加上经过霜打的蔬菜天然带着一种香甜,几个人尝了一下,都赞不绝口,似乎比鸡鸭鱼肉更为好吃。
午饭过后,日已西斜,天空渐渐阴暗下来,久晴的天气似乎是要下雨了。林圆萍说:“你们都早些回去,天下起鱼来,到时就不好走了。徒孙儿,小燕子,你们要好好的!”
燕舞点了点头,虽然百般不舍,但深知各人有自己的人生方式,也不能强求,心里遗憾,说:“姑婆,等找到姐姐后,我们一起来伺候你。”
雷雄说:“到时候,师祖您要跟我们一起下山,享受一下人间平凡的幸福。”
林圆萍说:“你们都去吧,我这辈子哪也不去了,这里好得很。小洛,你也去,我这里住不下。”究竟是方外之人,虽刚刚认了侄孙女和徒孙,还没有亲热够,她说起这些话来,就像是平常的告别一般。
燕舞却更加不舍,说:“姑婆,我回到广华之前还会再来看您。”
三个人穿过飞云岭,绕过山梁,才到云舞崖顶上,天越来越暗,随着一阵冷风,雨就下了起来。淅淅沥沥地越下越大,越下越密,不一会儿树枝上和地上就全湿了,两个姑娘的头发上已经能拧出水来。
雷雄说:“走,我们去云岩洞避避雨。”
小洛俏皮地说:“要去你们去,我得去看看那边的猕猴桃都熟了没有。我前几天来的时候,它还硬着呢,酸得我直掉牙。”
原来云舞崖的岩石旁长了许多野生的猕猴桃,个小肉甜,在初冬成熟,兴许是今年秋冬太干燥,没有雨水滋润,仍然没有成熟。不待燕舞呼喊,小洛已经转过一块大石,消失不见。
雷雄说:“这个疯丫头,你不要管她,我们先去石洞避一避,等一下她会摘了桃子过来,给你这师娘吃。”
燕舞捶了他一拳,说:“你是她师父,不去管管她,却还在这里说笑。”
雷雄捉住了她手,说了声“走”,牵着她在栈道上奔跑,很快就来到云岩洞。洞里一切如旧,关公的石像威武庄严,石像前多了许多新老陈杂的香灰。
雷雄说:“关二爷,我回来啦!虽然不是衣锦还乡,但我始终没忘义字当先。我还带回来一个仙女一样的姑娘。哈哈!”双膝跪地,又对燕舞说:“小舞,你也来拜一拜。”
燕舞长在南方,对关公本来敬仰,更不愿违拗了雷雄的心意,和他一起跪拜起来。也不知拜了多少下,两个人起了身,在一侧的石凳上坐了下来。冷冷的山风呼过,夹带着雨水飘进洞来。雷雄轻轻将燕舞搂在怀里,怕她着凉,双手握住她的纤纤素手,驱动内力给她驱寒。眼看着洞口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两个人都开始担心小洛。
雷雄正准备出去找她,小洛却一阵风似地跑了进来,差点和雷雄撞了个满怀。
雷雄说:“你总是这样冒冒失失,什么时候能像个姑娘的样子?”
小洛满脸委屈,嘟着嘴说:“你没有瞧见,我怀里兜了一大堆桃子来给你们吃,走路自然就不方便啦。你这做师父的,一点也不关心徒儿,还要怪我。”说罢将怀里的猕猴桃小心翼翼地放在石像前面,又拿了一些过来放在石凳上,说:“燕舞姐姐,关公爷爷的我已经上贡了,这些都是给师父和你的!”
燕舞看她全身湿透,心里不忍,将自己外套脱了下来,要她换上。小洛也不推辞,却忍不住皱起鼻子,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雷雄出了门去,翻身一跃,来到栈道下面,由于栈道的遮盖,果然有许多尚未淋湿的杂草和树根。他心里一喜,收拾了一堆,回到洞里,点着了火。干燥的树根很容易燃烧,不大一会儿,熊熊的火苗就燃了起来,洞里渐渐泛起暖意。雷雄又去收了一些进来,码在石凳旁边。燕舞加了许多在火堆上,火越烧越大,暖意融融,几个人的衣服上都冒出热气来。
小洛说:“师父,你很有办法。你们快试一试,我在悬崖边上摘的桃子。”
雷雄把眼一瞪,说:“你没那么大本事,还要跑到悬崖边上去,也不怕摔下去。将来谁娶了你,还不得天天担心。”
燕舞剥开一个猕猴桃,咬了一口,这果肉有点沙沙腻腻的,但是却极甜,还带着一股香味,比水果商人贩卖的要好吃了得多。
几个人闲坐无事,雷雄看到这雨丝毫不停,便开始教授小洛内功心法。小洛悟性极好,雷雄只须稍一指点,便立即领悟。大概练了两个小时,外面的雨小了许多,但天色更加暗了。几个人趁着这当儿,出了石洞,沿着来时的路,踩着被雨水浸透的枯草,在渐渐模糊的夜色里,飞快地下山。到了地势稍微平坦的山脚,雷雄索性施展了轻功,将两个姑娘带得飞了起来。到了村口时,天完全黑了,家家户户已经点亮了灯,透出温暖的光来。
雷雄母亲殷秀妮早已撑了伞在门前眺望,看见一对璧人出现,一颗心终于落了地。
雷雄责怪地说:“妈妈,你一到了阴雨天就身子不舒服,却还站在这雨里。”
殷秀妮把二人迎进屋,红红的火炉上,挂了一个大大的吊锅,里面热气蒸腾,煮好的菜正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母亲已备好了碗筷,给父子二人各温了一小壶酒,小酒壶尖尖的嘴里正在往外冒着淡淡的热气。
殷秀妮说:“我当年生了你之后落下这病根,特别是春夏之交的雨季,腰涨腹疼得厉害。这季节,还不碍事。”
雷雄喜悦地说:“静雷庵的林婆婆是我师祖,她精通医术,你哪天去找她给你看看吧!”
殷秀妮在燕舞的碗里添满了菜,说:“那个疯婆子?我可不要她看。”
燕舞微笑着说:“她现在一点也不疯了,您说巧不巧,她还是我的亲姑婆。”
殷秀妮说:“哦?世上还有这么巧的事?那再好不过,我跟她要结成起亲家啦。等哪天雨一停,我就去找她。”
静雷庵里,一老妪一少女就着昏惨的油灯吃了晚饭。外面的雨声越来越大,空气越来越冷,林圆萍把火塘里的火烧旺了,说:“丫头,我知道你这样的人都性喜安静。我老尼姑这二十多年来,性子也变了许多,有时候一连好几天都没有人来,我便一连好几天也不说一句话。我们两个在一起,倒真是合适得很。”说罢呵呵笑着,似是自嘲。
木可儿裂开嘴,浅笑了一下。
林圆萍瞧着她明亮的眼眸映着火光,发出点点明亮如星又润泽如珠玉的光彩来,轻叹一声,说:“年轻真好啊!丫头,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木可儿点点头,满脸笑意。
林圆萍喝了一口茶,缓缓地说道:“二十二年前的一个初夏,有一个大大咧咧似乎是缺了一根筋的女人,她独自一人从清霞山下的家里出来,到卫州来接她的侄女和侄女婿。到了汉北火车站时,已经是晚上了,却没有去卫州的车。那时候外面下着瓢泼大雨,她无处可去,只得在火车站的大厅里等到第二天天亮再作打算。
几个小时过去,候车厅的人陆陆续续地上车走了,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大厅里冷清而又空旷。虽然是夏天,但这雨不停地下,风带着雨,把大门吹得一开一合的,还是有些凉。
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大厅里进来了两个男人,看样子他们是刚刚下火车,来这里避雨的。他们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二十七八的样子。这两个人都是南方人,他们边走边说,谈得非常投机。他们一进来就在那个女人旁边的那排座位上坐了下来,中间隔了一条很窄的过道。那个缺了根筋的女人一看见那个年长一点的男人,心就要跳了出来。”
林圆萍说到这里,丝毫不动声色。木可儿却本能地捂住胸口,一双清澈的大眼露出询问的声色,显然她已经被这故事吸引进去。只听林圆萍又说:
“因为那个男人正是这女人的同门师弟,十年前他们都在清霞山上学艺。本来,这一对师姐弟日久生情,互相爱慕,常常一起交流在师父那里学到的武功和医术,但两个人都没有把这话说出来,才导致这一辈子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