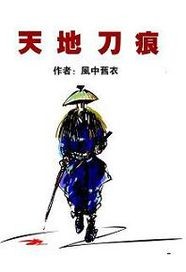第二天就开工。
三人都是练功夫的人,干这些活自然不费什么劲。成人杰和郦云的工作在棚子底下,避开了太阳暴晒。
雷雄的工作重些,还有技巧。不过对他来说,这根本就易如反掌。雷雄把一排排的坯砖整齐地摆放在板车上,摆得越整齐和紧密,便能摆得越多,但是又不能太过,否则坯子会粘连成一体又得重新回到泥口。雷雄总是比别人做得多,别人摆五排,他摆七排。运用板车的技巧也是恰到好处,不费一点儿力气。
和他做同一个工序的另外两个人累得汗流浃背。一会儿,他们的板车上几乎已经没有砖可码了,他们索性坐在车把上休息,抽烟。
“你一个人做得了,我们回老家去。”
“这么利索,管事的一定会喜欢你,给你多算点。”
两个人用开都方言酸溜溜地说道。
雷雄这才意识到,这是按块计件的,谁的晒场码得多,那便是拿的钱多。他抬眼看了看自己的,才两个小时,比他们两个人加起来的还多。
坯子再出来,那两个人依旧没有起身的意思。
“接住呀,大师兄!”眼看着坯子要掉地上了,郦云叫道。
雷雄把出来的坯子都接住,一手推了一辆板车,送到晒场去。那两个人惊得张大了嘴巴。
他再回来时,对那二人笑笑,说:“以后我只做半天,免得抢了你们的活路。”
那两个人早已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唯恐因为他遭到淘汰,听他这样说,齐声问道:“兄弟,这话算数吗?”
“我师兄说话从来没有反悔过。”
郦云答道。
那两个人推着自己的板车来接坯子,一个说道:“女娃,你也是快脚快手,一个人供应我们三个。照这样下去,不到下午,今天的产量就完成了。”
郦云轻快地一笑:“这地方闷死了,做完好出去玩玩。”
到了中午,传送带上面再没有泥出来,计划一天的量,半天就完成了。
人们把机器关了,坐着歇气。
管事的满脸堆笑,说:“中午多休息两个小时,下午还要做。小伙子,你跟我过来。”
雷雄见他叫的是自己,跟着他来到大烟筒后面。
“管事,找我有事?”
“嗯,你这个小伙子不简单,你愿不愿意帮着我管理这个砖厂?”
“不好意思,我还真没有这个打算。”
雷雄不假思索,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本能地排斥这个想法。
“我看得出,你们都很能干。你答应我,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为什么?”
“工头在外面还有几个厂子,他照应不来,准备叫我去别的地方,那我得找一个人来接替我。我们虽不是老乡,但我很喜欢你。”
“你不要再说了,我只想做好自己的分内。”
……
中午,管事的让人加紧备了大半天的泥。不到下午收工,人们又把它做完了。
“照这样下去,今年的产量要翻番了,就是累点。”
“咱出来是为了啥子哟?累点怕啥子,只要票子多。”
人们议论道,对这三个人投来异常友好的目光。
成人杰嘀咕道:“现在说我们好话,累趴下不怪我们才好。”
雷雄把师弟师妹叫到一起,轻声说了一席话,两个人对视一眼,点头答应。
到了第二天,三个人都下意识地放慢了速度,但仍是比那些人平时要快一些。
一天重复相同的动作无数次,夜晚躺在床上时,三人还是觉得些微的腰酸背疼。不过到第三天头上,这种不适感已经完全消失,反而觉得神清气爽,精力充沛。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三人对里面的环境和人们都熟悉起来。对这环境,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厌恶,只知道,不能一直待在这里。雷雄偶尔拿出师父给他的木盒,看一看,只得又放回原处。
“你瞧什么呢?这盒子看着挺精致的。”一个室友盯着盒子,眼神怪怪地问道。
雷雄笑笑说:“没什么。”
晚上,月朗星稀。雷雄独自一人,来到后山。虽然有风在轻轻地吹着,但仍不解闷热。他奇怪这树林里竟然听不到蝉声,也没有萤火虫,但也懒得细想。他环顾四周,找到一棵大松树,跃上树梢,折断一根一米多长长的树杈,把松针摘了,用它当作一个工具在地上戳了一个小坑,然后以掌为刀,运足内力。掌风到处,被松动的土被拍得四散。很快,一个一尺见方一米来深的土坑就挖好了。
雷雄把小木盒放进土坑,自语道:“这地方人多手杂,放在宿舍始终不安全。如果万一丢失,帮师父寻找亲人的线索就断了,我也不能一天到晚装在身上,只能先埋在这里。有了安定的地方,再挖出来。”
何志友再也没有出现过。
一天傍晚,即将收工时,大家一如既往地干着活,工棚里忙碌而又紧张。
忽然,郦云眼前一黑,“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成人杰一看,急了,忙停下手中活,将郦云背到宿舍。
雷雄跟了进来,摸了摸郦云的额头,只觉得烫手。
整个生产线也都停了下来。
成人杰跑去食堂倒开水。过来时,郦云已经晕了过去。
这时,外面人声鼎沸,只听见人们愤愤地骂着:
“真不是个东西啊!黑了我们的血汗钱自己跑啦!”
“狗娘养的,真不是人,卧槽他十八代祖宗……!”
成人杰正在给郦云喂水,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回到宿舍来。
雷雄问:“大姐,这是怎么回事?”
那妇女眼睛红红的,恨恨地说:“天杀的工头跑了,早上还说今天下了班就发工资的,他却拿着钱自己跑了,我们两个月没发工资了。”
雷雄正想再问,那妇女收拾着东西说:“你们还不快走!我们都是跟着工头来的,老板得知工头跑了,怕我们在这砸了他的砖场,要来把我们都赶走。”
“这都是些什么人,我们已经很惨了,他还要来赶人?还有没有王法了?”
妇女急急地说:“他已经派人过来传话了,今天晚上都要离开这里。”
“大姐,你不用怕!这件事,我来管。”
成人杰说:“雄,别多生事端。现在师妹病着,先救她要紧。”
雷雄双眼冒火,说:“这事我看不下去,非得管一管。”
成人杰说:“好!我也不愿意当缩头乌龟,要管,我们一起管。”
“不行,你留着照看师妹,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要出来。”雷雄说得斩钉截铁,“不知道待会是个什么阵势,师妹这样子不能拖延,我们不能跟他们理论,要速战速决。”
那妇女眼含泪水,说:“兄弟,你们都是好人。可是在这节骨眼上,你还是先救这女娃吧!我们身在他乡,首先要保证的是自己的平安啊!”说完,提起自己的包袱就走。
这时,有几个粗壮的人牵了几条大狗已来到了山凹里,那狗对着一片宿舍狂吠起来。人们禁不起这些惊吓,乱成一团。
那些人和狗很快来到了这边。
“都给我滚!搞快一点!”牵狗的一人用夹生的普通话说道。
人们大部分已经拿了自己的行李包袱,有的仍在收拾,有的不要包袱双腿打颤地往外走,而还有的,则眼巴巴地望着雷雄。
雷雄只觉得胸腔里有一团火就要燃烧了,怒吼了一声:“你们是干什么的,不要太欺负人!”
那个牵狗的打了一声呼哨,一条大狗像箭一样地冲过来。
雷雄不待它奔到跟前,脚尖在地上轻轻掠过,带起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往前一送,一声轻响,那狗痛苦地吠了几声,再也没有声音了。
其余的狗都乱糟糟地叫了起来,它们的声音里似乎充满了复仇的愤怒。
那几个牵狗的松开绳子,同时说了声:“上!”
十几条狗一起乱叫着冲过来,行成一个合围之势。
雷雄脚尖轻点,身子离地,双掌一推。
“平地起风!”
“碧海生波!”
不要说冲在前面的狗,就是站在后面的人也无一幸免地倒在地上。他们全身剧痛,想爬起来也是非常费力。而砖厂的这一帮打工仔无不惊奇。
“靓仔,你系谁?”
一人忍着痛问道。
雷雄说:“你们别管我是谁,只要对我们有个交待。我们被工头卷了血汗钱,已经是受害者,你们却也昧着良心欺压我们。打工仔就那么好欺负吗?!”
“你要怎样的交待?我的钱已经给出去了,他们的死活再与我无关。”那人忍着痛说道,看样子,他就是老板。
他带来的人都纷纷附和。
“让我们留下来,有个安身之所。冤有头债有主,我们都是明事理的人,既然是工头已经拿了你的钱,我们又怎么会拿你的砖厂来泄愤?”雷雄说。
“好,靓仔,我就相信你一次。明天,我还会再找人来管理我的砖厂,愿意留下来的可以继续留下来做,不愿意的只能在这里住三天。”那人挣扎着起来说。
其他的人也都慢慢爬起来,在这人的带领下,牵着自己的狗,相扶着离去。地上多了五六条死狗。
“兄弟,多亏了你,我们把这狗肉炖了吃。”一人对着一条死狗踢了一脚,说道。
“师妹病了,我没有时间吃狗肉了,我们要出去找医生。”雷雄答道。
“从小路下山,到了街上一直往前走,过第一个十字路口左转,有个小诊所。”那人说道,从口袋里掏出被捏得干巴巴的几十元钱交给雷雄,“拿去给女娃看病。”
“好!给师妹看完病我们就回来吃狗肉。”成人杰将郦云背在背上,说道。
二人顺着来时的小路下山,远远地看见前面有一群穿制服的人拦住一个路人,说了三句话,便把那人押上车去了。
“人杰,这莫不是他们所说的查‘三无’的人?”
“怎么办,雄?”
“师妹不能耽误时间医治,还是躲开为妙!”
“好!”
他们调头,脚步轻快地往一片小树林里小跑过去,雷雄只想等这群人稍微走远,便用轻功带着二人赶快找到医生所在。眼看着那一群穿制服的往砖厂方向去了,雷雄在心里暗叫了一声不好。
穿制服的有一人眼尖,发现了他们,高声喊:“那边有人跑了!快追啊!”他们便也往小树林跑过来。
此时仍正值夏天,虽然还是日长夜短,但天色已黑了下来。
雷雄把郦云接过来,背在自己背上安慰她,郦云把脸伏在他背上,浑身冷汗直流。雷雄只觉得后背湿了一大片,也不知是汗水还是郦云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