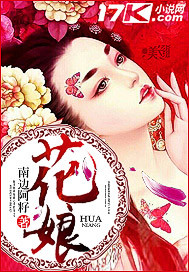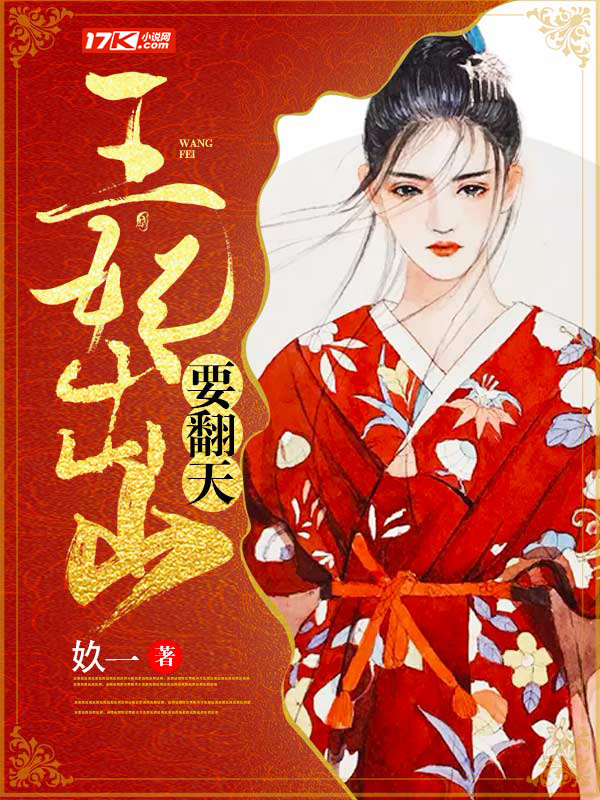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得了很严重的病,一蹶不振。
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和谁在一起我都会害怕,我觉得四周有某个人在阴暗的地方盯着我,随时会给我一枪,或者是我身边没人的时候借机将我捉走。
晚上的时候我总睡不踏实,我强烈的感觉坏人藏在窗帘后面,藏在衣柜里,藏在厕所里,藏在房顶的天花板上,我甚至不敢盖上被子,我怕掀开被子的时候坏人正仰面躺在里面直直的看着我笑。
每每顾延之下班,总要到处找我,我会藏在自己认为安全一点的地方,屏住呼吸。甚至有一次,我鼓起勇气把家里的床板打开,看到里面没有人的时候欣喜若狂,我把家里大的拉杆行李箱打开钻进去,在床板底下藏着。
明明知道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叫我名字的是顾延之,在床上翻来覆去弄出动静也是顾延之,但是我还是不敢出声,不敢出去。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空气,第四天的时候我彻底失去了意识。
等到我清醒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卧室的大床上,顾延之坐在床头看着我,眼圈通红。
我大声尖叫:滚开妖怪,你滚开!
他使劲的试图将我抱住,安慰我:是我,我是顾延之。
我挣脱他,胡乱挥舞着双手打他:你是坏人,是妖怪!
因为顾延之从来都不是那个样子的,凌乱的头发上混着油和碎屑,衣服扣子扣的乱七八糟,脸上的胡茬跟污渍把脸遮起来,分明就是流浪汉。
他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不再试图靠近我,而是温声细语的跟我商量:我走,这就离开,瑟瑟你不要动,不要乱跑,好好躺下睡一觉,等会顾延之就回来了。
我把被子整个的罩在身上,不留一点缝隙,在里面不可抑制的发抖。
等到顾延之又跟之前一样干干净净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抱着他的脖子哭的直抽气。
后来我的病越来越严重,开始出现幻听,幻视,我能看到地板上,床上爬满嘶嘶吐着信子的蛇,一脚踩下去软绵绵凉嗖嗖的,我还能看到正在我眼前慈祥的跟我说话的母亲突然长出青面獠牙。
吃药也越来越费劲,因为拿着药瓶的顾延之会突然变成清宫戏里的太监,尖着嗓子阴险的跟我说,他手里拿的是剧毒,要毒死我。
……
医生说我这是精神分裂,单单药物治疗是很难治愈的,需结合心理治疗,家人要对我有足够的关爱和信心。
顾延之休了长假,带我去他的老家静养,距离苏州市区四十多公里的一个风景秀美的小镇,古色古香的建筑,每天早上还能听到鸡鸣钟响。
敲开镶着铜环的大门,那里的人说着我听不懂的吴侬软语,顾延之骗我说,我们来到了仙境,这里不会有坏人,他们不敢来。
渐渐的,我的神识开始回归,只是偶尔还会做噩梦,生活起居不再是顾延之照顾,按时睡觉,按时吃药,也能跟顾延之聊聊天,听他教我说吴语。
顾延之会做糖年糕,他系上围裙站在灶台忙活,把粳米粉糯米粉和上白糖沾冷水揉成面团放锅蒸,等到蒸成玉一样通透再用冷水布包着揉捏,摁压至光滑,铺上桂花,切片装盘。
那天晚上,我将整盘的糖年糕统统咽进肚子,顾延之怕我噎着,皱着眉头给我沏了一杯碧螺春,澄黄透亮的茶汤清香甘洌,我尝一口然后随口问他:糖年糕是谁教你做的?
他沉吟了一会儿,说:是我的母亲。
他脸上的神情变化微妙,想到也许是触及到了他的伤疤,我低头不再言语,顾延之的母亲在顾延之二十五岁那年死了,他只告诉过我这个,其它的事情都讳莫如深。
细语温存之后是漫长漆黑的夜。
顾延之拿起我的头发在他手指上绕圈,一遍又一遍,很久之后我都要睡着了,他低沉暗哑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我的母亲是被人杀死的。
那个聪明贤惠声音温柔的漂亮女人,因为父亲长期的酗酒赌博被迫嫁给顾延之的父亲,顾延之的父亲自小体弱多病,结婚不到半月便撒手人寰。
顾延之平静的说:父亲留给母亲一笔钱,正是靠着这笔钱,母亲省吃俭用供我上完了学,我去外地工作,母亲执意不想跟着,她说她在这里待了一辈子出去会不适应,这里还有她的朋友们。
正是她的朋友们,觊觎她手里不知多少数目的钱而杀死了她。
我不应该把她留在这里的。
顾延之的声音愈发沙哑,手也开始不可抑制的抖动起来。
顾延之从枕头底下拿出他曾带着的腕表给我看:这是母亲给我准备的生日礼物,我回来的时候,看到她被人按住口鼻捂死在床上……
不要再说了,一切都过去了,我心疼的小声安慰。
良久,顾延之跟我说:瑟瑟,除了母亲,你是我最重要的人,不要离开我,也不要再吓我了,快点好起来。
……
我是他最重要的人,他又何尝不是我最重要的人呢。
我死的那一天才明白,这个世界上其实根本没有好人与坏人,邪恶与正义,公平与不公平,分不清也没必要分清,还是浑浑噩噩的什么都不知道,日子过得才自在。
病好之后,局里给了我一个大案子,正是跟当年那个服装店女老板有关,因为继她之后,每年都会发生那样一宗碎尸案,2035年凶手作案终止,一共死了五个人,成了悬案。
切割整齐的尸体碎片煮熟后存放在死者的冰箱里,被丢出去喂狗的内脏跟肠子,还有失踪的头颅,死者年龄最长的是五十三岁,最轻的是四十岁,来自不同行业,家境也都不相同,唯一共同点就是都是女人,凶手没有一丝的破绽露出。
每天我都会起早贪黑跟同行出去四处搜寻证据,去找死者的亲属做笔录,奔波劳累时间长了,身体便有些不适,总是头疼,顾延之每天晚上会给我炖一份补品。
顾延之的温柔体贴让我彻底沉陷,却不知这只是夜幕来临前的残阳瑟瑟。
头疼的症状愈发严重,也开始做那些血淋淋的噩梦,顾延之说我太劳累,本来就有旧疾,不应该操劳,更不应该办理那种恐怖的碎尸案。
他让我休息,什么都不让我做,我不知道,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在警告我了,他在汤里放了刺激神经的药物。
那天,我抽空回去公安局,叫人拿出来之前的卷宗反复查阅,并没有什么结果,我想起来顾延之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有些案子并不难破,只是证据不足,很多证人都会刻意隐瞒死者的一些秘密。
当即我便去死者家属那里走了个遍。
我拿着五个死者的照片让他们的家属一一辨认,希望他们能给我点答案,至少让我再发现一点五个死者之间的联系。
如果我早知道结局,我肯定不会去。
五十三岁死者的母亲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上回见的时候还是头发乌黑腿脚利索,而现在显得格外苍老,我一张口她便打断我的话:不是早就问过,一次又一次的来是要做什么,我的女儿死了我很难过。
您的女儿死了,无论她之前犯过什么样的错误,都无法再追究,而现在我们要追究的是谁杀了她,给她应有的公道。
沉默过后,老太太的眼睛终于浑浊起来,她颤颤的坐到沙发上失声痛哭:她死了是罪有应得啊,她跟我说她害过人,这是恶报。
经过一番彻底的询问,果真这些死者家属都说了慌。
五个死者当中有两个是苏州本地人,后来迁移了户口,还有三个外地人曾在苏州市区做过工人,这些警察都不知道。
五十三岁的死者曾害过人,共同隐瞒的死者们在苏州的事情。
如果不是顾延之给我讲过他母亲的故事,我想我不会这么快破案。
思路渐渐变得清晰,我心惊胆战去咨询了苏州当地大大小小的警局,他们从未受理过顾延之母亲的案子。
五个罪犯千辛万苦的逃逸却不知道可怕的不是被警察抓住,而是被报复的死无全尸。
我想起来那天,我把顾延之送给我的腕表拿出来把玩,我一直都把它放在一个漂亮的小盒里放着,不曾发现指针已经不转动了。
我拿去修理,修理师父告诉我那只是一个观赏品,里面根本没有齿轮,什么都没有,不会走动的。
时间始终停留在七点一刻,当时只觉得迷惑,却不知道哪里迷惑,此刻才知道是当年他到警察局给我作证。
我想笑,到底是谁给谁做了证人呢?
……
我回到家,顾延之刚好炖出来一锅汤,想到他做饭的那双手沾满了鲜血我就想吐。
我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让他看出来,我说:顾延之,我知道凶手是谁了。
他盛汤的手稍微一顿,轻轻嗯了一声。
我继续说:和当年把我关起来的人是同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留在那间密室里,明天我会去把它找到。
我会自己去的,我刻意给他强调。
第二天清早,我去了那个让我梦靥的地方,然后爬上房顶去看到光秃秃的天窗,没有什么暗格的,怎么放钥匙呢?
我安安静静在那间密室待着,等着顾延之。
密室的门半掩,虽然有阳光和空气进来,但是依旧很臭,我告诉自己不要害怕,不会再有蛇了。
过了许久,门外传来脚步声,渐渐的离我越来越近,我越来越害怕,我听到手扶上门的声音,我知道他要来杀我了,我猛的站起来,用尽所有力气要把门关上,但是他的劲比我大,他使劲推着门,我们互相对峙,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被杀死。
幸而,他松手了。
我得以把门关紧,哭的稀里哗啦,我说:顾延之,我以后再也不做警察,你以后也不要再杀人了可以么,我不想死,我也不想你死,我放过你,你也放过我,我们还是夫妻。
就这样,连空气都安静下来,沉默过后,他什么也没有说,然后离开了。
我想,顾延之其实是很爱我的吧,他把埋在心底的关于他母亲的秘密告诉我,他把我关起来只是吓唬我,让我不再查案,他也害怕有一天我会亲手将他绳之于法,就算是刚才他也没有杀我。
我缓缓呼出一口气,忽然,有什么握住了我的一只脚,腐烂的血腥气渐浓,低头看去竟然有五具血淋淋的尸体张牙舞爪的过来抓我,她们发出尖锐的声音来:不想让他死,那你就替他死啊!
替他死,我是多爱他,才会出现这样的幻觉?
心脏骤然衰竭,我透过门缝看顾延之的背影越来越远,我想叫他回来但是发不出丁点的声音。
……
“真的有点累了,没什么力气
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
爱你的心我无处投递
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你
爱的委屈,不必澄清
只要你将我抱紧……”
顾延之睁开了眼睛,一滴眼泪顺着他的眼角滴下去。
我伸出手去想给他擦掉,却发现双手渐渐碎裂,消失。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响贪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