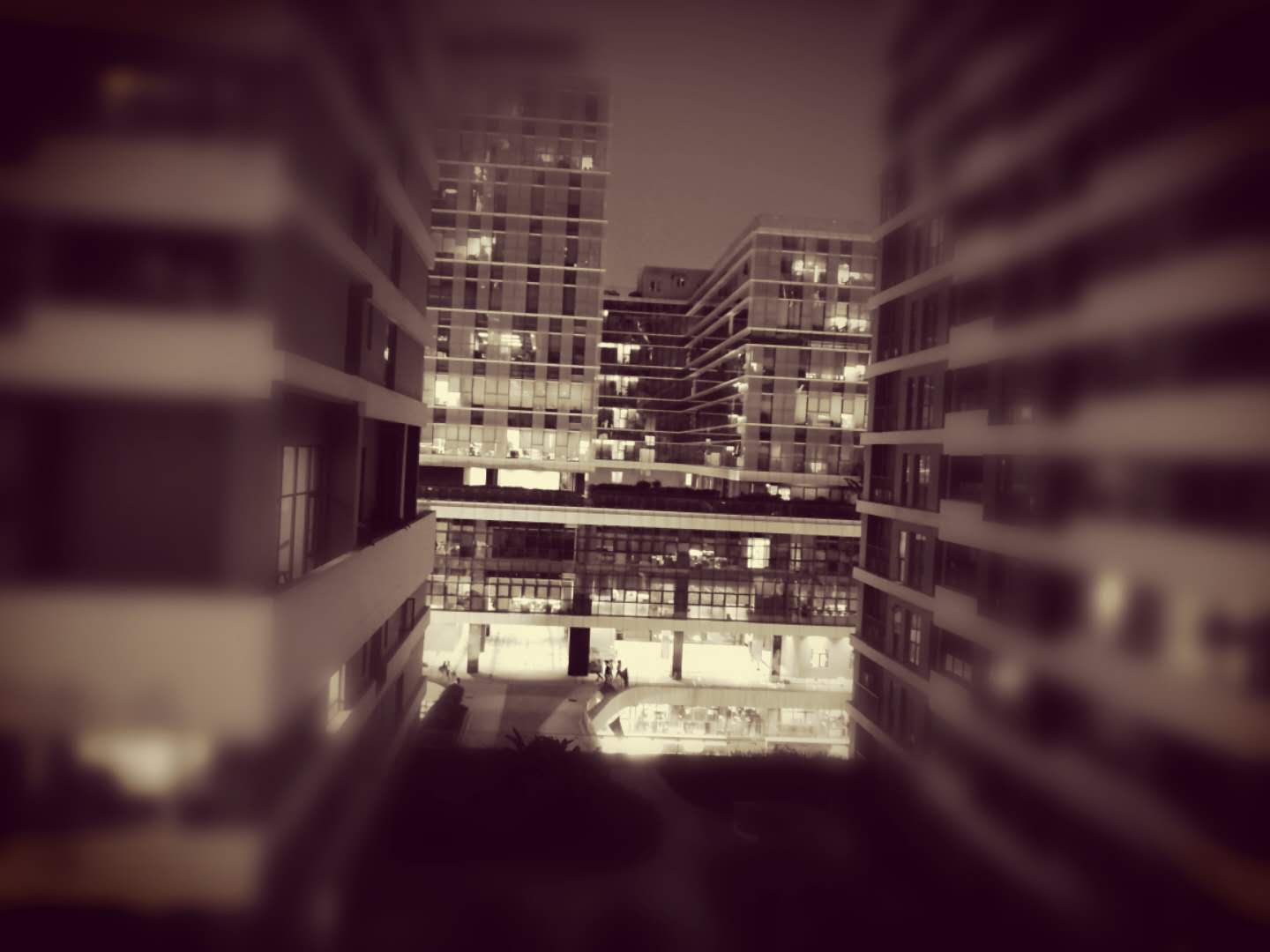“你真的要跟他回去?”手被干奶握得死紧,晏安甚至能感到自己的骨节在彼此摩擦。
干奶声泪俱下地开口:“晏粱是人是畜生你不清楚?他后找得那个媳妇又给他生了对龙凤双胞胎,你跟他回去,他不会对你好的。”
“我都知道。”晏安没什么情绪,淡淡开口:“但是干奶,我必须得读书。”
“磨蹭什么啊?”俞顺康烦躁的声音在门口响起,“衣服什么的都不要!回头找点俞珂不要的衣服给你,不要把跳蚤蟑螂带回我家。”
干奶扯着她的袖子不肯松手,问:“就在这里读书不好吗?”
晏安摇头,勉力安慰:“您放心,我一定照顾好自己。我妈的钱,我一分不会给他。”
炽烈的太阳下,院里老井孤零零地矗立着。
晏安想,她死在这里,又在这里获得新生。所谓的因果,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
“脱了鞋子再上车。”俞顺康把车窗升了上去,嫌弃厌烦地开口:“别把我车给弄脏。”
这是他的车吗?这分明是他老板的车。不过这家人一向这样,乐意把外人的东西当做自己的。
干奶捂着嘴嘤嘤地哭,晏安倒是一秒没犹豫就脱了鞋。
干奶拉着她的手,像是要把她的骨头都给捏断一般。
晏安抱着她,把头埋在她耳畔轻声说:“您照顾好自己,等那边稳定下来我就回来看您。”
她提着鞋光着脚坐上车,下一秒,鞋就被俞顺康从窗户扔了出去,他哼了一声,说:“妈是捡垃圾的,女儿也是捡垃圾的,母女俩一样得脏。”
晏安抿了抿嘴,把到了嘴边的讥讽刻薄给咽了下去。
“没事,丢就丢了。”董馨拉住了她的手,笑意盈盈地开口:“回头再给你买双新的。”
晏安歪头看了她一眼,没吱声。
俞顺康转过头来骂她,“你哑巴了不成?你妈跟你说话呢!”
晏安没忍住,顺嘴接了一句,“我妈在今天刚埋,你……”
话音没落,一个摆件就擦着她的头皮飞了过去。
“你要不愿意管我叫妈,叫名字叫阿姨随便你。” 董馨还是紧紧握着她的手,说:“我和你爸生了对双胞胎,哥哥叫俞岩,妹妹叫俞珂,和你差不多大,以后都是一家人。”
晏安觉得这董馨实在是个巧妙人。平日里佛珠不离身,又是吃斋又是念佛,人长得也一团和气慈眉善目,怎得心里就能有那样多阴毒念头,能做出那么些龌龊卑鄙的事。
窗外树影婆娑,黄土飞尘黏上车窗,外头太阳被云遮蔽,整片天空昏昏暗暗。晏安想,如果人生轨迹和上辈子相同,以她母亲的死亡开始,以她的死亡为终结。那她这一生人的悲剧,就是从踏上车的这一刻开始。
她该怎么做呢?
车子一路飞驰,最后晃晃悠悠进了一个老旧小区。
董馨指着面前一栋墙皮脱落的矮楼跟晏安说:“我们家住在这的6楼。”
城中村里头的房子,看上去就有些年头。晏安记忆里,这里一到晚上楼下就全是夜摊,烧烤的油烟能顺着空气飘到家里,喝酒划拳醉酒吵架的声音要进行到半夜三更。
下了车,她赤着一双脚站在地上,董馨看见了,赶上前就说要背她。
晏安被她这一路过来的示好搞得心惊胆战毛骨悚然,这人表现出的温柔体贴是比俞顺康的打骂训斥更让晏安感到畏惧的东西。
她仓惶地摇着头,快步朝着前头的俞顺康追去,没走几步,脚底板就戳出了血。
楼道又黑又暗,满鼻子都是厨余的酸臭味道。估计着家里没人,俞顺康直接掏出了钥匙,门一打开,他就愣住了。
从缝隙里,晏安看到了沙发上勘勘分开的一男一女。
“俞岩!”
带着惊讶怒意的声音惊动了屋里的人。化着浓妆的女孩子从沙发上蹦起,嘴里念念着家中有事,慌乱地挤开俞顺康,从晏安身边跑过,留下一道的劣质脂粉味。
晏安侧眼,只见董馨脸色难看,俞顺康厉声质问:“她是谁?你们在做什么?”
一个听上去就吊儿郎当的轻浮声音在屋里响起,“同学,来送假期作业。”
俞顺康稍微错开身,晏安就看到了屋里那个满脸痘疤一头黄毛,左脚绑着石膏的少年。
董馨凑在她耳边亲切介绍:“这就是你弟弟俞岩。”
晏安看着俞岩,想基因这东西也真是奇妙,她大概两辈子也弄不明白,俊朗的俞顺康和中规中矩的董馨为什么会生出来这样一个丑绝人寰的玩意儿。
俞岩杵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朝他们走来,盯着晏安,问:“这就是以后要寄宿在我们家的人?怎么和俞珂长得一点不像?”
晏安看着他走近,满脑子都是他捏着烟头往自己胳膊上按,胁迫自己给他磕头求饶的狞恶样子。
只听董馨说:“也是倒霉,他前不久把腿给摔断了,这伤筋动骨一百天,也不知道开学的时候能不能好。”
晏安记起来,上辈子摔断腿的俞岩最后没恢复好成了个残废,也成了个心理变态。她印象里占据更多的,还是俞岩他打她欺负她时候的样子。
“这就是姐姐啊?”俞岩笑,露出了一口让晏安恶心难受的错乱黄牙。
“安安性子内向,你别逗她。”董馨拉着晏安往里走,说:“家里太小了,拢共就这么点大,只能委屈你先睡客厅一段时间,看看过些日子能不能搬到大一点的房子去。”
“大一点的房子?”晏安好奇,问:“打算搬家吗。”
“嗯,等手头宽裕些就换到大一点的房子去,到时候你们三孩子一人一个房间,住着也宽敞些。”
晏安扯扯嘴角,想这董馨说话也真是漂亮。什么叫等手头宽裕一些?手头不宽裕她就得一直睡客厅睡沙发?那什么时候手头才能宽裕?等把她母亲的抚恤金拱手送给她?
她上辈子也确实给了,结果呢,她在这翻身都困难的沙发上睡了整四年。
不过这能怨得了谁。那时候遇到个会说话的人都在明里暗里提醒她不要相信这家人。只是她蠢,觉得俞顺康毕竟是她亲爸。然后在她把母亲抚恤金交出去的那一刻,她就成了蜗居在这个家角落的一只蟑螂,不好赶走,但谁都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