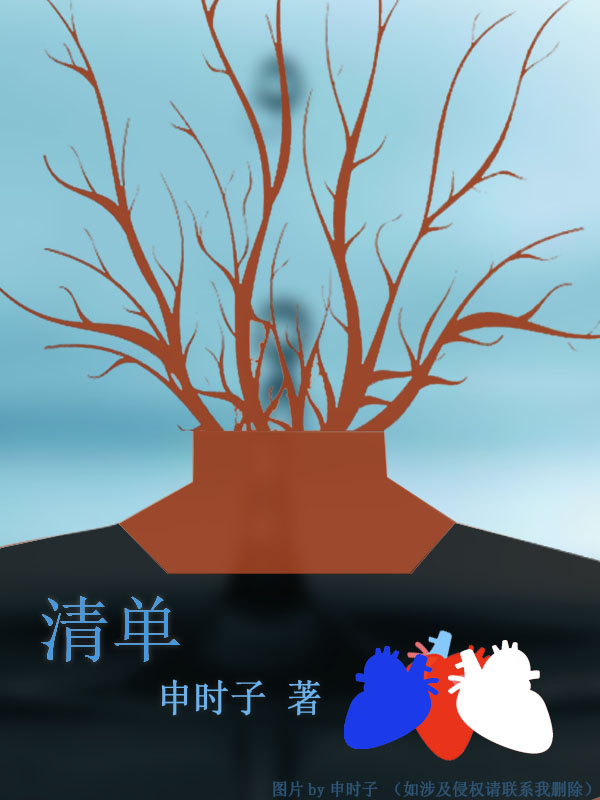距离推算出来的边缘位置,只剩下了两个房间。
三人一致决定铤而走险,看看能否到达所谓的边缘。
只是当我忍不住走到最后一间监狱中时,看着眼前最后一扇圆形铁门,就连握着拉环的双手都不禁有些颤抖。
门后的世界应该就是所谓的监狱边缘,逃生的希望就在于此。
此时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既然所在的方形空间是有规律的移动,那么我又怎么可能保证自己一路穿越过来,眼前的位置依旧是没有脱离轨道的终点。
或许队伍在无形中早已经迷失的方向只是我们不得而知…。
醒来的时候自己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旁边是正在削苹果的小玥。
她看见我朦胧睁开双目的样子,激动的连苹果都掉落在地上,那一刻我隐隐看见她的脸上落下泪痕。
那是激动的喜悦,眼神交流中瞬间明了,我恐怕已经在这张床上躺了太长时间吧。
身上盖着的是白色的床单,床边放着生满铁锈的氧气瓶,在这间陌生病房醒来的自己不禁有些茫然。
好在有小玥,她将我昏迷以后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
原来那条暗道的尽头处居然通往着日军逃生的电梯机关,而那个老贼也确确实实的死在了墓里。
残碎的尸体是小玥和胖子亲眼目睹,胖子念他曾是自己的师兄还为其找了一块埋骨地,算是简单超度了一下。
至于我是什么时候就开始不省人事,这一点他们也并没有注意。
只是在登临电梯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队伍里少了一道人影,回头时我已经躺在石阶上双眼翻白。
脸上的面具也已经掉在地上。
“嘶…这么说,咱们成功逃出来了。”
我有些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却发觉浑身上下没有不疼的地方,当初在墓里时还未感觉到这么强烈,现如今却仿佛连脑仁儿都在痛。
经历过这一次以后,眼前小玥似乎也比曾经蜕变了不少。
只是当她将下一个消息告诉我时,就连脑子里仿佛也是一阵僵硬。
“出来以后就遇上了廖警官,原来医院早已经被他们封锁…,其中还有一些穿着怪异的人。”
“是军方的人,这件事情被军方插手管进来了!”。
一瞬间我醒悟了过来,不过这似乎已经没什么大不了,墓中并没有发现,我一直苦苦寻觅的阴珠。
“既然他们愿意,就让他们去搜索吧。”
回想起醒来时的经历,宛如南柯一梦。
这么说自己和胖子小玥最后在超级立方监狱里寻找出口,这一切都是因为少了面具后的癔想。
三个月以后我的病情终于彻底恶化和爆发,好在有小玥的陪伴让我不再那么寂寞。
而癌细胞已经彻底侵入全身大半个器官,我像是濒死的人疯狂的开始抓住救命稻草。
甚至不惜花掉吴老狗继承给我的遗产,我真的太想活下去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阴珠还没有找到。
经过一周一次的化疗以后,我的病情总算有了稳定,小玥丫头失业了以后就像是牛皮糖一样黏上了我。
或许这种比喻不算太贴切,因为她一个19岁的小姑娘,又怎么可能会对我这个年近30岁的将死之人如此细心照顾。
如果有,那说明她一定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少了佩戴面具以后,晚上经常会被噩梦吓醒。
我几乎每一晚都能梦见一道瘦小的小女孩身影,身旁站着两个高大的男人。
那个胖男人嘴角总喜欢叼着根烟,脸上有一道骇人的疤痕。
至于那个瘦高的神秘人,我始终在梦里看不清他的脸,这一切都是朦胧的。
在小玥的极力坚持下,我决定趁着病情有所好转去看心理医生。
随着我的轮椅被小玥缓慢推入病房,眼前狭窄的空间内正坐着一位身穿医大褂,脸上戴着眼镜看样子有些文弱的男人。
窗外细雨蒙蒙,我甚至有些开始厌倦这种天气,每一次下雨我都会忍不住大发脾气。
当然是趁着小玥离开的空档,一个人生气的摔着枕头。
我将自己连续几天做的噩梦通通倾诉给了眼前这个男人,他告诉我戴面具能够防止人格分裂只是一种心理暗示和假象。
随后他叫小玥先退出病房,想和我这个有精神历科的病人单独交流,只是当身后的病房门被轻轻合拢的一霎那。
一股无形的压抑,以及恐惧弥漫在自己的心头。
“原来是这样…,那你能将梦里的三人轮廓画在这张纸上吗。”
眼前的心理医生面带微笑,他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了纸笔,脸上的笑容让我无法拒绝。
自己的画工只能算是普通人的境界,并不像有些人天生就对美术有着天赋加持。
不过我还是尽力描绘出了许多细节,例如中间的那个小女孩穿着花棉袄,身旁的胖子脸上有一道疤。
另一边高瘦的人影总是看不清人脸等。
眼前的心理医生接过我递来的画像,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那张惨白的C4纸,似乎是在若有所思的沉思着什么。
“甘先生…,您之前还幻想过什么…,例如您有一位警察朋友。”
我瞬间呆愣住了,随即瞪大着眼睛问道:“警察…?”
心理医生的话让我彻底荒了神,毕竟在故事的开头我还真的认识过一位不苟言和的老刑警。
只是关于他的样子,我无论怎么样也想不起来。
“老严!”
“老严是谁…,我怎么一点点印象都没有了。”
思索间却觉得自己的头皮仿佛要炸开,我忍不住用双手捂着头疼欲裂的脑袋,目光却在无意间瞄在了刚刚递过去的C4纸上。
那上面画着的哪里是梦境中的三个人影,分明是一道魁梧的人像。
他身上穿着的警服,身材与气质都在无形中透发出威严和正义。
只是脖颈上空无一物…,在刚刚的作画中我并没有画出他的脸。
紧接着便是脑子嗡的一声,有什么东西仿佛是要撑破枷锁,却又硬生生的憋了回去。
时间结束了,我看着眼前的心理医生心中不由生出了一丝疑问,随即小心翼翼的开口问道。
“我算是您接受过的最怪异的病人吗。”
他听罢竟忍不住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随即轻轻的摇了摇头微笑道。
“我治疗过很多有精神病史前科的病人,他们有一些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有一位病人说,自己一出生就发现周围的人都没有脑袋,包括自己的父母。”
“只不过那时候自己还很朦胧,直到五六岁时候照镜子时才发现,为什么别人的脖颈上都是空无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