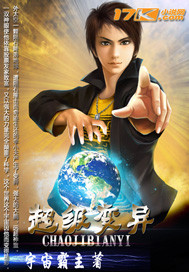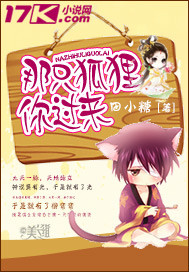纪挽月见她不语,笑意又深了几分,喝着茶淡淡道:“此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全看陛下如何揣度,说小了不过是你这个推官的无能,并没有查明真相,大不了罢官回去种田。”
略顿了顿,他低头喝了一口茶润嗓子,似乎就是为了吊她的胃口,良久他才道:“这往大了说,是你恶意隐瞒事实,企图图谋不轨之心,大不了你小命不保,只是,你一个六品小吏,背后不可能无人撑腰,所以这所谓的往大了说,恐怕是这段大人……没准还要扣上一顶欺君的帽子。”
他的语气看似平平淡淡 ,实则在每个厉害的字眼都加重了语气,白寒烟不由得心下一慌,此事绝非小事,明显是冲着段长歌来的,若要将此事闹大,或者有人在旁煽风点火,圣上极有可能一怒之下,治他一个欺君谋逆之罪,只是皇帝却按下不发,只派了锦衣卫来此,想来就是为了试探段长歌。
当下她沉下双眸,思虑良久才开口道:“下官不过六品小吏,百死无惧,段大人却是国之栋梁。芜族残部一族向来记恨我大明,更恨段大人昔日铁面,今日得了王大人之死的由头,来挑拨陛下与段大人的嫌隙,陷害忠良,借刀杀人……皇帝英明,既然将此信借由纪大人之手丢给下官,自然是看破了敌人如此卑劣的伎俩,更不相信别人的恶意诬陷,可见段大人忠心可昭。”
纪挽月定定的看着白寒烟,这本来一件祸可砍头的大罪,竟被这个六品小吏三言两语便轻易化解,将段长歌摘得是干干净净,更是看透了皇帝的心思,此番奉命试探竟成了一场无功而返,弄不好自己反倒成了污蔑皇亲要员之罪。
纪挽月想了想,只好抿唇笑道:“你这小吏当真是牙尖嘴利,我不过说了下其中利害,并无恶意,不过,你对段大人倒也忠心。”
段长歌依旧斜倚在椅子上,眉目浅淡,却是戚戚的笑了一声: “指挥使大人这话,若无真凭实据的话,果然是酌尽黄河之水,也洗不去本官一个欺君谋逆的嫌疑了。”
纪挽月身体一抖,当即惶然,这朱长歌可是皇帝金口玉言亲自封的外姓皇亲,不仅战功赫赫还统领贵阳一司,诬蔑朝廷大员这罪责绝不轻,当即 站起身对段长歌行了一个大礼,方才起身略歉疚道:“段大人不必恼怒,本官只是替陛下揣度利弊罢了,岂敢诬蔑段大人呢,就连圣上也并没有将此信放在心尖上,只看了一眼就置之不理,想来朝中还要倚仗段大人。”
“小人伎俩,且付之一笑罢了。”段长歌挑眉看着他,眼间的一股强大的气势摄人千里。
白寒烟想这种强大的气势,真正的是行军打仗之人才有的,那是在战场上一刀一剑砍杀出来的。
纪挽月附和的笑了笑,才落首座,低眉看着地上的白寒烟,又笑着道:“王锦之死凶手布局巧妙,韩推官竟然短日内便破了凶手计谋,圣上也盛赞不已,想要亲耳听听你的述案,所以此番回京,韩推官怕是要与本官同行。”
此言一出,白寒烟当即震惊不已,皇帝竟然要她亲自去述此案,看来,他还是不信这精铁矿产实属空穴来风,想要亲自试探她。
“怎么你不愿去?”纪挽月瞧着她一时无语,冷然嗤笑。
“还不谢恩。”段长歌落下手中茶杯,轻声喝了一下,白寒烟当即跪地叩首:“谨遵圣意。”
纪挽月满意的笑了笑,偏头对段长歌笑道:“段大人,从即刻开始,案犯便交由锦衣卫看管,圣上说了,进京之前不准他二人殒命,我们锦衣卫可要好生看管,以免他二人想不开。”
段长歌饮茶的手一顿,低眉敛住眸子的神色,只是淡淡应了声:“好。”
夜里无月,风声鹤唳,好像女人悲伤的呜咽。
涟儿在白寒烟身后掩袖悲痛的啼哭,她知道,灵淼这一去是必死无疑了。
“涟儿,对不起,答应你的事我没有做到,现下灵淼和灵姬已经移交锦衣卫,恐怕连我见上一面都很难。”白寒烟对涟儿面带歉意,终归是食言于她。
涟儿悲戚更盛,泪水一下子全部都涌了出来,哭得伤心悲痛。
“那该如何是好,锦衣卫的诏狱比起阎罗殿更可怕,进去之人怕是会被活活折磨死。相公他如何承受的了……”
白寒烟也低声叹息,这锦衣卫的手段的确令人发指,这二人又是叛族余孽,怕是会扒皮抽筋给折腾死。
忽然,涟儿笔直的跪在白寒烟身旁,抓着她的袍尾,一双泪眼不断的祈求道:“韩大人,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能不能在帮我一个忙。”
“涟儿,你快起来。”
白寒烟急忙伸出去扶她,涟儿却倔强的摇头跪在她脚下,眼里全是恳求搭救之意,白寒烟微叹息:“你想让我帮你什么?”
“帮我……”涟儿深吸一口气,目色悲戚哀绝却意态坚决,一字一句道:“给他一个痛快。”
白寒烟愣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
夜深人静,贵阳狱牢。
此时,牢狱门口全是锦衣卫的人,门口还有两个锦衣卫百户在守卫。
今日午时,段长歌就下令将他的人全都撤了下来,由纪挽月接手。
白寒烟隐在暗处,打算先探一探锦衣卫的虚实。
此刻已到子时正牌。
白寒烟目色冷凝盯着牢狱,心下细细思量,这牢狱门口两道监门,若无看守之人亲自放行,根本就不可能进去,而且灵淼和灵姬被关押在最里头的重牢里,更是无缝可击。
而且,纵使是这等夜深人静之际,也不见一众锦衣卫有丝毫的松懈,明哨、暗哨、巡哨各司其职,全无死角地将整个牢房仔细看护,任何人想要躲过如此多的锦衣卫靠近牢房都是件难如登天之事。
白寒烟紧了紧手掌,如果想要夜闯重牢是绝对不可能了,白寒烟敛眉想了想,她若是以贵阳推官之职若想见一面,应该不会很难,只是不知会不会给段长歌惹来麻烦。
正思及间,却见门口那锦衣卫百户猛然拔出虎头刀,对着白寒烟隐匿的方向大喝一声:“何人在那!”
白寒烟来不及反映,却觉身子陡然被人从后束缚住,将她扛在背上,身影一闪,已经离开狱牢百丈之远。
白寒烟在那人背上使劲挣脱,那人终是将她一把扔下,白寒烟怒极看去,是段长歌恼怒的双眼直切了过来,不由得让她心口一颤,立刻不再动作。
段长歌冷哼一声,扯着她的手腕向前行去,几番挣脱竟也无济于事,白寒烟只好被迫随着他的脚步而走,忽见他停下,偏头看去却是到了她的家。
白寒烟正惊疑间,段长歌却抬腿将大门一脚踢开,白寒烟正欲开口怒斥,却被段长歌一把甩进门里,而他也闪身钻了进来,随手便将门关好。
“段长歌,你要做什么?”白寒烟被他粗鲁的一甩踉跄了几步才站好,忍不住怒上心头。
“我才要问你要干什么,你大半夜的蹲在牢狱门口,若是被锦衣卫瞧见了,当场就会被当做刺客砍下脑袋。”段长歌双眼冷冷的瞧着她,满面怒容。
“我只是想探一探锦衣卫的虚实。”白寒烟忿忿的甩着袖子:“这锦衣卫私刑实在严酷,只怕灵淼和灵姬会遭到酷刑。”
段长歌猛然拂袖,气息冷冽:“只怕这事根本就没有这么简单。”
白寒烟偏头皱眉冥思片刻,想了想上前道:“你这是何意,难道你担心灵淼会受不了酷刑,会将这地图奉上么?”顿了顿,她又道:“他对圣上恨之入骨,段大人实则不必如此担忧。”
段长歌摇了摇头,凌厉的眼底有了一丝锋芒毕露,连冷笑都色厉内荏:“其实皇帝对于芜族精铁之事一直怀疑,王锦之妻便是圣上派来查探,只是一直没有证据。此番匿名信正是印证了他的猜测,可我在王锦之案奏折上对此未提片字,便知我有包庇之心,却又拿捏不准是否真的是个圈套。所以圣上将此事压下来,只派纪挽月来此,是想给我一个警钟,一是侧面鞭笞我其心不忠,再让纪挽月加以试探,二则便是给予抚慰,表示他还是愿意信任我。”
白寒烟惊骇于皇帝用人治人的手段,看来,程潇背后之人此番是针对段长歌来的,好在这一场只是有惊无险。只是如此,他再也无法插手此事,那么灵姬……
“灵姬,我对她心有愧疚,我本想偷梁换柱,诈死放她一条生路,可如今……将我的全盘计划打乱了,灵姬,必死无疑。”段长歌面露阴鸷,一双眼眸冷冷的全是杀意,白寒烟微微一怔,此刻感觉他好像就是地狱而来的死神,忽觉不寒而栗。
“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此事我会重新筹谋,倒是你……”段长歌回眸看着她,忿怒的眼里竟有了一抹担忧:“皇帝让你随之进京,怕是会有所试探。你要学会藏隐锋芒,示弱微小,否则,我不在你身边,没人能救得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