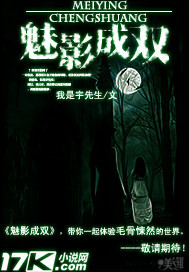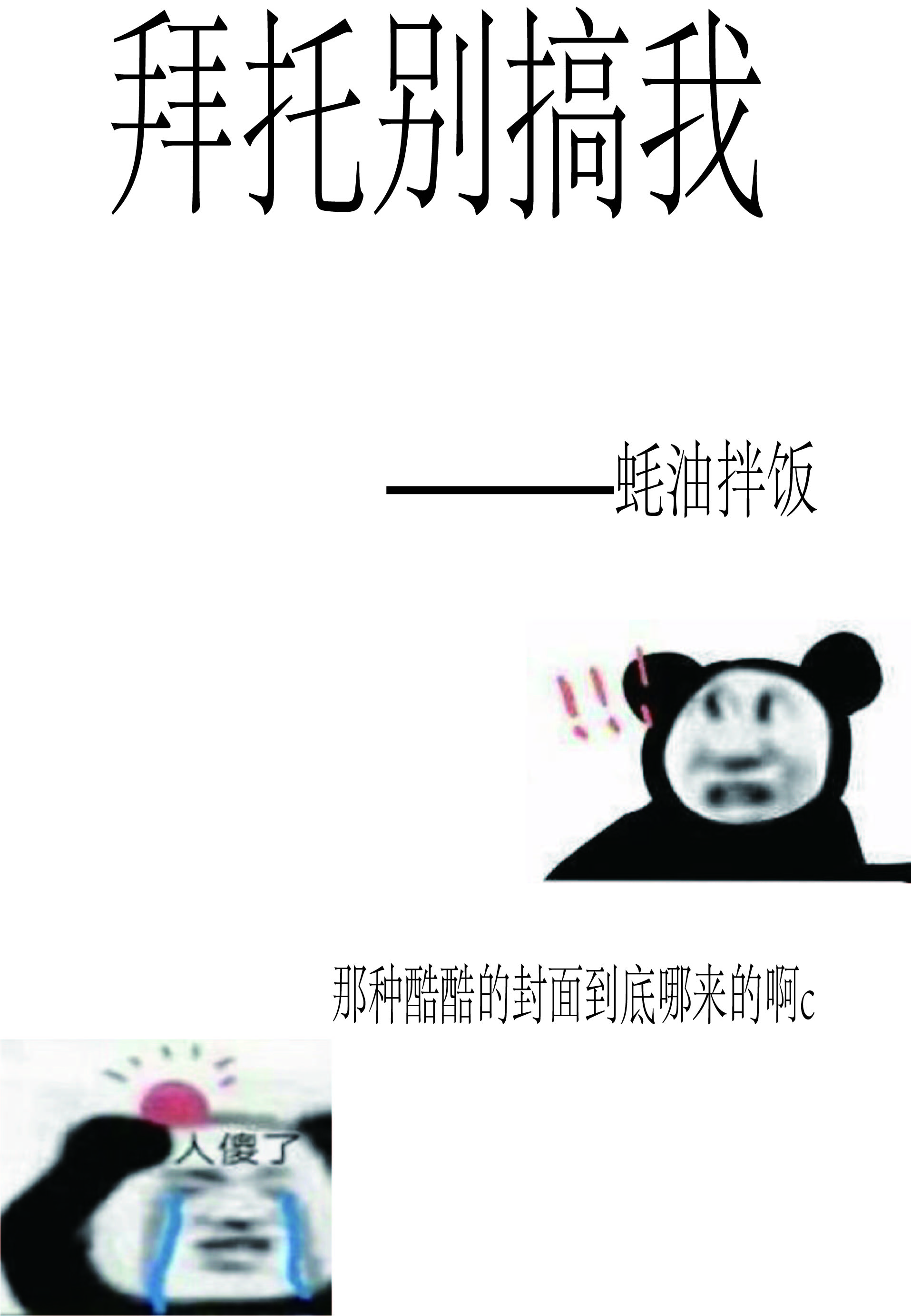老仵作将目光放空,似乎回想到了一些久远的往事,依旧在眼前历历在目,许久,他缓声道:
“有多久了,大约是二十五年前吧,有一位初入仕途的士子要入京城为官,途经锦州城郊时,遇到了劫匪被抢了浑身金银,而那是士子与劫匪搏斗时受了重伤,劫匪正欲他杀他性命,正巧,有一绮罗族的商队经过,好心将他救下,那士子重伤昏迷,绮罗族人天生乐善好施,将他带回去救治,绮罗族一向不准外人进入,可又不忍见他枉死,族长便破例留他在此治伤,那士子在无意中从那商人处却知晓了关于绮罗族的秘闻,永生之说。在他伤好归去之时,那商人便恳求他,莫要将此事泄露出去,那士子满口答应着离去,可谁知这人心险恶,士子进京为官不久,便将此秘闻泄露出去,殊不知这一秘密的泄露会带来多少的灾难?”
听闻到此,白寒烟也是气愤填膺,殊不知那人的言而无信,会对别人造成多大的劫难?
那老仵作满面悲伤,继续又道:“一年后,那商人带着一队绮罗族人又外出经商,便被险恶之人暗中盯上,夜里,当初那个劫匪,那时他已经摇身一变成了边水城的县令,和京城来的一个高官,将这手无寸铁的商人们全部抓了起来,囚禁再一个偏远的地洞里,每日不停的鞭打拷问,勒令他们将此秘闻说出来,若不说,那二人有的是方法折磨这群商人那,段日子,他们过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老仵作稍微顿了顿,白寒烟看见他眼中有别样的情绪浮动,使得他的呼吸急促起来,喘息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平息。
白寒烟不动声色的观察着他,沉声问道:“那后来呢,那群商人的结果如何?可是有人将他们营救出来?”
老仵作望向虚空的视线收了,回来转眸看着白寒烟轻笑一声,声音里带了一丝嘲笑的意味:“姑娘,这世间不公平的事太多了,有几人能像当初那个进京做官的士子一般的好运,这些人虽都是普通的商人,可他们个个都是铮铮铁骨,宁死不屈的好汉,任凭他们如何严刑拷打,都不肯泄露族人的秘密半分,那个高官为之一怒,一气之下,在那地洞里里放一把火,将那群商人全部活活烧死,手段极其残忍。”
白寒烟闻言心头一颤,一股愤怒让她全身血液都微微发热,直至四肢百骸,这和结局在意料之中,都是被人的贪婪之心所驱使。
那仵作浑浊的眼里热泪盈眶,眼前似乎重演着那一场触目惊心的大火,他的声音苍老中透着哀绝:”地洞里那一场火烧了很久,里面绮罗族人凄惨的叫声,声声不绝,最后变为诅咒,是他们临死之前仇恨的血咒,他们说即便是死后魂魄不散,不会放过他们二人,就连这个满城之人也因他们二人的过错而受到荼毒,一个都不会放过!”
外头春来的骄阳温暖宜人,而只有一墙之隔的矮屋内,却让人恍惚是秋寒白霜一般,微生寒意。一如此刻老仵作那双紧紧地盯着她毫不掩饰的双眼,眼里冒出阴冷,抬起腿像一头吃人野兽,一步步向她逼近。
白寒烟双眸微眯了一下,脚步一点一点的后退,老仵作阴毒的眼一直盯着她的双足,倏地,他停下了脚步。
白寒烟一瞬不瞬的盯着他,老仵作脸上嘲讽般轻笑,道:“怎么,现在可是怕了?”
白寒烟不理会他的嘲讽,略显犀利的眼神落到老仵作的脸庞上,沉声问道:”所以那日,在那被冻死之人的尸体旁,你才说起关于会绮罗族勾魂一说,目的只是为了引起恐慌?”
老仵作似乎也不屑于伪装,干瘪的脸上带着阴森的笑容,在日光中仿佛是要人命的罂粟,诡异而邪恶:“不错,我要整个边水城的人终日惶惶不安,提心吊胆的害怕下一个死的人就是他!”
“你是当初那群商人中的幸存者?”白寒烟在次问出问题,皱眉揣测道。
“是!我苟且的活着就是为了今日的报复!”老仵作的声音低沉得漫了过来。
白寒烟却陡然将眉目皱起,不禁有些奇怪,既然地洞没有逃生之路,他是如何逃出来的,而且他丝毫没有提起绮罗花的事,最重要的是他已经杀了很多人,离祭坛开启只有一步之遥,他为何要如此坦荡的承认这一切?
老仵作似乎看透了她的心思,仰头悲怆道:“我命不久矣,祭坛也许开启不了了,可我在死前想要报复,报复这群险恶的人!”
“你既然想报复,为何不去找你的仇人,与这些无辜的百姓有何关联,他们甚至根本就不知晓这件事!”白寒烟怒斥一声,凤目凌厉地看向他,心中划过一抹惊疑。
老仵作若是凶手,那么他活着这二十多年的时间,为何不寻仇人报仇,非要等命不久矣时想要报复无辜的人,这如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你不需质疑我,人都是我杀的,而我还要杀很多的人!”老仵作如毒蛇一般浑浊的眼,阴恻恻的带着嗜血一般的狠厉,白寒烟忽觉心头一颤,道:“你要做什么,已经结束那么多年的事,又何必将那悲惨的事情再次重演!”
“结束……”老仵作的双眼一空,莫名的有些涣散,他喃喃道:“希望这一切是结束……而不是开始。”
“什么!”
白寒烟正诧异他的话中的涵义,却见老仵作忽然抬头朝她诡异的一笑,脸上浮出一丝奇异的表情,那笑容让白寒烟霎那间一阵头皮发麻,脸色苍白如月光般。
而与此同时,白寒烟却陡然发觉脚下一空,原来那仵作竟然开启了机括,在她的足下竟然陡然裂出一个黑黢黢的口子来!
白寒烟只觉耳旁机括的轰鸣震荡,她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眼前一花,身子在瞬间便跌入了黑暗之中,白寒烟的瞳孔骤然紧缩,她觉得自己似乎在不停的坠落,抓不到任何可以攀附的东西,只是这样不停的坠落……,然而,她头上唯一抹光亮也缓缓的关闭,顿时,周身一片漆黑。
后背猛地砸在地上,疼痛让白寒烟感觉到一阵阵眩晕,耳旁除了她的呼吸,再无其它声响,她愤恨的低斥一声,这个老仵作竟然算准了她会来寻他,竟然事先准备好这样一个陷阱,等着她。
顾不上身上的疼痛,白寒烟在黑暗里摸索的站起身,向四周摸索着,走了大约一丈之远便是冰冷的石壁,她顺着石壁一直往前走,走出十步便被一堵墙阻隔,她又摸索着向一旁走去,大约也是十步远也被冰凉的石壁阻隔,如此她丈量一番,心里清楚了,原来此处竟是一个前后不过一丈长逼仄的石洞。
好久,白寒烟渐渐习惯了眼前的黑暗,竟也能看清周遭的模糊的轮廓,她御气纵身,足尖轻点在石壁扶摇而上,很快触碰到那老仵作合上铁铸的洞盖。
白寒烟心下一喜,将双足踢在石壁上,想借力冲开盖子,奈何那石壁表面光滑,加之阴暗潮湿,根本无法支撑她的重量,足下一滑,白寒烟便如落叶一般再次摔在石洞之内,后背结实的摔在地上,她吃痛的溢出一声痛呓,只是她这低低的一声,黑暗中却陡然传来一声飘忽的男人声音来:“谁在那儿?”
男人飘忽不定的声音结实的落在白寒烟的耳廓中,她在黑暗中的眉眼露出一丝喜色,那声音她竟然很熟悉,当下她冲着眼前光滑的石壁大声喊出来:“杨捕头,是你吗?”
白寒烟的话音一落,石洞之内好半天都被传来一语,四周又陷入一片死寂当中,白寒烟星子一般的眼睛里的微沉,她挑起柳眉凝思,好像方才那一男声,似乎是她的幻觉中的幻听一样。
“是我!”许久,石壁一侧传来杨昭幽幽的声音,白寒烟惊诧的问道:“杨捕头,你在何处?”
杨昭低低的一声叹息,却没有回答她,二十低声道:“白姑娘,你还是来了!”
他的话让白寒烟心头划过一抹惊异,他的话如此奇怪,似乎和老仵作一样,都笃定了她会来此一样。
“白姑娘,此处太过危险,我也是不小心栽在了老仵作的陷阱当中,没想到,杀人凶手就是他! ”黑暗中杨昭晦涩不明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
白寒云幽深的眸子划过一抹精芒,老仵作虽然承认了一切,也有很大的嫌疑,可 她总觉得有些地方,还是很奇怪。
“白姑娘你怎么不说话?是受伤了吗?”杨昭见她好久不语,连忙关切的问道。
白寒烟立刻回过神儿,伸长了手臂摸着黑黢黢的墙壁,再次大声问道:“杨捕头,你被关在何处?”
杨昭顿了顿,道:“我也不知这里究竟在哪儿,眼前一片黑暗,我不能视物,只是感觉到你的声音能传过来,应该相离的很近。”
他的话瞬间惊醒了白寒烟,石壁隔绝封闭该是严丝合缝,如何能将声音传过来了?
白寒烟立刻惊呼出声道:“杨捕头,你快四下里摸索,此处应该有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