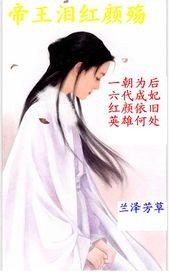这日午后,因为郝夫子临时有事没来学院,丹青课便换成了管博山的点茶课。
管博山中途闹肚子,不到一炷香的时间,他已经跑了四五次恭房,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茶水喝多了的缘故。到最后快要虚脱不成了,他只好先行告假去看大夫。本以为终于得了轻松不用再上课,他却在临走前特意改了主意,让我们自行临帖。
临帖是件非常枯燥的事儿,需要莫大的耐心,这对我一个生性好动的人来说,这过程实在煎熬难挨。
孟节在砚上磨墨的声音沙沙作响,更加令我意志消磨。我百无聊赖的转动手里的笔,墨汁溅了一身,也洒了一些在孟节白衫上。我不甚在意,索性扔了笔,撑着头去看窗外杏花树上的一对黄雀,树枝一阵颤动,便惊飞了那对鸟。我皱眉不悦,稍一移动视线,便发现这波动来源。秦落雪靠着窗边,伸出手去拽探进堂内来的杏花,杏树被他拽得左右摇晃,他折了一枝随手便放在允康桌上,允康接过放进桌上的花瓶里。
再看安康,她难得乖巧的坐着不吵闹,双手捧着脸,一点一点垂着头,打着瞌睡。
我从安康那里收回视线时,顺道看了眼长极。只见他端坐在桌前,眉眼安然自若,在纸上一笔一画的写着字,风吹动他的书卷,纸页发出哗哗的响声,他低垂着眼眸略无波澜。
尚书苑的墙建得极高,亭楼幽深,长窗吹进风来,让人昏然欲睡。
又熬了一日,在我几次和周公会话后,终于熬到放学。等我醒来时,人已经走的差不多了,我把书箱子扔给朵步,准备打道回府。
出了门,走在前方的孟节忽然停下脚步,转过头面对我。我刹住脚,恭恭敬敬对他行了个礼,本想绕开他走,他又一个箭步挡在我面前。
他不会是想找我算刚才溅他一身墨汁的账吧,可看样子又不像。
“你挡着我作什么,快些让开,我要回去了。”
他忽地道:“我又没惹你,你为何总是躲着我。”
“我就是不乐意见着你。”我急着回去吃饭,哪有这多闲工夫废话。
想必是我话说得太过犀利,他沉默了片刻,苦笑道:“你也太小气了,我不就是无意间看到一点你的糗事吗,你也不至于耿耿于怀到现在还不释怀吧。”
这大实话说的真是让人忧伤得很,我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说是显得我气量小,说不是吧,我又的确是因为此事躲着他。想我堂堂北邱公主,居然被人踩住尾巴,竟还是因为吐口水这种上不了席面的把柄,我一世英名,毁于一口水啊。
我立即驳回:“当然不是因为这个。”
然后一把将他推开,能跑多快跑多快的遁走。
一路上我都哭丧着脸,十分担心那个孟节是个大嘴巴,若是他将我的窘事说出去怎么办,若是说给于归和安康她们听到怎么办。别人还好,要是让这两个大嘴巴知道了,还不得奔走相告,组团来嘲笑我鄙视我啊。
我自己被嘲笑也就算了,可我好歹代表着北邱不是。如此想来,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这可事关一个国家的脸面啊,往严重了说,这可是有损国威的大事。我越想越觉得丢人,越想越烦。
朵步不停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摇头晃脑说没有,只是上课累的厉害。实际上,我也不知该如何向她解释我苦恼的原因。总不能跟她说,我在为吐口水去喂鱼的糗事被人看到而烦恼吧。这样也太没面子了。
我思前想后,决定还是不告诉朵步了,免得又是一顿数落。
我满腹忧思回了展华宫,因为这忧伤我只吃了半只鸡,花抚说我今日食欲不佳,中途只添了两次饭。我打着半饱的嗝对她说:“是啊,读书累得慌。”
花抚一听,脸上瞬间挂笑,她以为我是读书用功劳累到了,连连劝我要注意身子,不能操之过急累坏了。
我感动不已,由着这股劲儿,胃口似乎又好了那么一点。我瞟了一眼她面前的鲈鱼脍,花抚立刻会意,贴心的为我盛了一碗饭。“这鱼是特意吩咐厨房做的,给公主明目用的。读书辛苦,吃鱼最好。”
其实我的胃口也不是那么好,只因为这鱼做的实在不错,很是下饭,我又就着吃了两碗饭,终于打了一个饱嗝。
我喝着饭后甜汤,悠悠和花抚说着话,说着说着,不知怎地就扯到了孟节。
“您说的是孟世子吗?公主竟和孟世子做了同窗啊,真是不错。”花抚说着眼睛亮了一亮,满脸春风。
“怎么了吗?”我不解问了一声,却没想到拉开她的话匣子。
接下来,一直持续到我去睡觉的时间,她都在与我说孟节,当然,是她说我听。
花抚一脸花痴像,毫无半点中年妇女该有的矜持。期间她竟然一口气没喘,连口水都没喝。我甚是恼恨自己嘴贱,怎么就说起这人来了,原本只是想从花抚这里探探口风,打探一下那个孟节到底口风严不严。我哪里是想去听他那些光辉事迹。
总体听下来,花抚不断夸赞的都是孟节的医术如何精湛,相貌如何英俊。
孟节长相我倒是清楚,确实不错,只是不知他竟还精通医理。不过我对此一点不感兴趣,我和他又不熟,知道他那么多事干什么,但见花抚说的开心,我也没什么事就稀里糊涂的听她讲下去,全当是在催眠了。
月上中天时,花抚终于一吐为快,极为畅快的拍了拍手,我以为她要走了,正暗自庆幸,她又拉着昏昏欲睡的我问话,困意泛滥,我恍惚听到她在问我觉得孟节这人怎样。我困得要死,只稀里糊涂的说了句:“你和他豺狼虎豹,绝顶般配!”
第二日花抚来服侍我洗漱更衣时,笑成了一副春天到了,红杏出墙的样子。
朵步不知我们昨夜说了什么,看着我一脸茫然。
我感觉花抚看我的眼色怪怪的,我问她她又不说,只一个劲儿掩嘴偷笑,我一阵恶寒。
我倒抽一口凉气,想着无论如何也得挽救她这半老少女。我好心道:“花抚,你是不是慕少艾了?可你早就过了这个年纪了呀,你要是动春心,就只能叫老树开花了,这多不好听啊。而且,你和孟节年纪也相差太大了,你这样,是不是叫做老牛吃嫩草?这样不好,不好。”
花抚眼里闪过一丝暮霭,转瞬变脸,生气道:“公主又在胡说了,怎么能是婢子慕少艾呢。我是在为公主殿下开心。”
“为我?为我什么?”
这话怎么讲,你看上孟节那小子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又不是我阿娘,就算找了郎君,那也不是我阿爹啊,怎么能是为我开心呢?
我与朵步面面相觑,依旧没能弄明白花抚在说什么。
花抚貌似深思熟虑一番道:“孟世子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儿郎,相貌好,性格好,又学得一身精湛医术,出身也配得上公主。而且我听说,庆阳王夫妇也是个好相与的人,将来公主嫁过去,日子一定好过。”
“打住!!”她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
我怒道:“我看你才是在胡说八道吧,我和那孟节总共见过两次面,我何时说要嫁给他了!”
花抚猛然觉悟,却不在点子上醒悟,犹自畅想道:“是啊,不能操之过急,须得一步一步培养感情,等有了感情,再谈婚论嫁也不迟!”
我扶着额,无力地说:“花抚,我求你了,别再乱点鸳鸯谱行不行。我知道你很中意那个孟节,可你不能因为自己得不到,就忍痛割爱让给我吧,我无福消受……”
她再说下去,我就真的抑郁了。她怎么这么有空,竟无端端操心起我的终身大事来。
花抚怔仲道:“不是你自己说你和孟世子郎才女貌,天作之合的吗?怎么这会儿不承认了。”
“我几时说过这种话了……”
阿诏常教诲我说,饭可以乱吃,架可以乱打,可话万万不能乱说,尤其是这种没皮没脸的话。虽然他没少乱说话,却也不妨碍他的三观直。
花抚很是委屈的说:“就是昨夜你睡觉时说的啊。我问你觉得孟世子人怎样,你能看得上他吗?然后你迷迷糊糊就吐露了真心,说你和他是绝顶相配,你对他甚是满意。我这才想着跟你提提意见而已,免得你摸不着门道,讨不到他的欢心。”
我真想一巴掌拍死我自己,顺带上花抚。原来昨天晚上,花抚是在问我和孟节,不是说她自己啊。
我跟花抚解释,说她会错意了,花抚听后难过了许久。一直说我错失良缘,我哭笑不得,垂头丧气出了门。
我在尚书苑上课不满一月,便迎来浴佛节。郝夫子告假,说要陪夫人去踏青。如此粗糙的谎话,也是难为他想得出来。
我们乐得清闲,集体休沐三日。
傍晚时分,我瘫在床上一动不动,静静幻想着,我此刻就坐在蒹葭湖畔游的船上,听着远远飘来的隐隐歌声,吃着糕点赏着月。
而眼下,我只能待在房中枯燥难耐,好想走出展华宫,去看看建康城的夜景如何。
猛地记起今日是个特殊的日子,趁着安平随永河王进宫请安,展华宫暂时无人看管,于是计上心头,强拉着朵步跟我外出逛逛。到了门口,却很不凑巧的被看门的侍卫逮了个正着,生生给赶了回去。
大门不能走,我只得拽上朵步从后门溜出去,谁知后门又被给上了锁。
我思虑再三,为今之计,只有一条出路……墙角还有一个狗洞。
我一脸悲壮的把这个决定告知朵步,可她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一点面子都不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