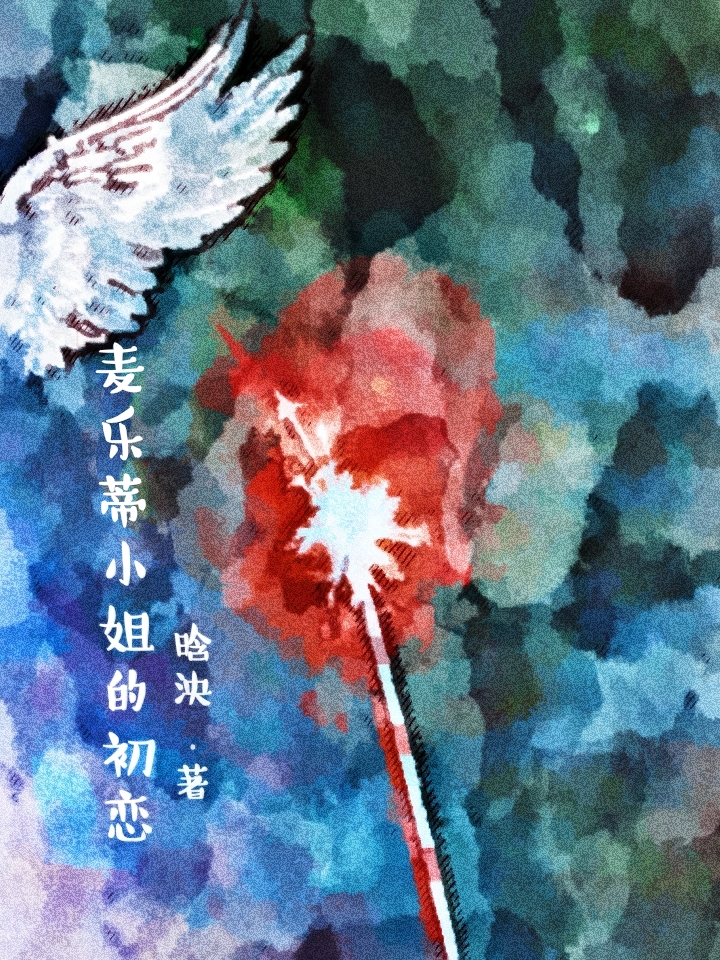贺江北捋捋胡须:“不错。首先是地域,月华山向西是乌兹国万花毒林,向东是沙州玉门关,关外人烟稀少,关内重兵把守。其次,玉雪峰的神兽,一只叫做‘獬豸’,通人语,喜诚信善义之人,若为邪恶定以角逐之。一只叫做‘飞廉’,性情温和。故,并非完全无可能。”
秦枫明白,贺江北不过是给了自己一个希望,好让自己活得久些。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轩朝至今,一千多年来,去月华山的求药者数不胜数,然而返回的只有两人。
他看了看秦柏,轻咳几声:“罢了,于我而言,多活几年,少活几年,并无差别。”
一时间,四下皆寂。
半月后第五蓦被接到竹家休养,相比秦楼的百里路途,自然是竹家这一里二分地,近了太多。
第五蓦不是安生的主儿,但在秦叶的“淫威”下,不得不老老实实又养了一个月,才好好地活动了筋骨。
秦叶告诉她,那次的杀手是倭国派来的,因为上次众人前去淮北帮助永辉坊,狄族尽灭,倭国探子却未绝。
于是,予以反击的倭国人比北狄愈发凶狠!
至于她呢?不动武便不动武吧,伤筋动骨一百天,她也知道。这一个月,她运用内息,好好修护经络,恢复得很好,已不似之前那般脆弱了。
一个半月没好好走动,今日好生将竹家转一圈,欣赏欣赏这颇负盛名的鸢州竹家就是不知,有没有秦楼那般特别?
她换了一身白衣,重伤初愈,身子怕冷,便裹了蓝色的斗篷。
竹家楼阁并不多,只有一座竹园、一隅竹亭、一处竹阁。竹园乃迎接官府贵客和江湖豪门,竹亭除去正厅,多建了寄居住所,用以待客,或亲友暂住。
至于竹阁,前院是主要居所,住着竹家二位家主,后院是仆人婢女的住处。
自竹家正门而入,两片竹林在侧迎门。绕过竹园,一条汉白玉铺就的小道拐个弯,便到了竹亭,分为东、西、中三处耳房。竹亭三处耳房的小道,过了三丈远,便汇合成一条大道,直抵竹阁。
竹阁前院有一座假山,水自上而下流动,汇集成一潭莲池。假山后有一片空地,左边搁着落兵架,右边立着不少木桩。若真要说有何特别,便是这幽幽的竹林,胜过太多府邸,满园竹香,自成风格。
第五蓦看着在空地上比试的秦叶,她偷偷溜了。
过了一处长廊,在某个窗前驻足,屋内的女子正绣着一个荷包。
男子温柔以待:“夫人,这是为我绣的?”
女子美目含情:“是,里面有我去庙里求的平安符,你带在身边,佑你平安。”
男子握着女子的双手:“你平安,我便平安。”
第五蓦暗自离去,心中另有思量。早听闻竹二家主甚是疼爱发妻,果不其然!
穿过后院,有问候的小丫头,每个人都客客气气,很是和睦。这一点,是其他家族没有的。不过,秦楼的仆婢相处的也还不错。
后院有座小山,是吴山的余峰,被竹家做了天然屏障。山顶之中有座别致的楼阁,匾额上题着“临仙阁”三个字。
临仙阁有三层,一层搁置物品,二层有张软榻,顶层搁着小香炉以及各种乐器。
顶层,临窗有个案台,案子上搁着一架筝,檀木筝上刻着四个字——千载芳华。每一层不仅有门窗,还摆放了精致的花瓶,插着文竹、梅花、迎春。恕她眼拙,真的没发现竹家哪里有花园,也不知道这瓶子里的花是哪里来的。
她坐下身,不动武,唱歌总行了吧?!
她的手不似大家闺秀那般,纤纤玉指,相反,粗短粗短,幼时经常冻伤,整个手平常看来也胖乎乎的,不甚好看。而且,还是断掌,双手都是,若没有秦叶,她怕是很难嫁出去了!
十指一滑,筝弦翻飞,乐声空灵。
“盖世武功那不是冒充
沙场上看我与众不同
所谓英雄只是爱慕虚荣
虚名一个我不求传颂……”
竹阁前院,竹尘赋与秦叶正在切磋。
秦枫认真地听歌,叹道:“好一个虚名不求传颂!”
秦帅抱着孩子,听着歌曲颇有感慨:“秦楼主,蓦姑娘真是全才,没有不会的吧?”
秦枫回眸,回味过往一般,笑得开心:“非也非也!那丫头,最怕题字,怎样都写不好,干脆不练了。亦从不习女红,缝缝补补之类的针线活倒没问题,烧饭炒菜亦不在话下。但若是命她绣花、做些精致的食类,怕比杀了她还难,打死不肯学!《女则》、《女诫》,压根儿不看呐!不施粉黛,是因从来不会。”
秦叶在一旁不乐意了,收了剑,回道:“秦叔,你笑什么,抱怨什么,反正她是要嫁给我的,我都不觉得她哪里不好!”
竹尘赋大笑:“叶子,你急什么!霜染不过是开个玩笑,瞧你紧张的,生怕委屈她呢?”
秦枫看了看秦叶,并不取笑,只问:“律辞,那日楼里有事我走得急,没来得及问,小侄子取了何名?”
竹尘赋微笑道:“他的到来,全倚仗蓦姑娘那夜拼死救护,故取名竹倚夜。”
秦枫抱过孩子,一个多月不见,小身子重了些许。
他沉吟道:“其实不必如此,蓦丫头不在乎这些,若非得感恩戴德,恐更是不习惯了。”
秦帅虽意见不和,但领会了对方用意:“秦楼主不必担心,我们只当她是亲人,不会因为恩情就当她如菩萨供着,那样太虚伪了些。”
秦枫会意一笑,见少了个人:“岂儿呢?”
“嗖——”利器破空而来,秦枫身形一闪,背对来人,见招拆招。
院中,白衣与青衫厮缠于一处。
秦枫丝毫没有伤病之态,身法快到极致,面上始终挂着一抹笑意。
秦岂见他这般不尽心,有些不满,软剑“咻咻”甩出:“爹,您不必让孩儿,孩儿欲真心讨教几招!”
秦枫扬眉:“好啊!你可接住了!”
远处传来潇洒的歌声,恰到好处的伴乐——
“傲骨多少清风来找,化入几分自在逍遥
磊落心肠玲珑风貌,情义挂眉梢……”
秦枫躲避的身法又快了一分,一把抓住秦岂的手腕。
秦岂的软剑一甩,竟逼得秦枫松了手。
秦枫不经意地笑了笑,翻手用力格挡,径直打落软剑,脚下一勾,稳稳卡住秦岂。
秦岂“嗤”地笑出声,身子顺势一倒,伸手打开制住自己的那只手,脚亦解脱出来。
秦枫诧异许久,直接收手,笑着点头,脸上上几许赞扬:“不错,大有长进!”
秦岂一个空翻,骑在秦枫肩头:“爹,离上次比试,已经过了一年。如今,我已在你手下走了四十招,你快告诉我,师姐厉害还是我厉害?”
秦枫驮着爱子,略略想了想。岂儿三岁识文五岁习武,如今已四年,却只能在他手中过四十招。至于蓦丫头,三年前的那场对决,自己一样不留余地,蓦丫头用承影剑,竟在青冥剑下走了六十九招!
同样是只有四年,蓦丫头的天分,高出岂儿太多了!
秦岂看着秦枫出神,叹气:“你不说,我懂了,师姐比我厉害,对么?”他从秦枫身上滑下来,泄气地说了句,“看来,功夫最好的还是爹,下来就是秦叶哥哥,然后是二叔和师姐,我又垫底了!”
竹尘赋将秦岂抱起来:“好小子,这都不知足啊!要知道,你竹叔父,可是学七年功夫才能过四十招~”
他真想在后边添一句,我至多也只过了一百三十招,迄今为止,从未赢过!我可跟你爹同岁,就小了一个月!同样三岁习武,同样习武三十六年,切磋也罢,动真格也罢,大大小小的比试不下三十次,一次都没能胜出过……用阿秦的话,能求求我的心理阴影面积么?那可是正无穷加负无穷好吗?!
不过,竹尘赋想到这里,竟然莫名其妙地笑了。
不为别的,只因为想到了离歌。是的,离歌一样打不赢秦枫,哪怕是现在,秦枫已经伤病多年,身体远不如从前,一样打不过他。
呵呵,离歌比他俩小一岁,习武亦迟一年,三十五年了,一样从没有赢过秦枫,至多打了一百一十二招。
秦岂似乎并不知道,父亲的武功如此高深,权当竹尘赋是在调侃自己,便似笑非笑地瞅着他:“竹叔父,莫要取笑我!说谎话,会掉牙的!”
秦枫笑容清爽:“岂儿,你年龄小,身子单薄,能过四十招已属不易,已胜过江湖中一些前辈了。”
秦岂乐呵呵地眨眨眼,一脸报仇雪恨的味道:“别的谁我不知道,反正我能打得过竹二叔!讨厌,他上次嘲笑我,太可恶了!”
童言无忌,九岁孩童惹得几人大笑不止,秦枫竟笑得咳了起来。这孩子还挺记仇呢!这点,怎么像许闹?
远处歌声不停,听得人精神为之一振。
突然间,歌、曲一并顿了。
众人皆惊了——莫不是又有了什么变故?
秦叶飞也似的奔跑,竹尘赋与秦枫紧随其后。
待三人赶到临仙阁前,眼前的景象令人难以忘怀——
只见一袭白衣正坐在竹子上打秋千,一晃一晃,好不自在!那人手中提着茶壶,淡淡的碧色入喉,竟像饮了酒一般撒欢。竹子上的人蠕动喉咙,继续唱道:
“路见不平将袖一扫,平生最爱冤直有报
勇字是刀侠字为鞘,奸佞难逃……
……人言滔滔我自笑傲,痴狂何妨趁年少
名利场中睡一觉,义气台上过几招……”
秦枫随竹尘赋上了临仙阁,秦叶一人自是无趣,一起上了阁楼。但他心里觉得好笑,这丫头分明唱的就是她自己啊!从青都到鸢州,始终在多管闲事,却又一副置身事外的态度,不冷不热。
竹尘赋则心疼自家的竹子五秒钟,点燃顶层的铜炉。他知道,秦枫伤病,不能喝冷酒,省得愈加严重。
临仙阁,竹尘赋与秦枫对饮,秦叶取了一管笛子,顺着第五蓦的调子吹奏。
第五蓦似乎觉着竹秋千玩累了,借着竹子的弹力一个纵跃,直直躺在了一片双竹上。
她一面换了梨花浆品着,一面吟诗诵词。似是倦了,捧着水囊,入定般静下来。
楼上三人谈笑风生,讨论着江湖事,偶尔聊聊国事。
不过是一炷香的时间,双竹上的人似乎睡醒了,睁开眼,还伸个懒腰。
她翻身下竹,于苍翠间起舞。
又一曲,嗓音换成了戏音,阔袍广袖轻旋,拈花指与袖袍交替遮颜,媚态丛生。
秦叶下楼,站在不远处望着,他疑惑不已,这丫头唱的是什么?曲调、排词都不像浥朝,更不似前朝。
竹尘赋很纳闷:“她唱的不是浥朝的歌曲,莫不是那丫头跟你夫人和我家阿秦一样,也是穿越过来的?”
秦枫摇摇头:“不是,她与卓晨景,也就是凌风谷主许闹待过一段时间,许闹教她的。哪有这么多穿越的,按许闹的说法,她们四个都已经快要把时空隧道穿成筛子了吧?”
竹尘赋恍然大笑:“我觉着她们不虚此行!”
秦枫很无语:“罢了,虚不虚都成定局。”
竹林中,白衣翩然,戏步与舞步不断更替,嗓音忽高忽低分段,犹如男女对唱:
“一双鸳鸯戏在雨中那水面
就像思念苦里透着甜
我不问弱水三千,几人能为我怨
轮回百转只求陪你续前缘……”
第五蓦的步子并不很到位,却别有一番情致;嗓音亦无甚优雅,却有着浓浓的情感。
举手投足间,尽显娇憨可爱,又带着几分妩媚。昨夜未干的雨珠被她带起,似一场薄雨轻雾,仙韵十足!
一曲毕,她弯腰提着水囊,倚着青竹喝了慢慢一口梨花浆。她喝得太猛,以至于秦叶鬼魅般的身影飘到身前时,给她吓得全喷出来,浇了秦叶一脸。
第五蓦呆住,尴尬地瞅着秦叶,他抽抽唇角,白色的液体顺着他的面具流下来,前襟湿了一片。
他无奈地摘下面具,用宽大的袖子胡乱抹了一通,额间的碎发有趣的翘着。
她看着秦叶的鸡窝头,再看看他手中的蓝色菩提叶,还在滴水,她从忍俊不禁变成了捧腹大笑。
第五蓦笑着瘫软在落叶遍地的林间,已笑得蜷成了一团。她见秦叶也在笑,只觉得他傻了,更是笑得一发不可收拾。
秦叶简单地整理一下,对躺在落叶中的人笑了笑,不冷不热地来了一句:“即便是烟花三月,昨夜落了雨,地上潮湿不堪,你不准备起来么?”
她终于反应过来,秦叶在笑她,气馁地抓了一把竹叶扔去,秦叶随心一拂袖,竹叶便尽数落下。她陡然失了兴趣,撇着嘴欲起身,却动弹不得。她很尴尬地仰起脸:“我,我笑的肚子疼,起不来了。”
秦叶上前两步,握着她的手,弓着身子,准备拉她起来。
忽地,从竹林里飞来一道气劲,不轻不重地打在他着力的脚踝,他来不及做出反应,直直栽下去。